误 读
作者:陆晶靖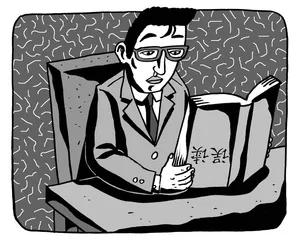
我上大学那会儿买了不少书,宿舍小没地方放,就在床头的墙上钉了几排劣质的铁书架。大家都喜欢有事没事看一看,瞧瞧我最近又进了什么货。有次一个朋友走到我床边看了许久,认真地说:“这本卡卡夫小说不错,能不能借我看看?”
我这个舍友不太喜欢自己的专业,老是挂科,但有股屡败屡战的劲头,总是相信下一次考试前一晚上熬夜复习就能在第二天顺利通过。就这样奋战了4年,依然没有什么挫败感,后来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去了瑞典的乌普塞拉大学学习生物,在那儿遇到一个伊朗女朋友,如今博士都要毕业了。
这个故事说明,不要因为别人在某个领域的无知而轻视他。另外,我那时候正在课堂上学习文本的多义性,他冒着被嘲笑的危险告诉我,这可能就是被德里达、哈罗德·布鲁姆和艾柯谈论过的“误读”。
我对这个术语至今的理解停留于,一个作品公开后,作者就丧失了对其解释的权力。很可能一切阅读皆是误读,因为谁也没法知道鲁迅先生这段为什么要这么写。说得更简单些,就是“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让艾柯非常不爽,他在《诠释与过度诠释》里非常愤慨地控诉了一通还不够,又写了一本《误读》来讽刺。可结果是,他想谈论误读,倒走向了戏仿。他把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改写成了《乃丽塔》,想告诉大家误读是件多么可笑的事,但最后也只是可笑而已。
幸亏我微小到让艾柯无暇顾及。2003年,他出了本小说叫《福柯的钟摆》,让我很不高兴。我想福柯重要的著作我差不多都看了一遍,也没发现有什么钟摆。这种感觉并不陌生,因为之前还有本《海边的卡夫卡》,之后还有本《1Q84》,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的选择是不看,并且因此有点儿反感艾柯,直到去年我在巴黎的万神殿里看到了真正的“福柯钟摆”。我在那里度过了一个下午,惊叹于这件作品的神奇,也责备自己的无知。
有一年CCTV歌手大赛,唱完之后照例要考文化,一个少数民族歌手不太肯定地说,这道题选C,《大地之歌》是马勤写的。主考的滕矢初老师很崩溃,但还是把分给他了。这事儿让我想起一个学汉学的德国朋友,我有一次问他德国文学界怎么看待误读,他一脸惊讶,然后做出一副要跳大神的样子。OK,Voodoo,那是另外一篇文章。
最后再说说乌普塞拉的博士。上次在MSN上遇到,他问我,最近听说中国抢盐呢,你没傻到那个地步吧?我说没有,对这种谣言我还有点觉悟。他可能有点得意,说:有本孔飞刀写的《叫魂》你看过没有?专说谣言的。
Alden Kuhn,哈佛大学教授,中文名字叫孔飞力。■(文 / 陆晶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