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定决心之后
作者:薛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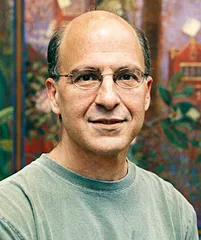 ( 艾尔弗雷德·米尔 )
( 艾尔弗雷德·米尔 )
无人坚持到底
英国《展望》杂志邀请“有影响力、直言不讳的人”分享他们2011年的新年决心。哲学家雷蒙德·塔里斯说他的决心是:“不再寻找逃避持续思考的狡猾的借口。我每年的新年决心都是这个,但是到了1月2日,就总是恢复到往常的状态了。”文学评论家约翰·凯里的决心是“每周游泳两次而非一次(恐怕我去年许下了同样的决心)”。作家约瑟夫·奥康纳说他的新年决心是移民。哲学家玛丽·沃洛克的决心是:“我终于要承认我耳聋了,再也不去参加派对了。”生物化学家尼克·莱恩说:“我不立新年决心,我只是怀抱希望,并加以努力。”英国科学博物馆馆长克里斯·来普利说:“不为没有新年决心而烦扰,也不担心坚持不下去!”
哲学家彼得·辛格说他的新年决心是“坚持思考”。这与他去年初的说法有些矛盾,这个决心太笼统。他在《如何把新年计划坚持下来》一文中说:理查德·怀斯曼是英国赫特福德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他跟踪调查了5000名制订了新年计划的人,发现只有大约1/10的人能把自己的计划坚持下来。在新近发行的书《59秒》里,怀斯曼列出了你可以做来确保取得成功的事情:“把计划分解为一系列细小的步骤;将其告知你的亲朋好友,从而既能获得他们的支持,又增加个人所付出的失败成本。”
辛格写道,我们制订计划的原因大概都是因为自己下定决心要做的事将带来最好的结果。而既然我们已经做了决定,为什么却不去执行呢?自苏格拉底以来,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哲学家们。在《普罗泰戈拉篇》这部柏拉图的对话集中,苏格拉底说,没人会选择那些明知对自己不利的东西。故选择那些不好的东西就是一种错误——人们只会做那些他们认为有利的事情。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认为,只要我们能够教会人们哪些是好的,他们就会去做。但这也是个非常难以让人接受的道理,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都在明知故犯,做对自己不利的事情。
与前两位哲人不同的是,亚里士多德则持另一种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更相吻合的态度。关于为什么我们不能完成自己明知是有利的事情,他认为,我们的理性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是最好的,但在某一特定时刻,理性可能会被我们的情绪和欲望所掩盖。因此问题不在于缺乏知识,而是在于我们的理性不能控制自己人性中其他的非理性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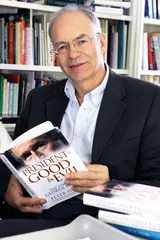 ( 彼得·辛格 )
( 彼得·辛格 )
这种观点也得到了最近的科学研究的支持,研究显示我们的大部分行为都是基于非常快速、直觉和感性的反应。尽管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我们有能力下决心去做什么,但在驱使我们行动的过程中,这些决心与人自身的直觉较量起来,通常都是软弱无力的。
那这跟我们坚持自己的计划有什么关系呢?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哲学教授理查德·霍顿在《意愿、需求、等待》一书中指出,计划是当我们预期未来会出现违背自身最初意愿的趋势时,试图克服阻碍维持意愿的那些麻烦的一种尝试。现在,我们想要减肥,同时我们也理性地明白这样做比享受更多的蛋糕所带来的快乐更重要。但我们预期,明天看到蛋糕时,我们对蛋糕上巧克力那种浓厚口感的渴望会扭曲我们的理性,于是我们就会尝试说服自己再重一点对整个减肥过程来说没多大影响的。
 ( 理查德·怀斯曼 )
( 理查德·怀斯曼 )
关于如何抵制诱惑,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英语教授迈克尔·伍德曾经在一次讲座中说,托马斯·曼笔下的阿申巴赫在威尼斯停留了太久,普鲁斯特笔下的马塞尔希望得到妈妈一个道晚安的吻,这两个人都错误地试图通过单纯的意志力来打败诱惑,他们应该做的是重新把想象集中于选择其他做法的理由(霍乱的危险,母亲的怒火)。
驳斥意志怀疑论
 ( 《有效的意向:有意识的意志的力量》 )
( 《有效的意向:有意识的意志的力量》 )
有时我们能够遏制住冲动,克制自己的欲望,这时我们展示了意志力。我们经常在日常生活中说到某人意志坚定或者意志薄弱。但很多当代哲学家拒绝在讨论人类行为时使用“意志”一词。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意志被认为是一种神秘、多余的东西。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的第621节写道:“当我举起我的手臂之时,我的手臂举起来。问题来了:如果我从我举起我的手臂这一事实中抽掉我的手臂举起来这回事,什么是剩下了的东西呢?(那么动力感觉就是我的意愿啦?)”维特根斯坦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为了回答它,而是用来说明这是一个不恰当的问题,问题里提到一些虚假的内在对象。
笛卡儿和休谟等英国经验论者认为,从我举起我的手臂这一事实中抽掉我的手臂举起来这回事之后,剩下的是意志行动。如果身体的运动是自主的,它一定是意志活动引起的,没有这样一个动因,活动就不是自主的。维特根斯坦很熟悉罗素和威廉·詹姆士的类似观点。在他看来,认为是意志引发身体活动的第一个问题是,难以找到相应的精神活动。有些例子还好说,比如,我考虑了是否举起某个重物,决定去举,然后我用力举起了它。但并不是所有的例子都是这样。我们经常不假思索地做事。比如我们平时说话时,不会思虑半天,说起来也毫不费力。而且,如果说用力或者运动时一定涉及意志,一动不动地坐着也可以说是有意的行为。后来有人提出,随意的行为的特点是包含尝试。对此,维特根斯坦的回答很简单:“当我举起我的手臂时,我通常并不尝试把它举起来。”
哲学家大多认为:“狮子打猎,熊捕鱼,但是我们人类在动物王国的成员中肯定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是主动施行我们的能动性。比如抵挡塞壬的歌声的尤利西斯,思考要不要继续她的婚外情的安娜·卡列尼娜,面对选择拯救她女儿还是儿子的苏菲。在每一种情形下,行为主体不仅行动,他们还体验到自己的行动。对自己的能动性的意识不只限于生命中的重大时刻,它时时刻刻都在。从遛狗到洗盘子,感到自己在思考、决定、做事,这是一个很平常的现象。”而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随意、意志之类的词并不代表某种先于或者伴随着随意行为的精神活动。“随意”一词的用法是怎样的呢?维特根斯坦说:“随意动作的特点是惊奇的阙如。”一个人并不是旁观自己的行为的第三者:一个人不会很感兴趣地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然后感到惊奇。
在维特根斯坦之后,意志问题成了心灵哲学和行为哲学之间的空白。近来,哲学界重新开始谈论意志。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哲学教授艾尔弗雷德·米尔在《有效的意向:有意识的意志的力量》一书中驳斥“意志怀疑论”,他说,我们更有理由认定活动手腕的冲动而非移动手腕的决定。理查德·霍顿在《意愿、需求、等待》中把意志加以分解,在书中依次讨论了意向、信念、选择、意志的薄弱、诱惑、意志的坚定、理性和自由。
霍顿认为,意志是心灵的一种功能或技巧,其作用是执行决定。这种能力大致是以各种方式控制自己。正统的哲学理论认为,意志薄弱是由于缺乏自制力:意志薄弱的人违背他们更正确的判断行事。霍顿认为,这是不对的。他借助意向和选择来澄清这一问题。我们为什么需要做决定,而不只是形成判断呢?他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往往确定不了该做什么。因为知道我们做不到,我们就形成做这一件事而不是另一件事的意向。如果我们担心,我们可能会受到诱惑去做另一件事而不是这一件事,我们进而决心让自己不受诱惑。决心是一种特别的意向,其目的是击败相反的倾向。意志薄弱的失败在于过快地修正个人的意向或决心。意志很大程度上独立于一个人对何种行为最佳的判断和信念。人可以通过做决定来控制自己,由此形成意向,以开展特定的行为。当我们面对诱惑不能坚持意向时,我们就是意志薄弱,当我们能够成功地坚持意向时,就是意志坚强。
霍顿援引了许多心理学实验来证明他的观点。有意向实验考查儿童延缓得到满足以得到更多奖赏的能力。如果儿童忍不住按铃,想尽快得到饼干,就只能得到一块,如果他们等到发饼干的时间到来,就能得到两块。为什么有的孩子能够抵制住去按铃以尽早得到饼干的诱惑?他们的策略各不相同,但最成功的是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不去想奖赏,而是想别的事情,甚至去睡觉。■
(文 / 薛巍) 下定决心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