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粥的唇齿江湖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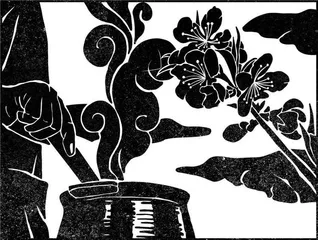 文/摇摇
文/摇摇
翻看朋友圈,看到易二在树皮纸上写了个《白粥帖》:“白粥的味道,时光的滋味和历练的情怀。”伴着树纹,白墨淡淡渗透,仿佛每一道痕迹,都运行着他煮粥时的表情,满纸清欢,穿过粥气入怀。
这帖即便不是一部千年秘笈,也隐藏着私人的戳记。多年前,他看完高考考场,就近住在父亲的朋友家。高考的第一天早晨,这家人盛情盛粥,结果他吃了第二碗后,就吃撑了,考试时遗忘了最熟悉的一首古诗。
虽说还是考上了北大,但是后来他一说起白粥,就像张爱玲笔下的旧月亮——“朵云轩的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
后来的后来,斗转勺柄向南行。直到有一天,他再也不想在异乡吃快餐时,趁着周末,他买锅买米买菜。初次下厨房,就给自己做了一道“五行菜”,白菜炒香菇里有生姜,五行就有三行了,白菜为金、生姜为土、香菇为水;加上几片绿叶和胡萝卜,有了木和火,五行也齐全了。
眠云梦月的午夜,他在包面条的纸上,一气挥毫。顿觉任何时候,只要可以写字,就算步入正轨了;一觉醒来到天明,再煮一碗粥,就有了烟火味,有了书意和笔法。如同师兄谢漆郎将漆器工艺的“晕金”法转化为“晕盐”法,为了让排骨留香,易二握住木勺的长柄,搅动白粥时,就仿佛以八面出锋的腕力,左旋,右旋,上顶,下压,左伸,右推,在锅里写出一个个35厘米大字。
木心说:“没有比粥更温柔的了。”假若彼时,伊人轻问“粥可温”,易二手中的那一把勺,便是一管羊毫笔的中锋,前调是一点一点地洇染,行移在粥面上,柔而飘逸。中调是看白粥克制地沸腾,以写字时的入木三分,将勺伸入锅底,缓而有力。尾调是左右回旋勺柄,欲提还按的那一笔,最情不自禁,也最有烂漫之心。
有粥气的书法充满天然生趣。有时,用勺搅粥,粥面变成芭蕉叶,记得怀素喜欢在滑润的芭蕉叶上写字,不易着墨,却促成了怀素那种忽断忽连、乍干乍湿的笔触,恣意,纵情。
读书时,易二喜欢拿根树枝,在雪地上写字,体验“锥画沙”“印印泥”的感觉。而今,以笔当勺,以纸化粥,写透心境:“在白粥的唇齿江湖/我看到荡漾的橹桨/那一笔如戈如剑/那一舞似飞似驻/留住了夕阳/留住了夏日/小雪还会远吗?”
勺荡粥,笔行纸,那一锅白粥,煮出的是胸中丘壑,磅礴大气。此时,粥就是字,字就是粥。
以粥为墨,残粥都可以在万年黑拓片宣纸上涂鸦几笔。仿佛在一粥一饭的素常里,闪烁了一花一叶的美妙。他在书法纪事《走走停停,不如一路向前》里写道:“书法的快乐,就像情侣间的唇齿江湖,因为互为情深,所以脉脉江湖。”
满粥氤氲,如满纸烟霞,也到底是白粥起底,锦上添花。唐穆宗曾赐给白居易一碗防风粥,诗人食之“口香七日”。易二呢,将淘洗过的大米、几颗去核的红枣,以及各种异国的坚果一同倒入破壁机。随着坚果一粒粒爽利地爆绽、粉碎,粥水早已沸腾不已,仿佛稠浓之中,冲出一刹果实香郁。
这样的粥,舀上一勺,温热的米香包裹着坚果香,哧溜而过喉间,可抵半晌销魂。 生活圆桌白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