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6)
作者:朱伟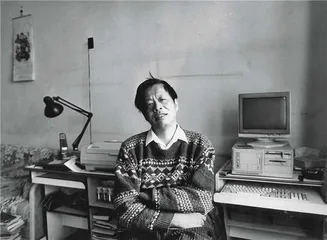 王小波写得最好、结构最复杂的长篇小说,就是《万寿寺》。《万寿寺》的原始素材,也是唐传奇——袁郊的《红线传》。在袁郊的《红线传》中,薛嵩原是薛仁贵的孙子,以臂力、骑射闻名,是潞州节度使。红线是他善弹琵琶的婢女。魏州节度使田承嗣招募了三千武勇,想吞并薛嵩的地盘。红线为主解忧,夜奔魏城(今邯郸),进了戒备森严的田府,在田承嗣枕边盗了装他生身甲子和北斗神名的金盒,拔了他头上的簪子。田承嗣因此“惊恐绝倒”,不敢再贸然行事,反送厚礼于薛嵩,谢其不杀之恩。这个故事后来改成戏剧,叫《红线女》或《红线盗盒》。
王小波写得最好、结构最复杂的长篇小说,就是《万寿寺》。《万寿寺》的原始素材,也是唐传奇——袁郊的《红线传》。在袁郊的《红线传》中,薛嵩原是薛仁贵的孙子,以臂力、骑射闻名,是潞州节度使。红线是他善弹琵琶的婢女。魏州节度使田承嗣招募了三千武勇,想吞并薛嵩的地盘。红线为主解忧,夜奔魏城(今邯郸),进了戒备森严的田府,在田承嗣枕边盗了装他生身甲子和北斗神名的金盒,拔了他头上的簪子。田承嗣因此“惊恐绝倒”,不敢再贸然行事,反送厚礼于薛嵩,谢其不杀之恩。这个故事后来改成戏剧,叫《红线女》或《红线盗盒》。
王小波戏写这故事,也是先写了个短篇小说,就叫《红线盗盒》。戏写薛嵩,为出人头地,先做了杨贵妃姐姐虢国夫人的面首,做生意赚了钱,又花重金买了个沅西节度使的官位,地点换成湘西。红线成了凤凰寨酋长的女儿,田承嗣成了两湖节度使。小说里的薛嵩成了狼狈的角色,田承嗣派刺客来杀他,红线带他钻地洞上了山,官府给刺客烧掉了,薛嵩就写了遗嘱,将红线交代给好友呵护,要自杀。红线被感动,就有了盗盒的故事。
《红线盗盒》变成《万寿寺》,王小波又用了套装结构。薛嵩和红线的故事还在湘西,还是田承嗣派刺客暗杀,王小波以他的想象力,将搞笑的过程复杂化,借助了卡尔维诺、博尔赫斯的迷宫结构。红线的身份还是酋长的女儿,但人物关系多了——薛嵩从长安城宝塔里救出一个女子,带她到湘西,成了专门管理雇佣兵的老妓女。老妓女期望薛嵩在湘西建功立业,薛嵩却沉溺在女色中——营帐中先多了个小妓女,小妓女与老妓女就成为对立面,王小波戏称老妓女“学院派”,小妓女“自由派”。随后,薛嵩又娶回了红线,一心在温柔乡里,这就彻底颠覆了老妓女在营地建立起来的秩序。故事情节变成,她请来刺客,要杀死红线,抢回薛嵩。刺客先后来了两拨,故事发展到后来才交代,刺客头子就是田承嗣。他假装收了老妓女的钱,来杀红线,其实是想杀死薛嵩,夺取凤凰寨。当然,这都是小说中的故事。王小波的套装结构,这小说是“我”写的,“我”可以在写作中不断更改故事走向,这就使人物关系与故事发展有多种可能性,给人扑朔迷离感。
这个“我”是史学研究的“实习员”,专业是史学,却不务正业写小说。小说开头,他就因骑自行车,撞了一辆面包车后失忆。王小波把他放进法国作家莫迪亚诺的长篇小说《暗店街》的语境里。《暗店街》写的是,主角“我”失忆后当了侦探,退休后寻找自己真实身份的过程。万寿寺是王小波小说里,“我”寻找自己的起点。“我”凭印象进万寿寺配殿里自己的工作室,看到自己的手稿,进入薛嵩的故事。这小说的精妙在于,“我”与薛嵩的关系。“我”阅读手稿中薛嵩的故事,伴随着“我是谁”的寻找。“我”的寻找,只有一个白衣女人伴随。这个白衣女人把“我”带到家里,似乎就应是“我”老婆。薛嵩的故事,起点是长安城;而我的寻找,跟随着薛嵩,终点也在长安城。这是王小波的精心架构。“我”与薛嵩对应,薛嵩是“我”的心理投射。薛嵩有点像唐·吉诃德,在“我”的小说里,他的起点是,小说结尾前第七章,从长安金色宝塔里,救出那个被锁着的姑娘,这姑娘到了湘西,就成了老妓女。小说的叙述者“我”说,依小说创作的可变性,这姑娘到了湘西,也可以是小妓女;可以是薛嵩救了那姑娘去了湘西;也可以是薛嵩从湘西来到长安,救的姑娘;可以是故事开始,也可以是故事结束。重要的是,这个“塔”的情节,其实源自万寿寺的锅炉坏了,使“我”想起在大学里修茶炉的情景。茶炉坏了,没水喝,是干渴;干渴引发那姑娘被戴枷锁与塞了黄连木衔口,待营救的场景。从情节是“我”的状态投射的角度,“实际上,是别人用重重枷锁把我锁住,又把黄连木的衔口塞到了我嘴里”。于是,小说中,就会变成“我”在等待薛嵩。因为从“塔”里逃出来,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人。
这小说因此就是,“我”与薛嵩的“双人舞”。这小说里写得最好看的是薛嵩精心设计的迷宫,王小波先描写,刺客们来杀薛嵩,进了无数道门,走了无数条小径,完全迷失方向,最后冲进了牛棚里。然后,薛嵩建了座柚木院子,院子架在八根大柱上,可自由升降。刺客们冲进去,黑漆漆什么也看不见,原来是到了院子平台下,只看到亮处是关在木笼里的红线,木笼其实在平台上。红线让他们照个亮,黄蜂见到火光,就专蛰刺客;红线又让薛嵩把平台降下来,刺客就被压在了平台下。再然后,刺客冲进门,先是感觉上了座“悬浮桥”,一会儿冲到最高点,一会儿又冲到最低点,原来是进了一个由一根轴担在空中的大木桶,太好玩了。
小说中有许多隐喻,核心是不断强调枷锁。薛嵩先是用竹篾条捆红线,“竹篾条的性质与金属丝很相似”。然后又用柚木做了囚车,还做了两块枷,“分别枷住红线的手和脚”,囚车便是抢亲的婚车。从囚笼,后来就发展成可升降的柚木院子。而老妓女想杀小妓女的方法之一,是取出软木树的树心,将小妓女填进去,树皮上挖洞,套住她的脖子,人树嫁接,树皮上就有一张“女孩的脸”。故事的一种结局是,抓住了薛嵩,让他去做苦力,也套上了枷锁,但薛嵩能开锁,经常跑去凭吊红线,老妓女就令他造一把打不开的锁。但所有锁都有开锁的方法,薛嵩就只能造一个实心疙瘩,锁住自己。另一个结局是,薛嵩用他造的,像导弹发射架一样的弩,将老妓女与两个刺客串成了“三明治”。
从这些隐喻读出,这小说的主题还是囚禁与自由。囚禁,还要塞上黄连木衔口;薛嵩用一把打不开的锁将自己锁住,就如行尸走肉了。那么,长安城与万寿寺的关系呢?长安城在小说故事里,是诗意的象征。长安城经常下雪,雪就像整团蒲公英浮在空中,四方皆白,街道是黑的,很美。“我”追随那个白衣女人,乘风而行,漫游雪中的长安城,没有捆绑。而现实生活中的“我”却穿着没色调的衣服,在化粪池堵住的、臭气熏天的万寿寺里。万寿寺与长安,构成历史的距离。王小波要通过这结构表达什么呢?小说里的“我”有一段内心独白:“有意志的智慧坚挺着,既有用,又有趣,可以给人带来快感;没有意志的智慧软塌塌的,除了充当历史的脐带,别无用场了……”
就在这部小说的结尾,出现了那个“我还想回到长安城里——这已经成为一种积习。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的名句。这世界是在写作中,王小波写道:“纸张中间是我的铺盖卷。”这小说的结尾是:“长安城里的一切已经结束,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待续) 小说田承嗣长安城万寿寺王小波8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