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豆师许宝霖
作者:杨璐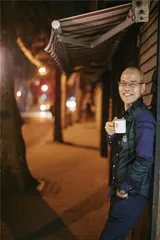 许宝霖(黄宇 摄)
许宝霖(黄宇 摄)
衡量一个地区的咖啡普及程度,现在最常用的一个标准是人均咖啡杯数。台湾2016年的统计数字就超过了100杯,而根据《福布斯》的数据,即便是在中国大陆的一线城市,人均咖啡消费量仅在20杯到30杯,如果平均到庞大的全国人口,每年咖啡消费量还不到一杯。除了数据上的对比,2016年的世界咖啡师大赛上,来自台湾的吴则霖获得了冠军,这项既烧钱又考验咖啡技巧的比赛,亚洲只有日本和台湾地区获得过冠军。因为经济腾飞的时间早,又受到日本和美国的影响,台湾已经走过了从速溶咖啡到精品咖啡的发展过程。
许宝霖1993年进入咖啡行业,是华人地区最早一批国际咖啡竞赛的评审,曾经在2006年到2018年担任过32次卓越杯国际咖啡竞赛评审,从2008年到2013年担任最佳巴拿马咖啡竞赛的国际评审。这两项比赛都是咖啡行业里最知名和重要的比赛。也因为担任比赛评审和每年深入中美洲、非洲咖啡产区寻豆经营自己的咖啡公司,他谙熟咖啡产业链上从种植到经营咖啡馆的流程。他出版的《寻豆师——国际评审的中南美洲精品咖啡庄园报告书》《寻豆师2——国际咖啡评审的非洲猎奇》成为难以到达咖啡产地的咖啡从业者、爱好者们弥足珍贵的产区资料。
对许宝霖的采访,既想通过他的从业经历来标注大陆的咖啡发展阶段,也在其中请他分享了明星咖啡豆的来龙去脉,如何喝懂咖啡的经验。
台湾地区的咖啡文化源于日本和美国
我对咖啡最早的记忆要回到40年前了。我读小学四年级,邻居家的姐姐在台中市美军顾问团工作,带了速溶咖啡回家。那时候台湾的经济条件很差,小朋友没什么零嘴吃,看见那个罐子挺漂亮,就打开看,里面是黑的,蛮香。她弟弟跟我说,你不能拿,否则我姐姐会把我打死。我当然就不拿,但是把香气记住了。
大概到了小学五年级,我下课跑去打工,赚到零用钱,就去镇上一家专门卖进口食品的店里问,有没有一罐小小的东西,里面是黑色的,还很香。老板想了一想,拿了一罐速溶咖啡问我是不是这个。我看瓶子是一模一样的,就说是这个东西。他说,是你爸爸要喝吗?这个东西很贵的。我到现在都记得,那罐的价钱是48块钱台币,当时一碗排骨面大概差不多5块钱台币。
我把速溶咖啡买回去还搞了一个笑话。因为没有见过咖啡嘛,而且挺贵的,我就煮了一大锅水才放一点点粉末,没什么味道。我跑回去问那个老板,他说,你是煮的吗?我说,不就是烧水丢一点下去吗?他说,不是这样子的,大概200毫升水放一勺半的咖啡粉。我听完就要走,老板叫住我说,你不能只买速溶咖啡,会太酸了,不能喝,还要买方形的葡萄糖。我又开始存钱买葡萄糖。那一瓶咖啡,我躲躲藏藏喝到小学六年级,不但过期了而且因为放太久受潮结块了。这就是我开始喝咖啡的过程。
美国大兵都喜欢喝咖啡,他们把速溶文化带到台湾,但当时对民众的影响并不大。台湾本地的咖啡主要还是受日式咖啡馆的影响。那大概是上世纪70年代,也就是我读初中的时候。台湾升学跟大陆一样,竞争非常激烈,学生们都很辛苦,我那时候会偷存一些零用钱,每次月考结束之后就去咖啡馆里喝咖啡。台湾当时的咖啡馆还是在用虹吸的方法煮咖啡,价格很贵。有趣的是,如果搭早班车过去,正赶上咖啡馆里供应早餐,它的早餐是便宜的,大概80块钱台币可以吃到煎荷包蛋、烤三明治,小杯的果汁等,重点是还有一杯咖啡,虽然是小小的一杯,但也是现煮的。
如果你去过日本的喫茶店就会发现,台湾的咖啡馆跟日本这种传统的咖啡馆是一模一样的。这是我要讲到的一个重点,台湾的咖啡文化并不是受到美军速溶咖啡的影响,早期是受到日本影响的,包括店里的装修风格,及提供早餐附送咖啡这种经营模式。
1993年,我进入到咖啡行业,当时已经是速溶咖啡和美式咖啡的天下。速溶咖啡属于快消品,电视上都是它的广告,另外还有一种是装在铁罐子里的,也很盛行,比如说伯朗咖啡,就是铁罐子咖啡品类里市场占有率的第一名。美式咖啡流行的关键时间点,我觉得是麦当劳进入台湾。它早餐可以无限续杯,虽然跟现在精品咖啡比,品质很一般,但造就了很多喝美式咖啡的人。
讲究咖啡品质的开始,自己烘豆子
我1993年创立欧舍咖啡的时候,台湾人对咖啡的认识就像很多亚洲国家一样,没办法分出品种,只能用国家来分类,比如哥伦比亚咖啡、巴西咖啡、埃塞俄比亚咖啡,说不出更详细的关于咖啡豆的信息。日本在亚洲是个例外,我特地跑一趟日本去做考察,当时他们就已经能喝到很多特别的豆子,比如也门的摩卡、夏威夷可纳,当然最重要的是牙买加的蓝山咖啡。蓝山咖啡在那个年代因为又贵又出名,渠道被日本垄断,其实非常罕见,台湾卖的蓝山咖啡很多都是假的,没人知道真正的蓝山咖啡长什么样子。
我在日本待了一个星期,找到一些确实很好喝的咖啡馆,它不是只有苦或者酸或者涩,而是很协调,不用加糖后味也是甜的。日本之行颠覆了我对咖啡的认识,但用在我自己的咖啡店里,条件还不允许。我的第一家店开在台北,第二年又在台中开了一家店,结果台中店的状况很差,台北店又没人可以去管,顾此失彼,所以就决定把台北店收了。股东们的合作告一段落,只剩下我一个人守着台中这家店。
因为店里生意不怎么好,我就比较有时间练习咖啡功夫。一杯咖啡或者说一个咖啡馆的质量,受熟豆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买了一个小型的烘焙机,开始自己烘焙豆子。我发现豆子并不都是那么酸、那么焦的,如果烘焙功夫好,生豆材质好,豆子其实可以用浅烘焙来维持它产区的原始风味、香气和协调性。那就可以喝到这个产区、这个咖啡品种的特色。我那时已经开始跟朋友晚上喝一些红酒,常常在红酒里找香气和味道的变化,咖啡跟红酒的性质很像,它里面含有几百种芳香物质,不同产区、不同品种都有自己的特色。
台湾当时自己烘豆的咖啡店很少,我主要靠自修。那个时候已经有了网络,虽然非常慢,但能连接到国外的一些网站去看资料,也能写信给外国人。网上很多人讨论自己煮咖啡,虽然互相不认识,但是很友善。我慢慢摸索,店里来了朋友、客人,我就免费请他们喝,让他们说自己喜欢哪里,不喜欢哪里,功夫就是这样磨起来的。
因为开始自己烘豆,我从咖啡供应链的最下游咖啡回溯到熟豆,又继续往上关注到生豆领域。1997年开始,我有机会拿到国外的生豆样品,就像我在日本咖啡馆里喝到的那样,一些特别的、台湾市场上见不到的豆子。喝到样品,我就跟台湾的贸易商沟通,拜托他们帮我买一些这样特别的豆子。他们说,这种豆子很贵,在台湾也没有市场。我的咖啡店虽然在马路旁边,可那个地点不好,生意少,消耗不了很多,只能是贸易商大量进商业豆的时候,在货柜里帮我买一袋、两袋。这一袋咖啡豆,有的国家是45公斤,有的国家是60公斤,在我这样的小店里要卖一年时间。
咖啡供应链:从咖啡馆到产地
2002年的时候,台湾经济起飞了,可咖啡豆消费并不多,中美洲的一些庄园当然很希望打开台湾市场,就邀请一些咖啡行业的人到产区去。我从前一直麻烦贸易商朋友帮我找生豆的资料,买奇怪的豆子,他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找我一起去。我大概是台湾做精品咖啡和自家烘焙的人里,最早一批跑产区的,那时候中南美洲很多做精品咖啡的庄园还没有遇到过华人客户,后来,我又去了非洲,同样也是这种情况。在我们华人之前,是欧美人和日本人追求得早。这里面欧美人事实上指的是美国人,欧洲人直到现在对咖啡的质量要求也不高,整个欧洲懂得欣赏咖啡品质是从北欧开始的。准确地说,美国人、北欧人和日本人是精品咖啡的先驱。
当时我已经从事咖啡行业十年,其实不清楚生豆是如何生产的,全是靠材料获得知识,抵达庄园现场,才目睹由种子、萌芽、采收、去皮,之后处理、静置仓储所有过程。我也明白了要了解咖啡豆的风味变化和品质差异,唯一的方法就是到产地去请教栽种者。优质咖啡的变数太多了,咖啡豆虽然来自于咖啡树的果实,可采摘只是咖啡豆生产的开始。果实处理成生豆,其中就牵扯到地域性对咖啡风味的影响和处理方式对咖啡豆的影响等很多细节。处理后的咖啡生豆只是原材料,它们要运到消费国去烘焙,烘焙师对这一款豆子的理解和如何用烘焙技术去实现也是一关。最后,熟豆到了吧台师傅手中,他们的冲煮或者说萃取技术也很重要。每一关都是一个环节,我入行20多年还在摸索和学习中。
回来说原产地,中美洲和非洲的情况也不一样。中美洲咖啡指的是墨西哥以南,巴拿马运河以北的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巴拿马等7个国家,以庄园体系为主要形式参与到咖啡行业中,比如巴拿马的翡翠庄园、尼加拉瓜的柠檬树庄园等。2008年起,我因为担任“最佳巴拿马”竞赛的评审,每次都要深入到不同的产区和庄园。如果是生豆公司或者寻豆师都是跟庄园主进行咖啡交易。
非洲则主要是小农户种植,采收和后制处理的设备简陋,比如埃塞俄比亚九成以上的咖啡由小农户生产,大型农场只占5%,多数咖啡农栽种面积小于1公顷。这种情况下地区水洗场或合作社就具有庞大的影响力。即便如此,想精通所有非洲产区的生豆非常困难,仅埃塞俄比亚的西达摩就有数百个水洗场,在同一产季内遍访、记录、测试所有的样品,几乎不可能。
寻豆没法一劳永逸,从我最开始去产区到现在,同种咖啡的风味和品质都有差别。现在世界上最贵的咖啡豆之一瑰夏,它是2004年由巴拿马的翡翠庄园打比赛出名的。我那一年也拿到了翡翠庄园瑰夏的样本,并且在欧舍咖啡举办了一个杯测会,当时它的花香、柑橘、莓果、大吉岭茶香引起了热烈讨论,有人误认为它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耶加雪菲。
2006年,我拜访了翡翠庄园。它位于巴拿马博魁地的巴鲁火山山脉上,博魁地被称为“咖啡乐土”,海拔1200米到2000米的地区是栽种优质咖啡的高度,低温11摄氏度,高温27摄氏度,温差大但是低温不至于带来霜害。巴鲁火山的沃土、太平洋带来的雨量、山区雾雨和多变的风势都是绝佳的微型气候。这里虽然在赤道附近,可很像夏天的瑞士,早晚温度低,每次去我都会穿外套。
翡翠庄园的瑰夏是按照生产区域再细分成小批次竞标或者售卖的。我曾经连续几年杯测过标示为ES4批次的瑰夏,不同年份的风味多少有些差异,主轴风味不会偏移,某些香气或者独特风格确实会改变,比如花香味不同,佛手柑味道转弱,柑橘味也发生变化等等。庄园主瑞秋曾经跟我说,高品质的咖啡有能控制和无法控制两种因素,采摘成熟的咖啡樱桃、严苛的处理工序和按照批次做杯测品控是可以控制的,但是雨水和夜晚温度是没办法控制的,它们会造成品质落差。
还有一个变化更明显的例子是蓝山咖啡。早期的蓝山咖啡是很典型的牙买加品种,酸不会很明亮,有温润感和独特的草本香气,带一点比较熟甜的瓜果味道。它的触感也很好,又不是像印尼咖啡那么强烈厚实,属于温润均衡、皆大欢喜的咖啡。后来这个国家的咖啡树得了叶锈病,农业单位处理得很糟糕,使得它的质量和生产量都下滑了。产量变少以后,它因为也是世界上出名的咖啡,所以,价格变得更贵了。我觉得它现在的性价比不高,其他好咖啡也越来越多,懂咖啡的人慢慢就不太喝它了。
像喝茶、红酒一样喝懂咖啡
咖啡有一个好处是上班族负担得起。好的红酒很贵,好的茶也是天价。我公司的经理买的老茶,要花去他一年的薪水。无论是瑰夏还是蓝山咖啡,它就算是很贵,也比不了顶级的红酒和茶的价格。1997年,当时台湾市面上加糖、加奶卖250到360块台币一杯,我算了一下成本,如果卖70块钱台币不会亏本,但是也没有赚钱。我就用蓝山咖啡做了一次活动,卖100块钱一杯,但是不许加糖、加奶,这既省了成本,又喝出了蓝山咖啡的好滋味和我烘焙的功夫。因为很多人以为蓝山咖啡不可能那么便宜,媒体就来采访,发现我这家店小小的,自己烘豆子,说我是怪店,就红了。
所以,台湾人一开始不懂得喝咖啡的新鲜不新鲜,烘焙怎么样。我觉得来店里的七八成人都是喝不出来的,但是有一两成喜欢时髦的人,比如有喝红酒的、喝茶的习惯,或者听说国外有特别好喝的咖啡,他们在味觉上比较敏感,喜欢追求饮品背后的知识,是喝得出来的。还有个奇怪的现象,一些大学生是喝得出来的,他们在网上跟国外交流,还会买爆米花机自己烘豆子。这些大学生当时没什么钱,跑到欧舍来玩咖啡,我就让他们自己冲自己喝,需要帮忙的时候,在店里帮一下忙,不收喝咖啡的钱。经过20年,这些人中已经出了台湾咖啡圈的名人,比如我们的店长李雅婷,从店里的小妹做起,她是第一届世界杯虹吸咖啡大赛的冠军,还拿过“世界咖啡师大赛”台湾地区选拔赛的冠军。
一杯好咖啡的原则,我觉得第一是要喝出风土味,第二是能够让消费者喜欢,第三是接地气,让多数人喝完还想喝。风土味并不神秘,经常喝就能归纳出来。比如非洲豆里出名的品种都集中在东非,它们的酸质成分比其他国家的要明显,比较明亮,可能是柑橘柠檬类的酸,到了肯尼亚变成莓果类的酸,甚至偶尔带有百香果的酸、葡萄柚的酸,这种地域风味很好辨识。除了风土味之外,一杯好咖啡必须让消费者喜欢,这就需要在烘焙阶段对咖啡因地制宜地调整。咖啡的风土味再好,如果消费者不喜欢喝,那豆子就可惜了。台湾早期跟大陆现在是一样的,普通消费者不喝酸咖啡,我就把豆子炒得特别深,花香、水果香都没有了,但是不酸,先让人接受,以后再培养欣赏浅焙。
接地气说的其实是把客人培养成喝咖啡的行家,以后他自然就跟着你一起喝了。咖啡是水果的果实,如果想喝出层次丰富的香气和风土味,一定是浅焙,一定是酸的。酸没问题,但是酸中一定要有甜来打底,也就是水果酸。我20多年前去日本的时候,发现两家不同的店,焙炒同一款豆子的方法是不同的,一家焙炒得深,有焦糖甜巧克力味,另一家焙炒得很浅,是花香和蓝莓味。这个事情一直在我脑子里激荡,难道不能兼顾吗?回到台湾,我开始把同一批豆子分成两种出品,一种焙炒得深,一种焙炒得浅。最开始喝深焙的、比较甜的人多,可是经过了很多年后,变成喝莓果调性的人多了。客人们接到了产区的地气,变得懂咖啡了。
除了顺其自然地等客人自己喝懂,也要做些推广。我的咖啡店一直有试饮文化,只要是营业时间进到店里来,就有咖啡免费喝,客人觉得好可以买豆子回去煮,也可以现场点来喝。公司的网页上还有我们进货的100多种豆子的风味特征、香气、产地等信息,如果是对咖啡感兴趣的客人,不但能喝到,还可以很方便地查到资料。从1994年开始,我还在台湾各地办品尝会和趣味冲煮比赛。这件事有趣的地方是,我跟消费者们不是盲测来猜咖啡的品种和产区,而且鼓励大家欣赏它的美。这一杯咖啡哪里好喝,你喜欢它的哪个特点,这既让人很放松,也能从客人的角度回溯,让冲煮咖啡的人,炒豆子的人,跟咖啡农都战战兢兢地把品质顾好。
很多对咖啡感兴趣的人追求能够喝出咖啡的品种和产区,这些都需要多喝才能记得住。有一些客人已经喝了快20年,我们供给的印尼豆子、埃塞俄比亚豆子或者危地马拉豆子,他都能喝出来。比较容易练的方法是专注于某个产区或者品种,每天喝,喝个两三年,就能喝出来了。
(实习记者王雯清对本文亦有贡献) 饮食咖啡消费咖啡烘焙咖啡风味危地马拉咖啡咖啡的产地蓝山咖啡咖啡行业烘焙师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