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科学地制造一个“异世界”?
作者:苗千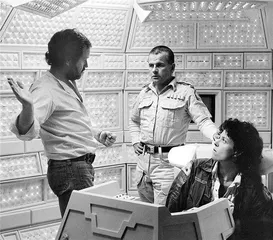 除了能够制造出符合好莱坞标准的产品之外,詹姆斯·卡梅隆的另一面则经常被人忽略,这就是几十年来,在他不同的电影作品中,一以贯之并且不断完善地对于“异世界”的构建。这种持之以恒的对于人类世界之外的想象世界的构建,或许是出于拍摄“科幻电影”的基本要求,或许是源于卡梅隆在早年接受的物理学训练,或许是源于难以解释的天性。无论如何,这些因素已经被卡梅隆融于一体,为他独特的电影风格和种种奇异的想象世界服务。
除了能够制造出符合好莱坞标准的产品之外,詹姆斯·卡梅隆的另一面则经常被人忽略,这就是几十年来,在他不同的电影作品中,一以贯之并且不断完善地对于“异世界”的构建。这种持之以恒的对于人类世界之外的想象世界的构建,或许是出于拍摄“科幻电影”的基本要求,或许是源于卡梅隆在早年接受的物理学训练,或许是源于难以解释的天性。无论如何,这些因素已经被卡梅隆融于一体,为他独特的电影风格和种种奇异的想象世界服务。
通过更细致的观察,我们还能看出卡梅隆构建“异世界”的时间脉络——这些与现实世界或似是而非,或大相径庭的“异世界”,其来有自。
由科幻源头开始
《异形》的剧本作者丹·奥班农曾经承认,他创作这个太空科幻恐怖故事的灵感来自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诸多科幻作品——以科幻的形式讲述一个恐怖故事,恰恰是回到了100多年前科幻文学的开端——卡梅隆作为科幻电影的导演,在有意无意间,让自己执导科幻电影的生涯从科幻文学的开端开启。
目前人们公认的世界上第一部科幻小说,是由英国小说家玛丽·雪莱(Mary Shelley,她也是英国著名诗人珀西·雪莱的妻子)在1818年创作的科幻恐怖小说《科学怪人》。在这部开创性的作品中,作者通过想象,创作出了一个似人非人的、通过科学手段制造出来的怪人弗兰肯斯坦。弗兰肯斯坦的形象大致代表了当时人类对于科学的态度——它强大却又对自身充满迷惑,难于被人控制,对人类来说充满危险。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最终给他的创造者,也就是人类,带来了无尽的痛苦。
玛丽·雪莱创造这样一个科学怪人的形象,本来是源于几个朋友在瑞士旅行期间的一次创作游戏。她本想写出一个具有哥特风格的恐怖故事,却在无意之中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文学领域。与之类似的是,在100多年之后,卡梅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拍摄的《异形2》也是一个披着科幻外衣的恐怖故事。卡梅隆的创作能力和雄心壮志显然不止于此,由此开始,他努力拓展出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创作领域,这就需要他吸取科幻文学发展的经验,以此来营造出愈发完整的科幻异世界。
比《异形2》更早上映的《终结者》或许更能够体现他的科幻风格。“终结者”系列电影,虽然更多是以视觉效果取胜,观众们更容易记住阿诺德·施瓦辛格在电影中的硬汉形象和其中的精彩特效。但正是在这一列的电影中,卡梅隆首次建立起他自己完整的异世界——虽然电影所展现的仍是一个人类世界,但使其作为一部科幻电影能够立足的根本,则是源于一个贯穿故事始终的科幻理念:在“未来”的人类(或是机器人)利用时间机器回到“过去”,希望通过杀死“过去”的人而改变“未来”。
实际上,究其根本这个理念源于一个物理学悖论:时间为什么是单方向的?有没有可能进行时间旅行而回到过去?又有没有可能通过改变过去而改变未来?几千年来,关于时间的本质一直是哲学家们研究的重点,而关于时间旅行的可能性,则是现代理论物理学家们所热衷讨论的问题,至今众说纷纭,这也因此成为科幻作品的一个“富矿”。卡梅隆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基于能够进行时间旅行的基本假设,构建出了一个完整的科幻故事。
当我们时隔30年再看《终结者》系列电影,施瓦辛格的硬汉形象已经不再流行,电脑特效也显得落伍,但导演所构建出的这个具有赛博庞克风格的未来世界却丝毫没有过时。
异世界的运行规则
卡梅隆创造异世界的能力在1989年上映的《深渊》中得到了完美的展现。在这部电影中卡梅隆身兼编剧和导演,在开篇即示以哲学家尼采的名句:“当你凝视深渊,深渊也回之以凝视”。此句颇有警示的意味,而在影片开头的深海世界场景中,一艘人类的深水潜艇发生灾难坠入海底,一下就把观众带入了一个陌生、压抑甚至恐怖的情境之中。
影片中最为关键的,正是他对于海底世界的构造。电影中所谓的“深渊”,指的是对于人类陌生且危险的海底世界,同时也代指在海底世界生活的高科技文明。而在电影开始时尼采所说的人与深渊之间的相互“凝视”,也就不难理解为人类与未知的高科技文明之间的第一次接触。
 在《深渊》故事中,虽然开场的气氛有些压抑紧张,最终却出现了一个圆满的升华式的结局——在有更高文明程度的海底生物看来,人类的美苏争霸不值一提,但人与人之间富于牺牲精神的真挚情感却能够跨域种族和文明,最终打动了它们,让两种文明能够进行交流。或者也可以说,是更高层次的海底文明拯救了陷入重重困扰之中的人类文明。这样的故事设置,不是导演不知道该如何收尾所做尴尬升华或是陈词滥调的道德说教,而显然是经过了审慎的思考和设计,凭借他对于科幻作品的深入理解而设计出的另一个神奇的异世界。
在《深渊》故事中,虽然开场的气氛有些压抑紧张,最终却出现了一个圆满的升华式的结局——在有更高文明程度的海底生物看来,人类的美苏争霸不值一提,但人与人之间富于牺牲精神的真挚情感却能够跨域种族和文明,最终打动了它们,让两种文明能够进行交流。或者也可以说,是更高层次的海底文明拯救了陷入重重困扰之中的人类文明。这样的故事设置,不是导演不知道该如何收尾所做尴尬升华或是陈词滥调的道德说教,而显然是经过了审慎的思考和设计,凭借他对于科幻作品的深入理解而设计出的另一个神奇的异世界。
与在“异形”系列中状若蝎子、以人类为食的可怕外星生物不同,《深渊》中的海底生物外形与人类类似,对人类也展示出了友善的一面。这些海底生物不仅拯救了人类潜水员的生命,而且看其外形,除了有类似于深海鱼类的鳍之外,它们竟然有着与人类极其类似的四肢和五官——这样的外形设计会让观众容易生出亲切的感觉。无论居于海底或是外星,人类文明与发展程度更高的其他类型文明的第一次相遇,从20世纪以来就一直是科幻作家们创作的竞技场。
人类与外星文明的相遇,这样的题材固然在现代熟读科幻的读者眼中接近于陈词滥调,但它并不是自科幻文学诞生之日起就出现的自然产物,其间经历了接近100年的演化和人类对于宇宙认识的革命性变化。在20世纪之前,人类绝大多数的科幻作品都是对于工业社会和经典物理学发展的想象,其中代表性的人物当属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在这位活跃于19世纪末的科幻巨匠的作品中,人类乘坐着远洋船探索地球表面的陆地和海洋,发明了潜水艇探索海底,还发明了比空气重的飞行器飞上天空(在当时尚未有飞机出现,人们普遍认为想要飞行,必须利用“比空气轻”的飞行器,例如热气球才能升上天空,但凡尔纳则预言比空气重的飞行器必将出现),人类甚至将牛顿力学发挥到了极致,用一个大炮把几个探险家发射升空,环绕了月球一周之后又回到地球。
在19世纪的科幻作品中,人类如同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幼儿,用欣喜和激动的目光探索周围的一切,确认自己是整个地球的主宰,相信未来也必将是这样的生活的延续。在这样的心态中人类无暇他顾,没有兴趣也还没有能力去想象还可能存在其他类型的文明可能与人类进行交流。但科幻作品对于机械社会和经典物理学的想象随着20世纪的到来戛然而止,被称为“科幻小说之父”的凡尔纳也于1905年去世,这恰好是狭义相对论诞生的年份。
由量子力学和相对论所掀起的物理学革命,展示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量子力学揭示了微观世界的行为规则与人们所熟悉的宏观领域截然不同,相比之下相对论的诞生对于科幻作品的影响又更为深远。在1915年诞生的广义相对论,成为人类探索宇宙的工具,人类第一次把目光投向了无垠的宇宙,也第一次意识到了自身的渺小。相对论的诞生对科幻作家造成了持久的影响——宇宙的广阔甚至超出了人类想象力的界限,该如何通过科幻作品去表达这样的广阔,成为一个持久的命题。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科幻作家们开始幻想在其他宇宙环境里,有着与人类文明完全不同的外星文明。外星生命以怎样的状态生存?它们是否知道人类的存在?它们的科学水平会否远超人类?如果有朝一日两种文明能够相遇,又将会对人类造成怎么样的影响?这样的想象成为20世纪上半叶多数科幻作家创作的动力。在诸多的科幻作品中,近如月球和火星,远如数千万光年之外的遥远星系,都是外星人的栖身之地,而人类又总能在某种情境之中与之相遇,发生种种离奇的故事。
生命现象为何在宇宙中如此稀少?人类是否是宇宙中唯一的智慧生命?此类问题在科学界尚且存在争论,而科幻作家们已经先走一步,开始探讨人类与更高层次的文明形式接触时可能发生的故事。当我们回顾此类作品,会发现其中的经典大多出自受到过科学训练的作家。例如曾经进行过雷达研究,在伦敦大学学院获得了数学和物理学学位,被称为20世纪三大科幻作家之一的亚瑟·克拉克就创作过多部有关地外文明的小说。在《2001:太空漫游》中,人类通过一块深埋在月球土壤中的黑石板意识到了外星文明的存在,从而义无反顾前去探寻;而在《与拉玛相会》故事中,一个外星飞船无声无息地穿越太阳系,却对地球文明造成了极大的震撼。
在《深渊》中,卡梅隆已经赶上了科幻创作的时代潮流,利用高超的电影手段创造出了一部具有时代精神的纯科幻电影。由于电影剧情的需要,卡梅隆把高级文明从外星转移到深海,相比于大多数科幻作家不去通过文字正面描写其他文明生物的样貌,卡梅隆在电影中通过技术手段,塑造出了与人类类似的高级生命形象。这是卡梅隆通过电影手法对科幻作品进行的大胆创新。
在卡梅隆创造的深海世界中,这些起初不为人所知的生物所掌握的科技水平远远领先于地面的人类,他们理解人类,收听人类,同时躲避着人类。人类由于政治因素,把战场延伸到了海底,甚至差点引发核大战,而最终让深海文明与人类文明实现交流的,是人类所展现出的爱与勇气——这样的结尾实际上体现了同时代大多数有关外星文明的作品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所谓的异世界未必存在,外星文明可能永远都不会出现,人类有关外星文明的想象,其实都是有关人类自己,人类需要进行自我拯救。
构建出一个与人类社会不同的异世界,再将这个源于想象的产物通过一两个小时时长的电影表现出来,绝非只靠灵光一现就能够做到。构建这样的世界,既需要对人类社会的规则有深刻理解,还要能够对其进行变换,使之适用于各种不同的虚构环境之中。作为科幻作品,异世界中的运行规则又不能有过于明显的科学错误。
 融合科学与想象
融合科学与想象
如果说通过20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电影,卡梅隆已经与同时代的科幻作家们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那么在2009年上映的《阿凡达》则表明卡梅隆已经超越了同时代的科幻作家。这样一部史诗级的,充满人文主义色彩,想象力充沛,大胆运用新技术展现全新视觉效果的科幻电影,能够在全世界都引起轰动,正是基于卡梅隆所构建了一个复杂完整,而又合乎科学和逻辑,可以自圆其说的异世界——潘多拉星球。
把科学,科幻和奇幻等元素巧妙地结合在一起,需要对科学和科幻的深入理解和区分。例如电影《阿凡达》中潘多拉星球的山峰悬浮在空中,初看上去没有科学依据而显得荒谬,实际上这不仅符合电影故事的设定,也符合科学理论。根据描述,潘多拉星球的山峰富含常温超导材料,使它能够通过磁场作用实现悬浮。
电影名称“Avatar”本身就有“化身”“分身”的意思。不去考虑其中的宗教意味,电影男主角本是一个瘫痪的人类,却通过科学手段,进入到“Avatar”,拥有了在另外一个星球上的一个全新的身份,这个理念实际上与物理学的“多重宇宙”概念有相通之处。一个人何以在此时此地成为当下的自己?人有没有可能在不同的宇宙中拥有不同的身份和命运?这不仅是一个哲学命题,也是理论物理学家们热衷于讨论的话题之一。一个双腿残疾的地球人和一个强悍的、长着尾巴、一身蓝皮肤的那威人之间,彼此的命运可能相互联结。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个灵魂拥有的两个“Avatar”,这正是一位科幻电影导演对于多重宇宙理论的精彩演绎。
潘多拉星球的生命,与人类生命最根本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可以通过一种状似“辫子”的器官与其他生命相互联系,实现心灵的沟通。这种情节看似玄虚,实际上也有其出处。导演对此并未掩饰,所谓那威星人崇拜的大地之母“爱娃”(Eywa),正是源于曾经流行一时的“盖娅假说”(Gaia hypothesis)。英国科学家詹姆斯·洛夫洛克在1972年提出了这个假说,认为地球表面的生命彼此相联,形成了一个相互调节的有机整体,因此地球的整个表面可以被称为“盖娅”,可以被视为一个有机的生命体。
盖娅假说固然新奇,容易引人遐想,但其科学意义尚不明朗,也还难以找到太多的科学证据。尽管如此,这个假说已经为科幻作家们提供了大量的灵感,卡梅隆也把它应用到电影中,成为自己所构造的世界的一部分。生命的对抗与统一、意识的融合,都通过一个外星生命独有的类似于辫子的特殊器官展现了出来。
看上去与人类社会似是而非,拥有独特的魅力和无限延展的可能,这正是科幻作品,乃至魔幻作品最吸引人之处。在告别了19世纪由机械和古典物理学所支配的社会,摆脱了20世纪初期对于浩瀚宇宙无边无际的单调想象之后,21世纪的科幻作品开始更多与所谓魔幻相结合,创造出独立于人类社会,拥有自身结构和规则的异世界。这正是《指环王》《哈利·波特》与《阿凡达》之类的作品在全世界范围受到欢迎的关键所在。相比之下《阿凡达》又有着更为坚实的科学基础和更丰富的科幻成分。 人类文明恐怖电影科学科幻武打片深渊电影剧情片美国电影科幻片卡梅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