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神的黄昏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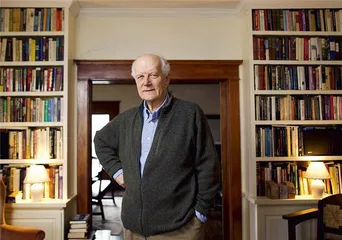 文/维舟
文/维舟
挑战旧秩序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还未散尽,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写下了小说《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他在后记中的叹息,证明那个世界还在继续崩塌:“……我们这些老人却来自于旧时代,那些曾被我们高度认同的世界观如今却成了可笑荒唐的昨日黄花。时代惊人地变快了,更年轻的人们不再以年龄段、时代或至少5年期来计量时间,而是以每一年,所以相信1903年的人与相信1904年的人已经有代沟了。一切都变得可疑,令人不安,甚至常常让人惊恐。”
对经历了战前那段漫长黄金时代的人们来说,这的确是一个令人幻灭、悲哀而惊恐的年代。通往非理性世界的入口已经洞开,世人拥挤在一起,在全身激情的驱使之下,以致命的加速度向那个辉煌的毁灭终点直冲过去。虽然后来的“二战”更惨烈、破坏性更大,但至少对那一代欧洲人来说,“一战”所带来的精神创伤却更为深远——长久宁静之后的破坏让人难以接受,相比起来,破坏之后的再度破坏反倒麻木了。“二战”爆发时尽管政客们摇唇鼓舌,但各国民众的反应都很冷淡,这与“一战”时截然不同:很多小伙子是手捧着欢送人群的鲜花上战场的,仿佛自己迎接的是一场战争形式的狂欢。
这暗示着,人们其实是期待这场世界大战的。这倒不是因为愚蠢,而是说他们在内心深处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期待,希望在一场最后的对抗中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那不仅将是“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还将带来变革。因为战前那漫长的和平年代尽管宁静,但由于它在社会快速变化时并不伴随着结构性的调整,因而已经让很多人日益感到沉闷而不满。事实上,战后人们之所以出现严重的幻灭,既是因为造成的破坏之大远超想象,但也更因为预料中的改变都没有发生:世界大战所造成的问题远比它解决的多,甚至根本没解决问题,死了几百万人,却只不过让战线来回移动了几千米,没有什么比这更荒诞的了。如果说战争是“以其他方式进行的政治”,那么现在第一次证明,它不是一种好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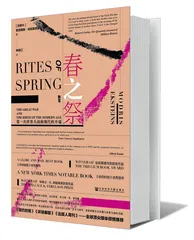 这在战前是极少人知晓的。关于这场战争爆发的原因,100年来始终争论不休,很多人谴责当时那些颟顸的政治家和将领,他们几乎像“梦游者”一样一头栽进这场可怕的战争;但更确切地说,这既低估了他们的智商,也高估了他们的能力:如果不是因为冲突各国的人们早已在本能地躁动,单凭他们也无法驱使数千万人相互屠杀。正因此,《春之祭》从文化史的角度给出了一个不同的解释:那场战争本质上是一场对旧秩序的宏大反叛,而这种普遍的内在冲动早已在人们的意识深处燃起。
这在战前是极少人知晓的。关于这场战争爆发的原因,100年来始终争论不休,很多人谴责当时那些颟顸的政治家和将领,他们几乎像“梦游者”一样一头栽进这场可怕的战争;但更确切地说,这既低估了他们的智商,也高估了他们的能力:如果不是因为冲突各国的人们早已在本能地躁动,单凭他们也无法驱使数千万人相互屠杀。正因此,《春之祭》从文化史的角度给出了一个不同的解释:那场战争本质上是一场对旧秩序的宏大反叛,而这种普遍的内在冲动早已在人们的意识深处燃起。
到1900年前后,正如英国地理学者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中所言,大航海时代结束了,那个曾经在发现的眼睛之前不断敞开的世界,在经历数百年后都已被发现无余,也都各有其主,世界开始封闭了。对西方人(尤其是德国人)来说,他们面临的是一个稳定固化的权力结构,一个无法再增长、开拓的世界。对后来者而言,这是无法忍受的,既然不能再开辟新世界,那就要对已知的旧世界重新分配。这样,世界在封闭之后转而向内坍塌。
简单地说,战前的和平长久以来依靠英国这个最主要的保守势力维持,它不仅在国际结构中占据了最大利益,还自视为进步与自由的象征;而对新兴的德国来说,英国所代表的却是资产阶级的虚伪,还压制着德国本应得到的利益。那句“我们也要有太阳底下的地盘”就赤裸裸地代表了当时德国那种不可掩饰的野心。战争的爆发也意味着旧秩序既不愿让步,新兴力量又无法得到满足,那么随之而来的便是通过战争来做剧烈的调整。英国诗人叶芝的诗很好地描述了这一幕:“事物崩解,中心不稳。”
诸神的末日之战
变革、反叛、野心、躁动、破坏、咄咄逼人的侵略性与活力、解放,在此仅是同一事物的不同侧面,被压抑的能量最终以战争的形式释放出来。然而,这种反叛的力量太强,释放时又不守任何既定规则,以至于它的破坏性远远超过了创造性。《春之祭》作为一部芭蕾舞剧之所以成为这种精神最好的象征,就是因为这种冲动的自毁性倾向:人们在追逐自由的过程中获得了终极的毁灭性力量。
毫无疑问,这是一部德国视角的文化史,不说别的,单是这种从文化角度来看待战争冲突的想法就非常德国。可以说,“一战”本身就是一场“文化”对“文明”的战争:保守倾向的英法所讲究的是从市民社会发展而来的“文明”(Civilization),但在反叛者看来,在戴着谦恭有礼和尊重国际法的虚伪面具下,仍是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而德国所推崇的“文化”(Kultur)则更偏向精神、道德与意志,按斯宾格勒的观点,那是生命进程或历史的基本现象,所有历史的文化象征都暗示着生命的形而上奥秘——这种带有神秘倾向的内在冲动,在英国的“文明人”看来则是非理性的、不守文明规范的。
在打响第一枪之前,人们在精神上早已处于交战状态。正如书中所说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中产阶级主要是从精神和道德的角度去理解愉悦,感官的满足不仅可疑,而且充满罪孽;与此恰成对比的,德国文化却推崇纯粹的激情和张扬的意志,强调满足自我,刷新体验。法国哲学家丹纳在1867年就曾表示:“德国人是现代精神的发起者,或许还是现代精神的导师。”但不受约束的现代精神所首先表现出来的却是它的破坏力。
这也可以让我们理解,这场致命的矛盾冲突,既是理念的分歧,也有审美的原因:英国人更多的是从“文明”和道德的标准来衡量他人,对他们而言世界就可分为“文明”与“野蛮”两部分,就像板球场上也可以根据行为举止迅速分出守规则的“绅士”和不守规则的“恶棍”两种人。从德国人的视角来说,他们却是从一种感性的、审美的、直觉的视角来看待对手,他们讨厌对方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就只是因为厌恶他们的做派、腔调。正因此,当时普遍将战争与解放、自由联系起来,诸如战争意味着“摆脱资产阶级的狭隘与琐碎”这种说法在当时十分盛行。
战争爆发之际,德国人享受着那种激情驱使之下的狂喜,感觉超越了庸常的日常生活,却很少去理性地考虑战争的后果。战争变成了一出宏大的歌剧,在抽象的审美体验中,人们感受到那种狂喜与悲哀,欣赏着诸神的末日之战。瓦格纳的歌剧成为德国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并不是偶然的:它就是德国现代精神的体现,一种不可抑制的内心超越;但这就好像过山车所带来的惊险刺激,只有在它安全的前提下才是美好的,一旦脱轨就变成了事故与不折不扣的悲剧。从这一意义上说,当时的德国人过度追求超越现实,以至于将那当成了现实本身。当他们纵身一跃进入战争去体验那种感觉时,却忘了绑上安全带。
毫无疑问,从理解德国文化精神的角度来说,这是一部杰作。在很大程度上,它也深受德国历史哲学的影响,带有浓厚的德国文化气息,那种从绘画、舞蹈等艺术类型切入来洞察时代精神变迁的手法,与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如出一辙,也势必像前者一样饱受争议。不过显然,作者对“德国文化”也有其相对狭隘的界定——例如马克思主义这个同样主张斗争与解放的德国思潮,就并未包括在他的分析之中。对于政治人物那种诸如“维护德国人的感情”“出于责任和荣誉”之类的说辞,他似乎也并未加以怀疑。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本《春之祭》本身的书写就像是沉醉在对复原那段历史的审美体验之中,那与其说是一段历史,不如说是一部歌剧。 埃克斯坦斯春之祭军事历史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