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现代哈姆雷特的睡眠七问
作者:鲁伊 “To be,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
“To be,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
几天前,送儿子上学后回家的路上,哈欠连天的我和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一样,陷入了摇摆不定的沉思。
不过,那位威腾堡大学的哲学系肄业生纠结的,是“究竟要忍受这强暴的命运的矢石,还是要拔剑和这滔天的恨事拼命相斗,才是英雄气概?”
而作为一名左手带娃右手写稿的中年妇女,我所犯难的,却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到底应该师法巴尔扎克和丘吉尔,还是选择瓦格纳和雨果的创作道路?
换言之,灌一大杯意式浓缩咖啡顶着困劲儿去图书馆看书写字,还是滚回家补觉等待灵感从梦中降临。
不能与不为
这事儿的前因,自然是我头天晚上没睡好。
虽然上床的时间并不迟,选择的几本睡前读物——《我们为什么要睡觉?关于睡眠与梦的新科学》(Why We Sleep: The New Science of Sleep and Dream)、《牛津通识读本:睡眠》(Sleep: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和《狂野之夜:驯服睡眠如何制造了我们不安的世界》(Wild Nights: How Taming Sleep Created Our Restless World)——无论是主旨还是内容也都足够催眠。但不知何故,各种杂念纷至沓来,总之折腾到两三点钟,才开始睡意萌生。
就在蒙眬之际,门外传来光脚丫啪嗒啪嗒跑近的声音,随即被子掀开,伴着一股冷风,钻进来一个穿着连体兔子睡衣的毛茸茸软乎乎的身体:“妈妈,迈克尔·乔丹和流川枫来找我一起跟外星人比赛,咯咯咯,Slam Dunk!……”
少年人刚开始发育的长手长脚在床上摆出个潇洒的扣篮姿势,立时占据了3/4的空间。还未等我想好该怎样有礼有节地抗议,那边厢已经呈现出刚刚在书里读到的进入慢波睡眠(Slow-Wave Sleep)的一系列典型特征:搭在我胸口上的手臂还挺有劲儿,肌肉没有完全放松,透过窗帘的晨曦微光下,阖紧的眼皮也没有显示出眼球转动的迹象……
我抓着一角被子,一边努力不被挤下床,一边开始理论联系实际:书上说了,与身体发育和修复相关的生长激素,主要在这个也被称为深度睡眠的阶段分泌;书上还说,这个阶段,前额叶皮质向颞叶和海马体传送信息,对记忆力的巩固至关重要;书上也说,人在这一阶段很难被唤醒,而一旦被强行唤醒,他们当时的火会很大,第二天还会感觉很累。
但所有这些关于睡眠问题的最新权威著作全都没说:当一个人试图进入这一阶段的意愿与另一个人停留于这一阶段的事实发生冲突时,到底该怎么办?
我最后的答案,来自哈姆雷特深得功利主义三昧的名句:
让那负伤的鹿去垂泪,
没受伤的鹿去游嬉;
因为有的醒着,有的睡,
世界就这样的逝去。
感性与理性
然而,我也并非真的全然高尚无私。
感谢家人的支持和我的自由职业,一个令人安慰的事实是,通常只要挺过了早上儿子上学前的兵荒马乱,那么直到下午3点钟放学前的5个半小时,理论上都属于我的任意支配时间。我可以选择去做或不做什么事情,看书写字或埋头补觉都随自己的安排——自然,前提是填满冰箱、清空洗衣篮、刷马桶倒垃圾、清理书本玩具、修剪花园草木、给汽车加油保养维护这些庸常琐碎重复但没人干绝对不行的家务事,还没有把血槽蓝槽耗干。
 这肯定不能和自己二十出头时背个包满天飞做采访、前半夜赶稿后半夜刷副本、然后猛睡两天就满血复活的洒脱相比,但与众多一样被职业家庭的双重期待与责任裹挟撕扯却无从选择的同龄人相比,运气实在已经相当不错。更何况,就像多年前李宗盛唱过的,所有的这些人到中年的烦,都要算是甘心而甜蜜的负担。
这肯定不能和自己二十出头时背个包满天飞做采访、前半夜赶稿后半夜刷副本、然后猛睡两天就满血复活的洒脱相比,但与众多一样被职业家庭的双重期待与责任裹挟撕扯却无从选择的同龄人相比,运气实在已经相当不错。更何况,就像多年前李宗盛唱过的,所有的这些人到中年的烦,都要算是甘心而甜蜜的负担。
但这么宝贵的自由时间,用来睡觉不浪费吗?哈姆雷特说什么来着?
“一个人只知饱食酣睡无所事事,这算是一个人吗?畜类而已。上帝造人,使我们有这样广大的智力,能够瞻前顾后,当然他决不能赋予我们神圣的理性而又霉着不用。”
要知道,从文艺复兴时起,在崇尚理性、关注此世的西方文化里,睡眠的地位就在逐渐被贬低。为什么不呢?反正“黄泉之下,有的是机会补觉”——这可是文艺复兴人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言。
但与此同时,对于正在写一篇与睡眠有关的文章、读了一大堆最新研究著作的我来说,睡,或者不睡,又不仅是在感性和理性之间选择哪一个的问题,还是在两种理性选择之间做出功利判断:
到底哪一种选择,会让此时此刻此地的我,感觉最幸福?
 失眠的荣光
失眠的荣光
毫无疑问,像巴尔扎克这样每天喝50杯咖啡甚至生吞咖啡粉来保证从午夜到凌晨可以一直处于“灵感纷至沓来,就像一支声势浩大的军队前往传奇的战场,战斗正酣”创作状态的高产大作家,是我等写作者的光辉榜样。
当然,巴尔扎克只活了51岁就死于心脏衰竭,临终前双目近乎失明,这可能让已过不惑之年、重度近视的我学起来有点心惊胆战。但幸好还有拿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丘吉尔在。根据《蒙哥马利元帅回忆录》里的记载,某次二人会面,军旅出身的蒙哥马利吹嘘说:“俺既不抽烟也不喝酒,还黎明即起,所以身体百分之一百健康。”然而前著名记者丘吉尔就直接怼回去,“咱可是好酒贪杯,能不睡觉就不睡觉,雪茄也一根接一根地抽。大概就是因为这样,我才能总是百分之二百健康吧!”
至少从寿命这一指标来看,丘吉尔还真不是吹。百分之一百健康的蒙哥马利活了88岁,百分之二百健康的丘吉尔,终年90岁。
甚至在睡眠的功用和缺乏睡眠的危害逐渐广为人知、与助眠相关的药物、疗法、商品开始成为一个蓬勃兴起产业的1978年,在理查德·特鲁博(Richard Trubo)撰写的科普畅销书《如何获得一夜安眠》(How to Get a Good Night's Sleep)里,他还特意提醒人们去思考一下失眠的“优点”——“比如,你的伴侣或老板会不会因为你连续几星期甚至几个月没睡好就对你的过错更有耐心呢?”他引述美国精神健康研究所心理学家朱利叶斯·西格尔(Julius Segal)的话说:“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带着一点胜利者的荣耀看待自己的睡眠不足。对这些人来说,不睡觉业已成为某种地位符号。他们会说,如果你真诚地对待生命,恰如其分地为生活担忧,那么就必然会被失眠所困扰。这是成功的徽章——就像胃溃疡或心脏病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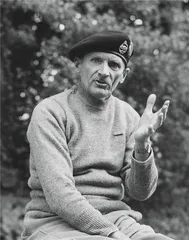 梦中的灵感
梦中的灵感
虽然上面的这些声音至今仍能从各种地方听见,但相对于近年来高扬着科学的战旗、唱得越来越响亮的睡眠颂歌来说,它们无疑在变得不主流、不动听——至少,不够炫酷。
比如,在哈佛大学的斯蒂芬·洛克利(Steven Lockley)和牛津大学的拉塞尔·福斯特(Russell Foster)共同撰写的《牛津通识读本:睡眠》中,两位睡眠神经学权威就提醒我,史蒂文森是在睡梦中得到《化身博士》的灵感,柯勒律治的名作《忽必烈汗》也是在睡梦中吟出,瓦格纳则作曲时一旦思路不畅就上床大睡,并且把梦境作为歌剧的主题。这么一说,我也顺便想起,和巴尔扎克生活在同一时代,也差不多同样著作等身的雨果,不就是大名鼎鼎的赖床贪睡鬼吗?
很显然,是不睡觉才成就了巴尔扎克、丘吉尔和某成功人士,还是因为他们是巴尔扎克、丘吉尔和某成功人士才可以如此挥霍自己的身体,其间的因果关系,没那么容易分辨。细打起算盘来,这年头,咖啡、雪茄、葡萄酒都不是什么便宜东西,效仿巴尔扎克和丘吉尔不成,没写出《人间喜剧》和《世界危机》,倒搞出财政危机酿成家庭悲剧,用功利主义追求幸福最大化的标准衡量,实在不划算。反倒是理论上无需借助外物、自然而然的睡眠,用两位科学家的话来说,已经有大量坚实的科学证据表明,“不但可以让我们感觉良好,还有助于大脑找到解决日常问题的创造性答案”。
为了幸福,睡眠需要被拯救。于是,它在舆论上得到了拯救。
然而,和我一样因为受了点教育读了几本书就爱凡事思考不休的哈姆雷特,又开始在脑海里念念叨叨了:
“阖眼一睡,若是就能完结心头的苦痛和肉体承受的万千惊扰——那真是我们要去虔求的愿望。”
生活在七天24小时都可以是工作日的全球化时代,面对着与全球生产过剩、贫富差距激增并生的注意力经济和消费主义文化,被现代交通和通信工具赋予了几个小时内转换昼夜寒暑、在卧室里动动手指即可知天下新鲜事的神奇能力的我们,即便正值盛年,身体健康,但要想实现科学——以及基于科学而生的各种鸡血鸡汤——所承诺的那种高效率的理想睡眠,又谈何容易?
 多少算够?
多少算够?
好吧,睡眠很重要。阖眼睡去的这8个小时,和一天中余下的那16个小时一样,值得我们严肃理性地对待。
且慢——8小时?为什么不是9小时、10小时?为什么不是6小时、7小时?
按照《牛津通识读本:睡眠》中的说法,工业革命前的人类睡眠时间长达10小时。有些强调睡眠修复能力的保健自助书籍因此认为,这是古代人不得癌症不被心脏病困扰的关键。不过,这却被近年来多项关于睡眠时间超过9小时的人群反而死亡率更高的研究打脸。
与此同时,按照本杰明·赖斯(Benjamin Reiss)在《狂野之夜》一书中对睡眠进行的历史学和人类学考据,8小时睡眠和8小时工作制一样,是工业革命的产物,绝非必要和必然。被他引用的一项针对坦桑尼亚、纳米比亚、玻利维亚现代狩猎采集部落的研究表明,虽然缺乏电力照明,只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这些部落成员的平均夏季睡眠时间仅有6小时,冬天也只有7.2小时,而且并没有出现肥胖、糖尿病和情绪紊乱等被认为与睡眠缺乏相关的健康问题。
这很重要——因为前几年流行的“一万小时定律”宣称,10000小时的锤炼是任何人从平凡变成世界级大师的必要条件。假如六七个小时的优质睡眠就可以满足为身心充电的需求,一个老老实实睡足8小时的人,和与他同样努力但睡得少的人比起来,算不算“输在了起跑线”?
然而,在2017年出版后即高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和亚马逊健康类书籍榜首的《我们为什么要睡觉?》一书中,美国睡眠学界的当红炸子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神经心理学教授马修·沃克(Matthew Walker)却对这种解读大加抨击。他说,睡眠机会时间(Sleep Opportunity Time)和睡眠时间(Sleep Time)是两回事,这些部落居民留给自己的睡眠机会时间与睡眠学界的推荐标准——7到9小时——几乎一致,而现代人的问题是常常只给自己留5到6.5小时的睡眠机会时间。最关键的是,这帮人的平均寿命只有58岁,而且虽然运动量大、体形健美,成年人的肠道感染致死率却相当高,而这与严重缺觉的实验室小鼠免疫系统受损、更易死于肠道感染的研究结果很可能并非出于巧合。
那就还是老老实实地给自己留8小时睡觉?“我宁可忍受现有的苦痛,而不敢轻易尝试那不可知的苦痛”——毕竟,我们对同一时代身边人的生活与苦痛,都所知甚少,古典生活和部落生活的莫须有的美好,还是留给古装剧和穿越文吧。
深浅几何?
同是睡眠,此一时,彼一时,又还有区别。
我儿子戴的运动手环,除了可以监测睡眠时间,还能在小程序上显示睡眠状态:浅紫色的是“浅睡眠”,深紫色的是“深睡眠”,橘黄色的是中间醒来的时间。
对于擅长临时抱佛脚、把NREM、REM、SWS、WMZ这些术语背得滚瓜烂熟的我来说,除了那条橘黄色的线的确记录下我被夜袭的精确时刻之外,这一套,不过是糊弄小孩的野狐禅。
然而小孩子的确很把这一套当真。早上看到自己前一晚“深睡眠”时间比平常多了20分钟,就会做出一个“今天也是元气满满的一天”的可爱表情,蹦蹦跳跳地上学去。偶尔发现低于平均水平,则刚吃完晚饭就会很乖地表示,昨天他没睡好,今晚就别学中文早点睡觉吧。
我有必要告诉他,学术定义上的深睡眠(Deep Sleep),不过是非快速眼动睡眠(NREM)中的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虽然很重要,但有研究表明,可能并不像占据睡眠时间20%到25%的快速眼动睡眠(REM)那样生死攸关吗?
在《我们为什么要睡觉?》一书中,沃克引述了一项芝加哥大学研究小组发表于1983年的研究:当实验室大鼠被有选择地剥夺了REM睡眠时,它们会和那些完全没有觉可睡的大鼠一样在十几天内迅速死去,但如果仅仅是NREM睡眠被破坏,则受影响的大鼠虽然会出现皮肤溃烂、暴饮暴食却体重降低等一系列负面症状,但却仍能苟延残喘至45日之久。
然而,看完相关的研究论文,我反而开始担心,就像此前剑桥大学心理学系研究社会道德标准依从、身心健康、利他主义和快乐的讲师亚历山大·科甘(Aleksandr Kogan),其研究结果和调查工具反而帮助了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在Facebook上猎取个人隐私、散布假消息、左右选举舆情,这些针对睡眠的研究——尤其是心理学研究——真的能够为我们这些一知半解的知道分子造福,而不会被有能力获取更多专业知识但可能别有意图的利益集团利用吗?
这种阴谋论的念头不能多转,否则,它会让电子屏幕、蓝光LED灯、咖啡因饮料和酒精饮品摧毁睡眠的杀伤力变得比实际上更惊人。
但不管怎样,世间万事,都是破坏简单,重建繁复,知而不能行比比皆是,锦上添花难上加难。更何况,没有浅,何来深,一个晚上,人的睡眠会在NREM和REM之间经历几次周期循环,正如沃克自己也承认的,其中的进化原因,科学家至今也只能说是略窥门径——说不定,这一设计,一是为了不让任何一个阶段因为意外的晚睡早起而蒙受太大损失,二也是不给出于人的功利对其动手动脚的企图有移花接木的机会吧。
套用一句哈姆雷特对知交何瑞修说的话,这或许就是“宇宙间无奇不有,不是你的科学全能梦想得到的”?
孰害孰利?
其实,所有这一切纠结,都源于一个半吊子法学院毕业生在价值观习得过程中被启蒙恩师烙入思想深处的功利主义。
出于功利,当认为睡眠是一种不作为、一种时间浪费时,追求理性的我尽可能地去压缩它、舍弃它。
也是出于功利,当汲汲于自我价值实现的我发现,在入睡后的无意识状态中,身心都在进行着一系列至今仍未被科学界完全认识的奇妙工作,而可以有效地破坏睡眠的现代发明比比皆是、能够对缺失的高质量睡眠加以弥补的手段却寥寥无几且代价高昂时,又开始想方设法地压榨它、利用它。
然而,一个最明显但却常常在关于睡眠的热烈讨论中缺失的事实是,无论在什么时代、替代人力的智能技术发展到何种程度,都总有人渴睡、能睡却无法去睡。哈姆雷特时代的守城小兵和掘墓人,工业革命时代的纺织工和钢铁工,现代社会的警察、护士、急救医生、航空交通管制员以及林林总总的夜班工作者,这其中自然也包括我的需要周期性熬夜发稿出刊的新旧媒体同事。
可是,在功利主义的自我为理想睡眠和幸福人生设定欲望投射对象时,仍生活在时间之中的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地便锚定了巴尔扎克、丘吉尔、瓦格纳和雨果这样天分、努力和运气都经受住了历史考验的大人物——甚至连纠结,也仿佛只有哈姆雷特的纠结才值得师法比照。
这样做的危险,是容易忘记,对于我们的生存状况,对于我们追求的幸福和追求幸福的我们,个体所能施加的控制,其实极为有限,而一种过于激进的对结果平等和个人自由的追求,很容易便会成为集体主义暴政的引路人。
说到底,既然幸福的本源是参差多态,而人所追求的幸福不同于猪所追求的幸福,我们的功利主义不可避免地带来冲突——不仅是同他人的冲突,也是同自我的冲突。
正是这种冲突,让身为王子的哈姆雷特觉得,这世界不过是很宽绰的一个监牢,他的家国是其中最坏的一间,也让我们有时候竟会在几乎满足一切有助安眠外部条件的卧室里,辗转反侧。
于是,那一天,我没有选择回家补觉,而是去了学校的大图书馆。说来也是无心插柳,找资料的时候,随手从书架上抽出摆在旁边的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1958年出版的讽刺寓言著作《精英阶层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忍着一跳一跳的头痛看完,一本看似和睡眠八竿子打不着、使用搜索引擎绝对不可能出现在结果之中的书,却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所谓睡眠危机,有着惊人精辟的锐见。
而在那天晚上,我把一堆关于睡眠的专业著作请出了卧室,在Kindle上下了几本密尔、边沁之外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和20年前一样,康德永远不会令人失望——至少对我来说,从来就没有30页《纯粹理性批判》治不好的失眠。
(本文中引用的《哈姆雷特》为梁实秋译本。谨以此文怀念20年前教我读书的沈叔平老师) 梦深睡眠和浅睡眠睡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