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检到尹嘉铨
作者:卜键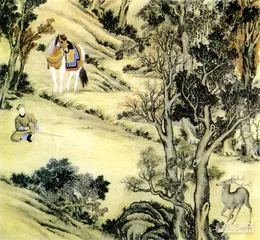 父子相接,仕宦传承,在历代官场皆属常见,至乾隆中期变得更为突出。究其原因,一则是承平日久,社会阶层相对固化;一则是弘历格外看重世谊,一旦发现故臣之子可能有出息,即会刻意培养。本节写到的两位,都属于世臣。
父子相接,仕宦传承,在历代官场皆属常见,至乾隆中期变得更为突出。究其原因,一则是承平日久,社会阶层相对固化;一则是弘历格外看重世谊,一旦发现故臣之子可能有出息,即会刻意培养。本节写到的两位,都属于世臣。黄检出身汉军镶红旗,有云骑尉世职,曾祖黄秉中仕至福建巡抚,祖父黄廷桂深得乾隆帝器重,历任两江总督、陕甘总督、四川总督,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加太子太保,封三等忠勤伯,卒谥“文襄”。弘历曾赋怀旧诗《五督臣》,以黄廷桂列在首位。廷桂仅一子先卒,三个孙子中以黄检最为干练,三十八年十二月的戎英献书案,就是交给他查办的。那时的黄检身任山西按察使,仅一年多就升为布政使,四十三年七月调福建布政使,甫一抵任又升福建巡抚。黄检生于乾隆四年,监生,捐纳同知,先在广西任职,三十三年春升山东省东昌知府,进京引见,得到乾隆的赏识,在其履历单上朱批:“黄廷桂之孙,竟可出息。年尚少,不宜骤用。”而有了皇上这句话,黄检仅十年就升至巡抚,不可谓不骤。福建因海岸线较长,又有管辖台湾之责,一向简任能员,选中了不到40岁的黄检,亦能见出皇上的信赖期待,没想到几个月后就出事了——
还记得前面写过的太监高云从案吧,只因兵部侍郎高朴一段含含糊糊的面奏,高云从被处死,枢阁重臣于敏中、舒赫德被处分,一批卿贰大臣被降革。弘历的复杂帝王心态也由此显现:接见臣子时希望得到一些信息,可又从心底看不上告密者,是以对“小人多事”的高朴并未重用。不久后高朴在叶尔羌盗挖倒卖玉石案发,弘历即命审明处死,同时传谕查抄其在京师的家,未料竟抄出一套《黄廷桂奏疏》来。此乃这位已故重臣在职期间的奏折,涉及朝廷机密甚多,还包括雍正、乾隆一些不宜公开的朱批,皆予刊印。弘历“深为骇异”,翻阅了一遍,又让军机大臣与原档核对,发现凡属嘉奖类文字皆保存,对那些训饬的话就删去了,随即降谕:
因思皇考朱批,久经钦定选择刊行;而朕临御后朱批之折,从未选刻,岂臣下所得私镌?况朕向曾降旨,凡臣工奏折奉有朱批者,概不准其引入章疏,所谓“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理应如是。则凡朱批事件,更非臣下所宜宣露。且其所刊多系嘉奖之语,其或奉有训饬,即未载入,尤为失实。……自系黄检逞其高兴之见,专务虚名,而不度事理,辄为刊刻。不意黄检荒唐,竟至于此!
文中也说到一个朝廷的规矩:如雍正朱批奏折已经整理刊行,臣子不得妄自加减;而乾隆朱批未经编发,臣子即便想要刻印,也必须经过批准,岂可擅自刻印送人!
弘历说父皇与自己重用黄廷桂,皆因其有办事之才,足任封疆,并非因章奏写得好,在其身后给予世袭伯爵,加恩于黄廷桂不为不厚;也说自己本希望黄检能有出息,看来也沾染了“汉人好名恶习”。就这样,黄检被解职,命来京候旨,“其所有板片及刷存之本,或已经分送者,并著即行查明解京销毁”。同时谕令“各省督抚,详悉晓谕确查,如大臣家有似此曾经镌刻者,即令其子孙将板片书本一并缴出,奏闻送京查销”。一场动作不算太小的清查开始了:军机处以六百里急递向黄检转达上谕,要求奏明该书印制和赠送详情,并将板片和余书“即速解京销毁”;以五百里急件向山西巡抚巴延三寄发谕旨,命在山西清查搜缴该书,并斥责其对此麻木不仁,视同泛常;同时传询承袭伯爵的黄廷桂曾孙黄文璟,要他交代该书的刊刻情况,孰知文璟一头雾水,诉说从未见过此书,亦不知刻于何地。黄文璟不敢怠慢,回家即向曾祖母报告,家祠中未见陈列,老太太也不知此事,只知那些奏折被叔叔回家取走了。黄检于三月初五接奉谕旨,顿时吓得屁滚尿流,承认自己一时愚昧无知,照祖父原本刻印20部,分送上司、同僚及下属。此人满脑子功利念头,刻了祖父的书,却没想到送给祖母和家人。他的哥哥黄模为镇筸总兵,辗转借得一部,“照抄二十四本”,闻知出事赶紧上缴。黄检至京后即被革职,对其家兄弟子侄未予追究。
此案一出,那些刊刻过类似奏章的官员皆有些着慌,其中有一位是原任大理寺卿尹嘉铨,赶紧将所刻乃父尹会一(曾任河南巡抚、吏部侍郎)的奏疏及板片呈出,奏请销毁。军机大臣奉旨先作审核,对不妥处各加浮签,建议“令尹嘉铨将不应刊刻各折撤去”。弘历详加批阅,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妥,认为不在应毁之列,命将原书及板片发还。此事让尹嘉铨备感鼓舞,自觉在皇上那里很有面子,接下来便惹出了大麻烦。
那是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三月,皇上返程中经过保定,尹嘉铨遣儿子到行宫迎驾,代呈二折。其一是为乃父请谥,引用弘历赐尹会一的御制诗,表示自己出于一片孝心。皇上即加批驳:“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而再看第二折,弘历更是怒不可遏,斥曰:
次阅伊为父请从祀孔庙一折,更为肆无忌惮,愚而好自用矣。从祀宫墙,非人品学问纯粹无疵、久经论定者,孰敢轻议!是以国朝从祀寥寥,宁缺无滥。今尹嘉铨乃奏请欲为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并请从祀,而厕以伊父,谬妄殊甚。……且尹嘉铨托于行孝,为此妄奏,天下之人孰非人子乎?使令皆为其父求谥、求入祀孔庙,亦可行乎?否则为不孝,即得罪仍托于为父,则朝政不至于大紊乎?
痛斥尹嘉铨丧心病狂,毫无忌惮,命革去顶带,拿交刑部治罪,同时派员到其原籍和京宅搜查抄检。
尹嘉铨的确格调不高,早在山东布政使任上,就曾借召见之机恳求赏戴花翎,并对皇上模仿其妻之言,说如果得不到赏赐,即无颜面与妻妾相见。弘历对这种毫不知耻的行径很惊讶,忆曰:“朕之深鄙其人,实从此始也,然尚欲全伊颜面,从未宣示廷臣。”而尹氏书香传家,藏书甚多,尹嘉铨又喜欢著述,连编带写整了80多种,抄家时成为一大罪过。此类审查一般由军机大臣负责,从四库馆臣中挑选踏实细心者审读,发现不少犯忌文字,如称大学士为相国、对朋党乱发议论等等,最为严重的,应是当今圣上70岁之后自称“古稀天子”,御制《古稀说》颁示中外,而尹嘉铨竟也大胆自号“古稀老人”。此类文字审核历来是宁严毋宽的,有点儿上纲上线、鸡蛋里挑骨头的意思,将加恩从宽留给皇上。而弘历认为“当此光天化日之下,此种败类自断不可复留”,如此一来,老尹可就性命难保了。大学士九卿拟为凌迟之罪,皇恩浩荡,命将尹嘉铨减两等绞立决,并赦免他的家人。
对于黄检,弘历以“其罪尚不至终于废弃”,仅过几天就给了个正定知府,至十一月升直隶按察使,很快又升布政使。到底还是喜欢啊。孰知这小子又飘了,让幕友精心撰写了一道谢恩折,说什么“如天而更高,如地而弥厚”,读得皇上心头火起,又是一通臭骂,警告他“莫再高兴,勉之慎之”。 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