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险要而唯一”的关系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张怡微 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韩国作家韩江之后,在社交媒体引发了不少争议。在中国,韩国文学是较为小众的外国文学。虽然近五年,有出版公司大量引进了韩国作家的创作,真正在社交媒体破圈的作家,可能只有金爱烂和写作《82年生的金智英》的赵南柱。
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韩国作家韩江之后,在社交媒体引发了不少争议。在中国,韩国文学是较为小众的外国文学。虽然近五年,有出版公司大量引进了韩国作家的创作,真正在社交媒体破圈的作家,可能只有金爱烂和写作《82年生的金智英》的赵南柱。
若从代际来分,作家孔枝泳是“60后”,韩江、赵南柱、金息是“70后”,金爱烂、崔恩荣、郑世朗、赵海珍、金惠珍是“80后”,金草叶、赵艺恩是“90后”。因此,当我们讨论“韩国女作家群”时,其实说的未必是一代人,只是因为陌生,我们觉得她们可能在处理同一时期的素材,对韩国社会问题也有近似的感受。若要细分起来,代际之间还是有不少差别,集体阅历也并不相同。正如在国内文学界,我们也不会认为苏童、毕飞宇与陈春成、王占黑经历和书写的是同一个时代一样。
若将已经引进中国的韩国作家做最笼统的研判,出生在1980年前的作家背负着较为沉重和复杂的历史,创作的主题离不开战争与革命。例如入围2024年布克奖短名单的黄皙暎,最近有新书《日暮时分》引进中国。黄皙暎出生于1948年,和陈映真有交往,是文坛大前辈。国内较有知名度的“50后”韩国作家,是导演李沧东。引进较多作品的作家金英夏,出生于1968年。1970年生的韩江,十分关切韩国所经历的战争及创伤,她以生态女性主义的方法论实现了文学与社会科学的叙事交际。出生于1974年的金息以漫长的、严谨的注释处理了慰安妇题材的《最后一人》。到了1980年生的金爱烂的文学世界,真正对作家有强烈冲击的历史事件已是“世越号”沉船,而不是朝鲜半岛的抗日战争、冷战余烬下的朝韩对峙、韩国军队与越南战争、80年代的民主化运动,等等。金爱烂最娴熟处理的题材并非历史创伤,而是高度资本主义化的韩国在经历金融风暴之后,都市年轻人的艰难生计。值得注意的是,金爱烂的作品并不是近五年才引进的,事实上她的作品经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更迭了两个版权周期,一直反响平平。国内年轻读者对她笔下的都会生活产生共鸣,则要到后疫情时代、经济下行之后。年轻人宛若社畜一般经历着无望的职涯,亲密关系中伴随着精打细算的约会开销,功利的婚姻诉求使得沉闷的日常生活雪上加霜,原生家庭中负债的父亲、坚忍却不肯离婚的母亲,这些小说中的情节要素都让中国的年轻读者产生了复杂的自我投射。换句话说,金爱烂笔下的痛苦,是经济泡沫、财阀干政的痛苦,这与她的前辈们很不相同。韩江获奖之后,小红书上有许多年轻人说,韩江写得不如金爱烂,这就很有意思。实际上两位作家并不是同龄人,其次她们所关注的韩国也不是同一时期的韩国。她们在国际文坛的影响也并非一个量级。然而,这种评价好像代表着中国年轻读者的当下感受和审美趣味在金爱烂的创作中得到了良好的实现。 2015年至今的韩国文坛,经历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一是前辈作家申京淑的抄袭事件引发了韩国文坛文学权力的讨论。二是《82年生的金智英》横空出世,开始影响并不大,后来却引发大量话题讨论,引发了女权主义浪潮,也揭露了业界及文坛以外结构性压迫的生态,这些新闻对中国女性读者也有重要影响,协助性别教育缺失的女性慢慢产生了女性主义的觉醒。但“金智英”热亦有复杂的一面,它甚至令人对韩国文学产生了刻板印象,认为韩国当代文学就是写性别题材的、写社会问题的。其实这是很不全面的看法。在我极其有限的阅读范围内,我认为韩国作家尤其是女作家在历史、奇幻、科幻等多元题材上都有不俗的表现。很可惜她们的作品被引进中国的时候,从一开始就被出版社引导了“误读”,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就是郑世朗的《孝尽》,读过这本书的同学可以在这本小说集里看到各种题材,有类似于海漄风格的历史穿越,有鸟类、珊瑚、无国籍人、无性别人、外星人,及大量的跨国越界生活经验和跨物种恋爱体验书写,但这本书的宣传语却喊出了“中国有招娣,韩国有孝尽”的离谱口号,实际上是窄化了作者的写作企图。另一方面,韩国与日本都有和中国完全不同的新人培育路径,分门别类、竞争激烈。几乎所有说得上名字的作家,都有十几个文学奖傍身,一步一脚印获得体制和市场的认可。很少有人能只写性别题材就获得肯定,许多年轻作者都是什么题材都写,有些作家如崔恩荣,也写过婚恋和男女冲突,但后来很快就开始写别的。用通俗的话来说,是卷度裁决了公平与质量。
2015年至今的韩国文坛,经历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一是前辈作家申京淑的抄袭事件引发了韩国文坛文学权力的讨论。二是《82年生的金智英》横空出世,开始影响并不大,后来却引发大量话题讨论,引发了女权主义浪潮,也揭露了业界及文坛以外结构性压迫的生态,这些新闻对中国女性读者也有重要影响,协助性别教育缺失的女性慢慢产生了女性主义的觉醒。但“金智英”热亦有复杂的一面,它甚至令人对韩国文学产生了刻板印象,认为韩国当代文学就是写性别题材的、写社会问题的。其实这是很不全面的看法。在我极其有限的阅读范围内,我认为韩国作家尤其是女作家在历史、奇幻、科幻等多元题材上都有不俗的表现。很可惜她们的作品被引进中国的时候,从一开始就被出版社引导了“误读”,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就是郑世朗的《孝尽》,读过这本书的同学可以在这本小说集里看到各种题材,有类似于海漄风格的历史穿越,有鸟类、珊瑚、无国籍人、无性别人、外星人,及大量的跨国越界生活经验和跨物种恋爱体验书写,但这本书的宣传语却喊出了“中国有招娣,韩国有孝尽”的离谱口号,实际上是窄化了作者的写作企图。另一方面,韩国与日本都有和中国完全不同的新人培育路径,分门别类、竞争激烈。几乎所有说得上名字的作家,都有十几个文学奖傍身,一步一脚印获得体制和市场的认可。很少有人能只写性别题材就获得肯定,许多年轻作者都是什么题材都写,有些作家如崔恩荣,也写过婚恋和男女冲突,但后来很快就开始写别的。用通俗的话来说,是卷度裁决了公平与质量。 我并不热衷如今文学趣味的社科化转向,尽管我对社会科学非常有兴趣,参与了许多跨学科工作坊,也写了很多文章,但我的兴趣正来自于警惕和对学科边界的高敏感。我并没有在追随这股风潮,可惜即使是我的文章也会被误会我是在追随社科话题。我想,韩江的获奖似乎从某种程度上加剧了社会科学(所出具的结论)与纯文学(故事)的生硬融合,这当然是路径的一种,但不会是唯一的方向。
我并不热衷如今文学趣味的社科化转向,尽管我对社会科学非常有兴趣,参与了许多跨学科工作坊,也写了很多文章,但我的兴趣正来自于警惕和对学科边界的高敏感。我并没有在追随这股风潮,可惜即使是我的文章也会被误会我是在追随社科话题。我想,韩江的获奖似乎从某种程度上加剧了社会科学(所出具的结论)与纯文学(故事)的生硬融合,这当然是路径的一种,但不会是唯一的方向。
在与我同龄的韩国“80后”作家中,兼具历史意识又对“关系”极度敏感且能有意识摆脱社科标签,走出纯文学之路的作家是崔恩荣。我最早读到崔恩荣的作品,是在一本小说合集《给贤南哥的信》中。《给贤南哥的信》是赵南柱的作品,小说集第二篇是崔恩荣的《你的和平》,这篇作品的重要意义在于,我们可以了解到崔恩荣并非对“金智英”风格的写作不熟悉,她甚至还模仿过“金智英”。故事写的是女孩善英首次到未婚夫俊昊家做客,遇到了俊昊的姐姐宥真,对于婚恋的陷阱,宥真将心比心,对这位年轻女孩有怜惜。宥真所倚靠的传统家庭,爷爷会将太太视为奴婢。宥真的父亲出于对母亲的同情,才迫切想要找到一个奴婢继承者,也就是善英进入到家族中。小说中许多设计都有综艺般的戏剧冲突,例如明知善英不吃肉,却准备了满桌肉食。善英、宥真去往各个传统家族就只有一种命运,那就是接受被忽视、接受被奴役。通过对话,崔恩荣也展露了她的尖锐和丧气,例如小说里写“女人读到博士有什么用?都去留过学的人,怎么可能守身如玉”。崔恩荣在小说附录的“作家笔记”中,则谈得更加尖锐,她引用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的话——“父权制是爱情的反义词”,解释她创作这篇小说的动机,她写道:“我不想成为那样的人。”如果我们的阅读停留于此,会对崔恩荣的写作产生很大的误解,她的实际才能被这类素材遮蔽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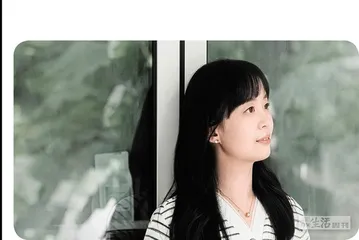 2023年,是崔恩荣作品正式引进中国的一年。我们如今可以看到小红书或豆瓣上许多人都非常喜欢她的长篇小说《明亮的夜晚》。而《对我无害之人》《即使不努力》等短篇集的引进,也令我们有机会更全面地了解崔恩荣的文学宇宙。《对我无害之人》的序言,崔恩荣对中国读者回忆了她与中国的联系。我惊喜地发现,她在2014年时居然来过我服务的单位、上海复旦大学参加学术大会,还在上海和近郊玩了几天,让我感到非常亲切。如果我们读过《即使不努力》,也会发现崔恩荣借由小说人物表达过她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她非常喜欢张曼玉,喜欢上世纪90年代的香港电影。短篇小说《德比·张》写了一名韩国女生到意大利旅行时遇到了一名中国香港男孩并产生十多年联系的故事。这位韩国女孩有多喜欢香港呢,小说里写:“第一次去香港,我坐了《重庆森林》里王菲乘坐的半山扶梯,去了《甜蜜蜜》中为纪念张曼玉和黎明的偶像邓丽君而建造的咖啡馆,还去了《花样年华》中张曼玉和梁朝伟一起吃饭的金雀餐厅,又爬了《星月童话》中出现的太平山。在太平山上,眺望香港的夜景,我想起身在某处的德比,还回想起二十出头时沉迷香港电影的年轻岁月,以及自认为在跟德比一起旅行时尚未成熟的自己。”女主人公和德比·张,是一种基于流行文化影响力联结的情愫。她看似只对个人有意义,其实这种精神影响对“关系”处境化的确认有决定性的意义。可以说,从一开始,崔恩荣就努力在韩国内外探寻着处境化的“关系”、处境化的人与人。什么是处境化的关系呢?我认为在崔恩荣的小说里,表现为一种隐微的敌对与本能的亲近之间,以叙事命名的“友谊”。
2023年,是崔恩荣作品正式引进中国的一年。我们如今可以看到小红书或豆瓣上许多人都非常喜欢她的长篇小说《明亮的夜晚》。而《对我无害之人》《即使不努力》等短篇集的引进,也令我们有机会更全面地了解崔恩荣的文学宇宙。《对我无害之人》的序言,崔恩荣对中国读者回忆了她与中国的联系。我惊喜地发现,她在2014年时居然来过我服务的单位、上海复旦大学参加学术大会,还在上海和近郊玩了几天,让我感到非常亲切。如果我们读过《即使不努力》,也会发现崔恩荣借由小说人物表达过她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她非常喜欢张曼玉,喜欢上世纪90年代的香港电影。短篇小说《德比·张》写了一名韩国女生到意大利旅行时遇到了一名中国香港男孩并产生十多年联系的故事。这位韩国女孩有多喜欢香港呢,小说里写:“第一次去香港,我坐了《重庆森林》里王菲乘坐的半山扶梯,去了《甜蜜蜜》中为纪念张曼玉和黎明的偶像邓丽君而建造的咖啡馆,还去了《花样年华》中张曼玉和梁朝伟一起吃饭的金雀餐厅,又爬了《星月童话》中出现的太平山。在太平山上,眺望香港的夜景,我想起身在某处的德比,还回想起二十出头时沉迷香港电影的年轻岁月,以及自认为在跟德比一起旅行时尚未成熟的自己。”女主人公和德比·张,是一种基于流行文化影响力联结的情愫。她看似只对个人有意义,其实这种精神影响对“关系”处境化的确认有决定性的意义。可以说,从一开始,崔恩荣就努力在韩国内外探寻着处境化的“关系”、处境化的人与人。什么是处境化的关系呢?我认为在崔恩荣的小说里,表现为一种隐微的敌对与本能的亲近之间,以叙事命名的“友谊”。
2014年,也是崔恩荣凭借中篇小说《祥子的微笑》荣获《作家世界》新人奖的时期,是她登上韩国文坛的起步,获奖作品《祥子的微笑》收入小说集《对我无害之人》中。祥子是个日本女孩,高中时通过“韩日学生文化交流”活动来到了“我”的城市,借住在“我”家。短短的一周时间,祥子和我们家建立了奇特又绵长的友谊。家里只有“我”和“外公”会说外语,我会一点英语,外公会一点日语。在祥子来家里之前,外公几乎不说话,他对家中的女眷,只会说一些命令式的日常用语,小说中写,“祥子住在我家的那一周,家里流动着怪异的活力”。一周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祥子开始给我们家写信,用英语给“我”写信,用日语给外公写信。高中毕业后,祥子的信就断了,这场断联在家庭内部激起的涟漪并不小,“每次提到日本就咬牙切齿的外公”甚至在妄想祥子能考上韩国的大学,之后要带她去济州岛游玩。多年之后,“我”才得知,祥子为了照顾爷爷放弃了早稻田大学的录取,只留在家乡的大学学习理疗。大四那年,“我”特地去日本找到了祥子家的村庄。祥子看到我时显得很疲惫,甚至有些冷淡。“我”的感受也很复杂。一方面,从高中生成长为大学毕业生的我,看起来比祥子更有光明的未来。另一方面,“我”和祥子似乎找不到一个词来定义彼此之间的友谊。回到韩国以后,“我”对外公说,没能找到祥子,外公因此也慢慢地不再去看信箱。一晃“我”忙到了30岁,在电影行业成为一个看似有梦想其实很彷徨的青年导演,对自己十分不满意且长期处于失业状态。一个雨天,外公从家乡到首尔找“我”,仅仅是为了告诉“我”,“祥子又给我们写信了”。淋雨着凉的外公那时快要走到生命尽头,这个三口之家寂寞的真相才慢慢浮出水面。“我”和家人唯一的合照还是祥子高中来家里暂住时拍下的。祥子对我们家是那么重要,怎么都挥之不去似的。“我”不知道的是,外公给祥子写过200多封信,他只告诉了这个敌对国度的忘年交朋友,他曾想当一个画家。
小说集中的另一篇故事《你好,再见》,亦是处理险峻关系的典范。故事的主人公随家人暂住德国普劳恩地区时,妈妈交了一个越南朋友阮阿姨。因为被孩子束缚在异乡的家庭生活中孤立无援,妈妈和阮阿姨越走越近。作为孩子的“我”也看出这段关系复杂的含义,因为只有在两家人聚会的时候,爸爸和妈妈才不吵架,妈妈才会笑得很好看。然而好景不长,经过两个孩子的争论,我们得知阮阿姨一家曾在越南战争中遭遇不幸,阮阿姨的家人死于韩国军人之手。更由于爸爸说了一句,自己的哥哥是雇佣兵也死于那场战争,两家人的友谊再也无法回到从前。多年后,母亲去世,“我”重返普劳恩,拜访阮阿姨,因为“我”知道,她是妈妈最喜欢甚至是一生中唯一一个好朋友。
险要而唯一,是崔恩荣命名的新型“关系”,基于人与人。人与人的背后呢,又有复杂的历史,有难以言喻的隔阂。倘若敌对是遥远的,那反而是轻松明朗的,崔恩荣偏要给出一个偶然的可能,让人照见死局一般的韩国传统家庭结构中微弱的光芒。小说中写的“怪异的活力”,就有如松本清张的名作《监视》中那位“就活了那几个小时”的绝望主妇一样,展现了人道、人性的本能,这在《即使不努力》中,表现为女性与女性之间理性难以斩断的亲近,“说想要靠近的人,其实都是她”。这样的心知肚明,到了《你好,再见》中就叠满了悬疑,让我想到金喜爱主演的电影《致允熙》,表达的主题是那么深情又那么难以启齿:那是妈妈唯一爱过的人啊,是妈妈的秘密,妈妈唯一的笑容。 我很喜欢崔恩荣为《即使不努力》扉页写下的题记:“爱并非一种需要努力找出证据的痛苦劳动。”爱的痛苦在于即使不努力,在复杂敌对的人世间,它也会自然而然地发生、自然而然地经过。这是我心中的文学性所在,它是文学本身、心灵本身,而不是去阐释社会科学的新词和结论。
我很喜欢崔恩荣为《即使不努力》扉页写下的题记:“爱并非一种需要努力找出证据的痛苦劳动。”爱的痛苦在于即使不努力,在复杂敌对的人世间,它也会自然而然地发生、自然而然地经过。这是我心中的文学性所在,它是文学本身、心灵本身,而不是去阐释社会科学的新词和结论。
(张怡微,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近年出版小说集《四合如意》《哀眠》) 韩国张怡微女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