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文学传记有意思
作者:陈以侃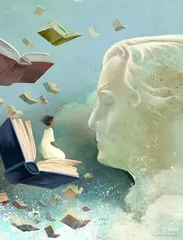 “传记是英国文学的一种病。”查这句话,出现在乔治·艾略特的书信中,但总感觉很多人都说过。其中那份厌恶太耳熟,大作家都讨厌传记。
“传记是英国文学的一种病。”查这句话,出现在乔治·艾略特的书信中,但总感觉很多人都说过。其中那份厌恶太耳熟,大作家都讨厌传记。晚年毛姆,还是住在南法那个海角上,送走最后一个客人,地中海晚风吹进他精美的宅子里,他就一夜一夜地跟秘书整理自己的私人文稿,把该烧的书信全扔进壁炉,关照遗产受托人,不许有官方传记,有人来查来问,一律轰走。心性再不同的作家们,意识形态天差地远如T.S.艾略特和乔治·奥威尔,都颁布了同样的遗训。布朗宁常做噩梦,说梦到自己家临街那面墙被剥掉,路人朝里看。更现代一些、更文雅一些的作家,像朱利安·巴恩斯,会写一部小说讲执迷于传记不可取,他说这东西就像渔网,全在你怎么看,说它是捕鱼用的网状工具,可以,说它是用线连成的空洞,也有道理。
多丽丝·莱辛1994年的自传,上来就说,一般都会问的:你怎么突然写起自传来了?回复:自卫;传记正在被写。这最后半句译得不像中国话,英文里,被动的正在进行时,are being written,句法讲究,作者要表达:写传记的,都是吸血鬼、寄生虫、盗墓贩子,心术不端,文学事上更是蠢陋,他们不配拥有姓名,在适当时候,连代词都不想分配给他们。
寻常的顾虑当然好理解,谁都有几件不愿让人知道的事情,而文人的此类指标,大概高于平均值。但在我看来,作家们如此忌惮人生被传记化,有个很讲得出口的理由:他们花了一辈子无数呕心沥血的钟点,将字词安排到尽如人意的顺序,在书页间塑造了一个他们愿意呈现给世人的自我。现在倒好,有个笔都拿不稳的雇佣文人,居然不知轻重到如此地步,敢号称要刻画一版真实的“我”,岂不荒天下之大谬,这跟打砸抢搞破坏,有什么区别?
普鲁斯特那篇有名的《驳圣伯夫》,驳的就是这个。圣伯夫是19世纪中期法国现代文学评论的奠基人,每个礼拜写一篇3000字的专栏,写了20年,他就讲究,“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觉得评判文学关键还是了解作者,普鲁斯特笑话他,说你到底懂不懂,每天吃饭抽烟坐咖啡馆的自己,跟创造艺术的自己,不是同一个人。《追忆似水年华》动笔跟写这组文章在同一年,几乎可以看作普鲁斯特的举例说明。 理查德·艾尔曼或许是20世纪业内互评打分最高的传记家,在牛津碰到晚年的奥登。大诗人训诫他,文学传记没有意义,因为它唯一的目的就是展示人生与艺术之间的关系,但这种关系要么隐晦得发现不了,要么就过于明显,根本没有必要提。艾尔曼说,他差点就要当场改过自新,但转念想,奥登自己就最八卦,“对于支撑艺术生涯的底层结构,没有人比奥登更好奇”。他写的很多诗作和散文,都是传记式的,高高兴兴示范着如何忽略自己反传记的箴言。
理查德·艾尔曼或许是20世纪业内互评打分最高的传记家,在牛津碰到晚年的奥登。大诗人训诫他,文学传记没有意义,因为它唯一的目的就是展示人生与艺术之间的关系,但这种关系要么隐晦得发现不了,要么就过于明显,根本没有必要提。艾尔曼说,他差点就要当场改过自新,但转念想,奥登自己就最八卦,“对于支撑艺术生涯的底层结构,没有人比奥登更好奇”。他写的很多诗作和散文,都是传记式的,高高兴兴示范着如何忽略自己反传记的箴言。
在文学趣味上,亨利·詹姆斯跟毛姆完全聊不到一块儿去。但大师也同样复制作家的标准动作,为了阻挠传记家,烧了大量珍贵书信,认定“一个人的抽屉和口袋不应该被翻找”。同样,他也不出所料关心作家的私事,看到传记、回忆录、书信集,两眼放光,当年跟伊迪丝·华顿自驾游法国,到了乔治·桑德的故居前,车没停稳就要去看看“她和情人们到底如何挤在如猪圈般的小屋子里”。 这样的好奇当然不只是作家才有。大肆鼓吹这种好奇之前,我要先给自己划块方便的场地,把这篇文章限制在“文学传记”的范畴之内,而且不是粗制滥造的、奥登所谓“一先令也能提供所有事实”的地摊书,而是由一个够格的写作者去呈现的另一个写作者的人生。那些在机场奔向辉煌履历,想要修习成功人士七种习惯的读者,阅读渴望同样正当,但他们或许会觉得,从一个城郊短篇小说家的人生故事中汲取智慧,效率略嫌低下。
这样的好奇当然不只是作家才有。大肆鼓吹这种好奇之前,我要先给自己划块方便的场地,把这篇文章限制在“文学传记”的范畴之内,而且不是粗制滥造的、奥登所谓“一先令也能提供所有事实”的地摊书,而是由一个够格的写作者去呈现的另一个写作者的人生。那些在机场奔向辉煌履历,想要修习成功人士七种习惯的读者,阅读渴望同样正当,但他们或许会觉得,从一个城郊短篇小说家的人生故事中汲取智慧,效率略嫌低下。
所以,我们讨论的好奇应该是延伸自“文学”那个部分,这种空口无凭的“文学性”,局促、扭捏、不知左右手该放哪里,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一直喜欢拿拉金的说法作前提,他说,一首诗写出来是干吗的?它是要读者感受到促使诗人写诗的那个冲动。对我来说,写作从来都是为了要重塑某种状态,某些能量在交汇时的停顿,生命的某处闪烁。而传记这整个工程,写传记、读传记,都是某种阅读的天然冲动,就是想要逆向把纸面上的美妙注回到一段生命中,让它变回一个穿过时间和空间的活生生的人。不用执着于文学的定义,即使把它剥除到最淳朴的状态,一个人要说对文学感兴趣,他有没有可能对文学的产生过程毫不关心?
而要捕捉这种过程,也是文学传记家格外不易的地方,他要意识到,人生与写作的转换往往不是单向的,作者的生活是他写作的一部分。这也是为什么有个传记家解释他的工作,写了一本书叫《文学传记:一门不可能的手艺》。血肉之躯,如何被物质世界和古往今来所有非物质的能量一路推搡,完成种种交易,换来一点点缥缈的艺术,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确实讲不太清楚,但传记工作者都会自带体系,他首先要有一套给自己的说法。
这也是为什么传记的历史跟我们如何看待自我很有关系。最早的传记就是流传在口头笔端的圣人伟人事迹、美德段子,往往有教育意义。到了16世纪末,蒙田发明散文的时代,大家发现用写作琢磨事情就是刻画人心,到17世纪就出现了不少法国人和英国人的回忆录、书信和文坛轶事。有人开始使用“传记”这个英文单词。18世纪是约翰逊博士的世纪,印刷和报刊写作开始普及,文人满街闲聊。约翰逊自己既是一流的传记家,也成了“古今第一传记”的主角,他和鲍斯威尔都相信,写人贵在真实,要靠各式各样的现场和细节去刻画人物。可到了维多利亚时代,帝国崛起,全民塑造光辉形象,大作家一死,经常是亲友或门徒,用三卷、五卷的大传给他们立碑,把痦子全部抹去。
战争引发新的人性和新的传记。利顿·斯特雷奇1918年写成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四名人传》,大致被认为是新传记的起点。他选取四个似乎正待被他戳破的公众人物,把他们的光环都重新解读为某种创伤和压抑,当时的影响难以估量。还有一股平行的力量更有穿透力:弗洛伊德一出来,人生都成了谜面,传记家的工作是解谜(弗洛伊德自然也是反传记的,觉得这帮人在抢他生意)。
又过半个世纪,斯特雷奇自己也成了一部重要传记的主角,迈克尔·霍尔罗伊德说他要“做一件全新的事情”,就是百无禁忌地探查性向和情爱,自此,大家对揭露式的传记胃口大增,大作家私人生活到处塌陷,正经活着都不容易,居然还能写出伟大的作品。三个狄更斯
描述风潮一定是不负责任的过度简化,每个时代都有了不起的传记被写成;但我们也看得出来,只有一点是能肯定的,那就是没有什么彻底客观和权威的传记。
“牛津通识读本”里,“传记”那一本的执笔者叫赫迈厄尼·李,牛津“人生写作”研究中心的创立者(这里面就包括书信、日记、回忆录等其他形态了),她就主张传记家应该尽量隐身,这也代表着这个行当里的名门正派。但她上来就列出写传记的十条规矩,要真实、要客观、要放到历史中,等等,但第十条是传记没有规矩。有多少种人生就有多少种传记。而且她也常说,不管传记作者再如何想把自己剔除出去,她都必然会带着自己的身份、年龄、性别、政治理念和文学趣味,而且,最好的传记,其中的动力往往是某种爱,她难以想象有人会花五年、十年,研究一个自己厌恶的对象。
我有几本最喜欢的当代书是一个作家玩味对另一个作家的迷恋,尼克尔森·贝克的《你和我》(U and I),写他如何崇拜厄普代克,杰夫·戴尔的《一怒之下》,写自己想写一部关于劳伦斯的书却写不出来。 尼克·霍恩比2022年底没来由地出了本小书,硬要把他热爱的两个人放在一起比较——Prince和狄更斯——说他们那种不可思议的高产是一种特别的天才,说他们都是不完美主义者,Prince录歌,声音出来是闷的,他无所谓,因为脑子里还有好多歌要完成;而狄更斯是可以同时连载两个长篇的人,而最后成书也不改,反正都是流传至今的名著,写累了,给自己放假,说我做一年杂志,约朋友写写稿子就好,结果杂志突然资金断了,他顺手抄起自己的一个短篇,即兴连载,扩充成了一个长篇,结果这个长篇还是《老古玩店》。文学史上的著名场面:美国读者守在码头,就为了能最先知道妮儿姑娘的生死,甚至发生踩踏,就是为了这部小说。事情据说是编的,但盛况不假。
尼克·霍恩比2022年底没来由地出了本小书,硬要把他热爱的两个人放在一起比较——Prince和狄更斯——说他们那种不可思议的高产是一种特别的天才,说他们都是不完美主义者,Prince录歌,声音出来是闷的,他无所谓,因为脑子里还有好多歌要完成;而狄更斯是可以同时连载两个长篇的人,而最后成书也不改,反正都是流传至今的名著,写累了,给自己放假,说我做一年杂志,约朋友写写稿子就好,结果杂志突然资金断了,他顺手抄起自己的一个短篇,即兴连载,扩充成了一个长篇,结果这个长篇还是《老古玩店》。文学史上的著名场面:美国读者守在码头,就为了能最先知道妮儿姑娘的生死,甚至发生踩踏,就是为了这部小说。事情据说是编的,但盛况不假。
霍恩比观察狄更斯和Prince如何写小说、做音乐、赚钱,他从中获得的鼓励、安慰和自由,完全能从他这本百来页轻巧的小书中透过来。读到霍恩比十多年前在Believer杂志的阅读札记开始,他一直是我最喜欢的读者之一,在这点上,我很认同他:不用逼自己读完一本读不下去的书,我们能从自己喜欢的东西中获得足够滋养,甚至只是看人为了自己喜欢的东西而高兴,也是很有益的。
扎迪·史密斯写了本将近500页的历史小说,是纽约时报2023年十大好书之一,叫《骗子》,讲一场1871年的遗产欺诈官司,是英国法制史上最轰动、最像狄更斯小说的案子。小说一头扎进当时的社会风气、阶级情绪、法律制度、殖民历史,直探到跟史密斯最为息息相通的牙买加身世和小说家的声名沉浮。追捧史密斯几乎整个写作生涯,新作才概括了一句话,后半句就已然透露,对我而言,小说所引发的兴趣蔓延出了小说本身。
史密斯在《纽约客》发了一篇文章,作为小说周边,题目叫《杀死狄更斯》,细讲她多年前逃离英国就是为了不像所有英国作家那样,最后去写一本历史小说,可惜功亏一篑,但最后给自己留个堡垒,说她绝不在这本维多利亚小说里那么没创意地绕回自己的文学师承狄更斯。但随着调研深入,狄更斯无处不在,最后只好由着他冲进自己的小说东奔西走,在碰到的时候像个神经病一样打招呼:Hi Charles。
第三个狄更斯是2011年一部传记中的狄更斯,作者克莱尔·托玛琳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声望的传记家之一,她写的皮普斯传、哈代传、奥斯丁传,等等,都是拿奖的畅销书。那本狄更斯出来也是狄翁两百岁献礼,书市上很是轰动。
前两本书,若是没有这第三本传记,是写不成的。霍恩比和史密斯当然熟读那本传记,张口就能引用,但我指的不是他们需要传记家提供的背景知识,才能放飞散文家、小说家的才情,也不是说这第三个狄更斯就比前两个更标准。而是说,前两位作家所感受到的那种摆脱不了的触动,来源于一个真正的人,他生命中的事件和能量如何转换成了伟大的文字,是有办法考求的。一个做学问的人,豪情壮志,签合同预支大段生命,说我准备把一个才华横溢的头脑放回它的手艺和境遇中,去弄懂它,暗示,我们为何写作、如何写作之类的问题,大概是要紧的。写传记也就象征着某种信念,追着罗兰·巴特吼他:作者没死,写作的人生一直都可以延续。传记家的三门功课
很多时候,传记卖的是分量,页数和价格都不很和蔼,怎么说通自己,这笔投资或许不亏?怎样才算一个好传记家?评判他们的手艺,最打动我的可能有这三点。
第一点,是下苦功总有种迷人的奢侈。当一个传记家坐定了,开始动笔,他很可能是在这个话题上占有材料最多的人。他的判断、他的解读未必正确,但你很难用举证来打发他的观点,因为十之八九他在这个问题上知道得比你多,想得比你久。传记家这种“我已经花了足够长的时间把该看的东西都看过一遍”的笃定,会从行文中散发出一股暖融融的可托付之感。
赫迈厄尼·李写过薇拉·凯瑟、伊迪丝·华顿、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对我来说尤为亲切的是她最近的作品《汤姆·斯托帕德传》和1996年出版的《伍尔芙传》。她写伍尔芙是分主题来写的,战争、阅读、布鲁姆斯伯里、她住过的房子,等等。后来读到李教授的工作法颇为震撼,她说自己调研开头几个月全用来制作详细的日程表,填好伍尔芙每天去过哪里、见过谁、写了什么、想了什么,她觉得自己也是疯了,因为类似的年表早有人做过,但“我必须自己去做,后来发现是必要的”。李说,她想到分主题去写伍尔芙,灵感来自于伍尔芙创作《达洛维夫人》时留下的感想,她说这像开掘隧道,“在人物背后凿出美丽的洞穴”,他们的思绪会不断落回到这些记忆的深潭中。所以,那些苦功,吃准小说家那些坚硬的数据,“钉住日期和季节”(又是伍尔芙的好词),是穿山的工具,让传记家能深入写作者头脑的洞穴中。 莱昂·埃德尔
莱昂·埃德尔
第二点,是硬币的另一面,传记家在砍削时又要变成一个最凛冽果决之人。他对这个传主要有明晰的认知,这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写的是怎样的一部作品,于是,那些满坑满谷的材料十有八九都必须割弃,即使是作者自己的话,很多时候也是混淆视听(有时欺人,有时自欺)。所以,要是你关心的作家有一部好传记,你会感觉里面每一段都有意思,因为能留下的东西,都经历了严酷的淘汰机制,它一定对你理解作传对象有帮助。
我前两年翻译了一本艾尔曼的文集,这一路不认为文学是在真空中生成的评论,《川流复始》是登峰造极的示范。这里面有一篇是评论1969年卡洛斯·贝克写的《欧内斯特·海明威的人生故事》,首先它是一篇对海明威写作生涯的一流论断,其次艾尔曼也对这部传记名作提了意见,他说贝克最大的问题,是传记家自己都没想好要如何解读海明威。所以有很多问题,贝克煞费苦心保持中立,其实应该给出判断。“大多数时候他让我们被海明威淹没,淹没在事件之中,但没有形状的事件只能算半个事件。”于是,看似是传记家在刻画传主的复杂性,但留下的只是摇摇摆摆的坏文笔:“(海明威)可以因为天气而跌入低潮,不管是湿冷还是潮热。但他的低潮又可以被凌晨、被黄昏、被阳光中的微风、被清冽的凉意,被丘陵、山脉和大海一下驱走。”这种复杂,可以拿来形容任何一个摄影博主。
第三点,对我是决定性的,就是任何一个值得你为他花钱的传记家,必定是个第一流的描绘者。小说家的文墨会自然流向让他动心动情的地方。学者,就有种含辛茹苦的阔绰,可以用前赴后继的论文,千页的巨著,堆积无数材料来阐释一个精微的想法。但传记家没有这样转圜的余地,他有一整套很严苛的作业,就是反反复复,只能用几句话去呈现一个地方、一个角色、一件艺术作品,甚至一种氛围、一个时代。比这些事情都难上加难的,是他需要不断去描绘阅读和写作,这种最亲密和飘忽的人类活动,对任何作家都始终是种考验。
还记得在大学的图书馆里,木头椅子坚实到绝情,面前是艾尔曼的王尔德和乔伊斯,缓缓辨认出他呈现的那个过程,日常的细节、时代的流转、作者和其他人的想法,汇集、交融,像浪头一样翻涌起来,凝固成《不可儿戏》《尤利西斯》那样如丰碑般的杰作,是我求学时代可能一只手数得上来的奇观之一。
用21年写出五卷《亨利·詹姆斯传》的莱昂·埃德尔,也是我书架上可以镇宅的大人物。他有个概念叫transference,一种传送、移情,指传记家写到投入的时候,作传对象会上身。艾尔曼写乔伊斯,句式会复杂起来,透露出某种自得和执着;写王尔德,相较之下就更精巧和灵动。比如你会读到这样的句子:“对于爱尔兰人来说,头脑到了牛津就如同身体到了巴黎。”“80年代,唯美主义与其说是一场运动,倒不如说是因为运动不成气候而做的一场规劝。”
马丁·艾米斯当年答应理查德·布雷德福给他写传记,写着写着,不知哪里不合心意,撤销许可,说因为布雷福德的文笔太差了。后来,我注意到布雷福德其实是个很好的学者,让我受益良多。但写传记这件事,确实尴尬,它有点像做翻译,比原作者差太多,是写不好翻译不好的,但真要找到一个跟服务对象水平相仿的人,却舍身忘我地甘当仆从,不容易,也因此更难得。
(陈以侃,作家、译者,著有评论集《在别人的句子里》,译有《海风中失落的血色馈赠》、毛姆短篇小说全集等) 《约翰生传》 [英] 詹姆斯·鲍斯威尔著蒲隆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
《约翰生传》 [英] 詹姆斯·鲍斯威尔著蒲隆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 《沈从文的后半生》张新颖著上海三联书店,2018 传记
《沈从文的后半生》张新颖著上海三联书店,2018 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