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关键词都难以概括的门罗
作者:孙若茜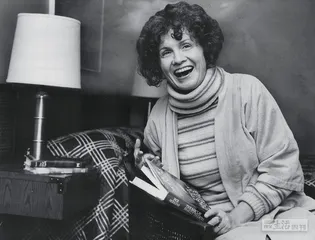 从1968年发表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并获得加拿大总督文学奖起,门罗几乎获得了所有重要的文学奖项。2012年,在短篇小说集《亲爱的生活》出版之后,门罗宣布封笔。2013年,她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诺奖的授奖词将她誉为“当代短篇小说大师”。
从1968年发表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并获得加拿大总督文学奖起,门罗几乎获得了所有重要的文学奖项。2012年,在短篇小说集《亲爱的生活》出版之后,门罗宣布封笔。2013年,她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诺奖的授奖词将她誉为“当代短篇小说大师”。门罗也被誉为“作家们的作家”。作家张悦然就曾告诉我,每一年,她都会重读几个门罗的作品。门罗去世,我们以再次讨论她的写作作为悼念,却发现门罗非常难以谈论和概括。问题也许在于,我们经常试图把作家绑在几个关键词上作为谈论的“抓手”。很多时候作家并不愿意,而有的时候作家自己也需要这样的东西。但很少有门罗这样的作家,这个时代所提炼的关键词对她都是失效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阅读艾丽丝·门罗的,从最初到现在,阅读的感受有什么变化吗?
张悦然:我是从很早开始读门罗的,第一次大概是在新加坡读大学的时候,我买了一本台版的《感情游戏》(大陆译作《恨,友谊,追求,爱情,婚姻》)。几年后,译林出版社出版了她的作品集,那个时候我一口气读了很多,但事实上那才只是第一次,后来我将会不断回到那些作品中。对她的阅读是一种慢慢累加的过程。一开始我会被其中的一些故事,或者是她笔下的一些女性形象触动,后来在阅读中,则不断会有新的东西浮现出来。我现在仍旧保持着每一年都至少在大学里跟我的学生们一起读一到两个门罗的小说的习惯。每次阅读总有陌生的体验,那种让人浑身打一个激灵的体验,但只有一个瞬间,很快会“撤退”下来。“撤退”是门罗在《纽约客》的编辑黛博拉·特雷斯曼(Deborah Treisman)在悼念门罗的文章里所使用的一个词,我觉得特别准确,好像你在无意之间跟她爬到了一个山的顶端,从完全不同的角度看见了曾经熟悉的事物,那个时刻令人战栗,仿佛一切都改变了,但是随后,她就悄悄带着你撤退回来,回到安全和庸常的生活里。
前两天看到李翊云写的悼念门罗的文章,里面也提到,门罗是她会反复去读的作家,门罗的作品和她人生的不同阶段会产生共振。你在门罗的作品里学习,也在门罗的作品里得到印证。 三联生活周刊:直到现在,对门罗的讨论通常还是围绕几个关键词展开,短篇、主妇、小镇、逃离……你怎么看这些概括,它们可以帮读者更好地理解门罗吗?
三联生活周刊:直到现在,对门罗的讨论通常还是围绕几个关键词展开,短篇、主妇、小镇、逃离……你怎么看这些概括,它们可以帮读者更好地理解门罗吗?
张悦然:在谈到门罗的时候,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总是试图用一些关键词去概括她,用得最多的可能就是“逃离”,关于在小镇生活的女人的逃离、家庭主妇的逃离,等等。但其实这种说法很片面,“逃离”并不是她多数小说的主题,用“小镇”概括她同样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我觉得门罗对她身边的环境进行书写只是出于选材的便利。有时我们还会听到人们说,门罗的小说是细碎和平静的,我想他们可能是受到“当代契诃夫”这一名头的干扰,自己其实读得不多,因为事实上门罗的小说非常激烈,也非常黑暗。她是一个短篇小说作家,每写一个短篇小说都像是在重启一个新的设备,承载新的故事、新的主题、新的思考。用某一个主题,某几个关键词去概括她的作品,是很困难的。
三联生活周刊:当我们单独面对门罗某一个短篇小说时,还能体会到难以概括的复杂性吗?
张悦然:门罗晚期的作品中有一些篇幅很长的短篇,写得非常复杂。《纽约客》编辑黛博拉就说到过,她经常在初读时感觉冗长,边读边划掉一些句子,结果等她读到后面,就默默把前面删掉的句子又放了回来。最后她会发现,没有一个词是多余的。门罗的小说就像一台精密的仪器,她的每一笔都让我觉得像是在将一个事物的内部向外展示,一开始你不明白那是个什么东西,但是当你触及事物的内部,就会觉得一切都联系上了。为什么她的句子都显得那么“必然”?可能因为它们要经受门罗一遍又一遍地审视。门罗是个非常执着于修改的作家,她经常在交稿后,又把稿子要回来,只为了改一句话。更夸张的例子是,有一次她被邀请参加活动,朗读自己的作品,坐在台下准备朗读的时候,她已经拿着一支笔修改了起来。当这本书下次修订的时候,她就采用了新的版本。门罗并不只是修改句子的表述方式,她还修改自己的意图。与“句子的必然”相矛盾的是,她的意图是始终变动的。对比她在《纽约客》发表的小说和后来结集出版的版本,就会发现几乎都有改动,有的甚至是意图上的变化。比如说《科丽》一篇,她改过两次,发表在杂志上,收录在当年欧亨利小说奖选集,最终结集出版的是三个不一样的版本。最终的结尾和最初的比起来,叙事又向前发展了一步,但这并没有让其意图变得更清晰,反而更含混了。关于她不断修改小说结尾的倾向,或许从一个角度证明了她的人物在她的头脑中是活的,是不断生长的。她经常会站在他们的角度想,也许他们会这样或者那样做。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门罗后期的创作明显比早期复杂,甚至被视作是一种文体的革新?
张悦然:我认为,门罗在后期的创作里,拥有一种令人羡慕的自由。这种自由首先和短篇小说这种文体有关,它不像长篇小说那样,要将几年的时间投注于一个项目,然后将它展示给公众,被公众评价。一部长篇作品成功了,或是失败了,这个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作家,甚至也塑造着作家的职业生涯。但是短篇小说作家,受到这种读者反馈的影响要小很多。没有哪一个短篇小说的评价能决定和改变什么,但作家的创作生涯又是由一篇篇小说累加起来的。创作后期的门罗,几乎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来创作,不管读者是否明白她的意图。黛博拉表示,编辑她的小说的过程,也是揣测她的意图、试着去理解她的过程。我想这建立在编辑对门罗的高度信任之上。此外,门罗的自由,还体现在她“拒绝”了很多事。有人说,门罗是一个最擅长说“不”的人。她拒绝了很多文学活动和图书宣传活动。当一个加拿大文学奖要再次授予她的时候,她拒绝了,并表示应该把它给更年轻的作家。她过着一种很简单的现实生活,确保多数时间都和她的人物待在一起。
三联生活周刊:能不能谈谈门罗一小部分作品中出现的自传性,她是怎么将自己作为素材的?在这一点上,可以将她与安妮·埃尔诺进行比较吗?
张悦然:门罗作品的自传性特质没有那么显著。她有一部分作品确实用了自己的素材,《石城远望》《乞丐新娘》以及《亲爱的生活》里的一部分小说。但我觉得对于门罗来说,这些都只是材料,她的写作还有别的来源,自己的经历并不是唯一的,跟别的材料比起来,也不具有特殊性。但是对于像安妮·埃尔诺这样的作家,自己就是最重要的文学源头,把自己探索清楚几乎是唯一的、迫切的、必须的事情。
此外,我会觉得她和门罗对时间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在《一个女人的故事》《一个男人的故事》等书里,安妮·埃尔诺用的是一种照片式的写法,写得特别的精确,她让你去看那个女人当时站在哪个地方,告诉你那个女人当时在想什么,她试图把自己主观的记忆客观化,为其赋形,这其中有一种专制。但是在门罗那里,这是一件绝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因为记忆从来都不讲实话,记忆永远在篡改,它要么在折磨我们,要么在保护我们。门罗永远在表现记忆的差池,表现它的不准确性。她在自己的记忆里进行自我教育,不停地打开记忆重新思考,思考当时为什么会这样选择,如果不这样选择又会是怎样。记忆成了她的一个教材,她在其中重新成长。
三联生活周刊:你会重读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作品吗?我知道她是门罗非常好的朋友,也同样是你很喜欢的作家,但她们的写作又是那么的不同。
张悦然:门罗和阿特伍德真的是都给了我很多的精神力量。阿特伍德也写了一篇文章悼念门罗,她很幽默地说自己是门罗倒数第二老的朋友,然后又在后面写了她倒数第一老的朋友是谁。你会感受到那种豁达,就好像一堆老人每天都清点一下人数,算一算谁是最老的那个了。
她们两个确实非常不同,以前我有一个不太合适的比喻,我觉得阿特伍德更像女孩,而门罗更像成熟的女人。阿特伍德小说里的情感是很直接很简单的,黑白分明,非常极致,像《使女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拥有的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核心,关于复仇。阿特伍德的小说受童话、神话的影响很严重,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都是对某些童话原型的改写。在她最好的长篇小说里,你会惊叹于她将小说的结构设计得如此复杂和巧妙。而且和门罗不同的是,除了小说,阿特伍德还涉及很多别的文学门类,诗歌、文论等。她的文论《与死者协商》《偿还》都是我非常钟爱的作品。不过,我必须承认,我很少重读阿特伍德的小说。我珍惜第一次阅读它们的那种感觉,但是重读她似乎收获没有重读门罗那么多。
三联生活周刊:在女性主义的视角之下,我们应该怎么看待门罗的写作?
张悦然:门罗和阿特伍德那一代人的文学生涯都和女权运动关系密切。如果没有女权运动,门罗的人生轨迹可能会完全不同,她也许不会离开家庭,重建她的生活,使她可以自由地写作。女权主义运动当然也影响着她的小说。她写过一些在女权运动的潮流和影响下,追求性解放、丢下孩子离开家庭的人。但是她也写了很多对此后悔、对此反省,重新回归家庭或者永远抱憾的女人。她在小说中写了很多无论是在当时的那个时代还是在现在都并不激进的一些女性角色,但我们还是会觉得在其中受到了一种女性主义的教育。我一直认为,小说很多时候是女性主义失败的地方。女性主义不是一个纲领,小说中经常呈现一个人拿着这个纲领,但是她在生活中根本没法执行,所以很多失败。这些失败,让我们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女性。比如门罗在小说《雅加达》里就写了两个女性位置的互换,一个受到当时文化影响更多、标榜自己更加自由的女性,其实被某些东西困住,而另外一个当时有了孩子,看起来被困住的女性反而变得更加自由。你会意识到并不是某一种生活方式能为你创造自由,或者你以为自己已经接受了女性主义的洗礼,就可以变得百无禁忌。自由仰赖于自省地认识,也仰赖于一点点地争取。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门罗对女性最深彻的洞察是什么?
张悦然:回头去看她的小说会发现,她在大量的作品里展现了女性的“幻想”是如何歪曲现实,却又提供给女性一种特殊的力量,使她得到保护,抑或受到惩罚,但无论如何,那都是一条迥异于男性的成长之路。她最复杂的小说之一,《忘情》,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它探讨了女性是如何可以用一生去爱一个没有面容的恋人的,她用了多少幻想,去维系、发展这份感情。
三联生活周刊:以你的观察,门罗的作品会吸引男性读者吗?在你的课堂上,男同学给出的反馈如何?
张悦然:我觉得男性读者也是会在门罗的小说里面受到很多启示的。即便是在一些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小说里,男性角色也从来没有被描写得很简单。而在另一些以男性为主人公的小说里,比如《火车》《熊从山那边来》等,男人的内心世界被展现得极其复杂,同时,这种复杂是通过充分体谅和同情来实现的,而不是来自女性的审视和批判。
三联生活周刊:门罗去世后,我看到你在小红书上发帖悼念,还让大家留下自己最喜欢的门罗的五个篇目,结果出乎你的意料吗?
张悦然:几乎每个读者的答案都不同,这也许证明了门罗的好小说太多了。从一个读者的最爱篇目,我们似乎也可以了解到读者是什么样的人。比如一个读者留的篇目是《好女人的爱情》《逃离》《乞丐新娘》《我年轻时的朋友》和《洗礼》。我会判断这个读者大概很年轻,还在面对婚恋、从家庭中独立这些人生主题。随着年龄的变化,或许她喜欢的篇目也会发生变化。像《熊从山那边来》这样的篇目,大概要年长一些,才会领略到它的好。
三联生活周刊:门罗在获得诺奖之前就已经宣告封笔了,作为读者,我觉得那已经是一次正式的告别。但面对真正的告别,还是会很难过。
张悦然:我会觉得对很多写作的人来说,门罗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她还在这个世界上和不在这个世界上的感觉是会不一样的。她让我们领略到小说的那种神奇,当想到这个喧闹芜杂的世界上,有这样一个专注地探索小说的无限可能性的人,作为同时代的写作者,还是会觉得非常幸福的。 张悦然门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