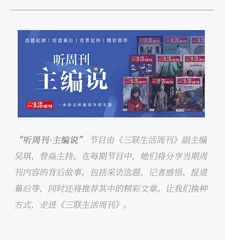主编说 | 和我们一起,去人民公园散个步
作者:曾焱最近“公园二十分钟”的话题在社交媒体上比较火,在印象中属于老年人的公园,如今成了年轻人日常生活里的一个时尚去处。本期新刊的封面题目是《你的城市有没有一座人民公园》,我们想从“人民公园”这样一个和大多数当代中国人有过交集的空间出发,尝试观察我们生活与记忆的样本,记录城市的更迭、社会潮流的变迁;同时也想通过这些故事,来讨论公共空间和个体生活之间的关系。
“公共空间”是一个外来词,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与现代、国民、启蒙、健康等名词差不多同时进入了中国。严格定义的公共空间,应该是一个不限于经济或社会条件、任何人都有权进入的场所,比如街道、广场、公园、公共图书馆等。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于中国人而言,人民公园就是这样一个极具有典型性的公共空间。同事丘濂就在文中提到,2020年初一位名叫刘熙的广州美院学生,在网上发起了一个名叫“在公园”的长线项目,以微博征稿的方式接受并选择发布与公园有关的照片,而在收到的来稿中,刘熙发现最多的照片来自于叫做“人民公园”的公园。据不完全统计,五十年代以后,从省会城市到二三线小城,全国有或者曾经有200多座名为“人民公园”的公园,成为现代中国最普遍的城市公园形态——与此并行的另一个中国式的公园体系则是中山公园,将近有90座。它们有一部分是在民国时期原有公园的基础上更名而建,另一部分则是新建,格局也差相仿佛,都有着凉亭、假山、湖泊、花卉观赏区、儿童游乐园,以及动物角。大多数人在自己的生活里,都和这样一座公园有过日常交集,它承载了许多个体和家庭的集体记忆,在怀旧之外,它是观察自己城市历史的重要场景,对于每一代人都有着不同的意义。
我们四位记者,去了四个不同城市的人民公园。
自贡是一座小城,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市民生活,人民公园都曾经是绝对的城市中心。记者肖楚舟写道,在小城稠密又缓慢的时光里面,大事小事都以人民公园为中心发生。历史上盐商带来过的富丽堂皇,八十年代的下岗潮和个体经商潮,九十年代被彩灯经济所改变的市民生活和城市建设,都围绕着人民公园发生又消逝。
上海人民公园是大都市里的熟悉坐标,近几十年里,功能一层一层剥离,城市庆典、孩童、年轻人渐渐离开人民公园,最后只有老年人聚在这里社交,相亲角替代英语角。记者刘敏引用了作家王占黑写在小说中的一段话,来表达人民公园在人们心中深刻的印记:“每座城市都有一个人民公园,如同每座城市都有一条中山路,一所光明小学和若干间便民理发店一样,它们是自己城市里的基本元素,就像人缺不来肝肺心脾肾一样。”
郑州人民公园,因为一首歌曲里的一句歌词——人民公园我们牵手说爱——而有了网红的气息。网络上关于这个公园的照片或视频都充斥着怀旧的情绪,每个镜头都在尝试捕捉那些即将消逝的记忆碎片。但记者陈璐在这里找到了省漂的故事,人们期待这个公园,既能包容城市的快乐,也能拥抱那些心碎的瞬间。
记者卡生笔下的南宁人民公园,仿佛是这座城市的某个缩影。旧时它并非处在城市中央,却是市民生活的中心,既是集会的场所,又兼具动物园功能,还是体育、文化活动的场地,五花八门,无所不含。就像南宁这座杂糅的城市,“类似混合的、时空错位的后现代布景”。现在,随着老城区的拆拆建建,人民公园反而处在这座城市的中心位置,却又慢慢退出了市民日常生活的中心,成了老字号一样的象征性存在。
就像一位采访对象所说,一个城市能被记住的东西其实屈指可数,“人民公园 ”就在其中。在我们的封面故事里,它是时代的滤镜,也是个体和家庭记忆的具身。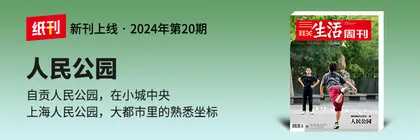 ———编辑/高一丁音频制作/张译丹
———编辑/高一丁音频制作/张译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