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在极度鲜活和极度虚无之间
作者:孙若茜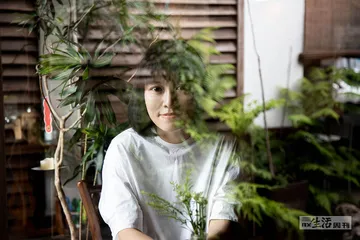 在《平乐县志》之前,有关平乐镇的故事颜歌已经写过几个。颜歌的故乡在四川郫县,平乐镇的文学版图就是依照那里构建的。平乐镇一共只有四条街,“南街上都是些操扁褂(打拳)的,西街上满是读书人,东街的人大多是政府和官家的子弟,北街是外地来的客家人”。颜歌的长篇小说《五月女王》,写了住在南街的袁青山,一个身体总在长高的女孩;《我们家》通过住在西街的段逸兴之口,讲述了他们一家人——以身为豆瓣厂厂长的父亲为首,筹备奶奶80岁寿宴的一场闹剧。接下来颜歌写东街,经过短篇小说集《平乐镇伤心故事集》中五个小故事的热身,有了长篇小说《平乐县志》。
在《平乐县志》之前,有关平乐镇的故事颜歌已经写过几个。颜歌的故乡在四川郫县,平乐镇的文学版图就是依照那里构建的。平乐镇一共只有四条街,“南街上都是些操扁褂(打拳)的,西街上满是读书人,东街的人大多是政府和官家的子弟,北街是外地来的客家人”。颜歌的长篇小说《五月女王》,写了住在南街的袁青山,一个身体总在长高的女孩;《我们家》通过住在西街的段逸兴之口,讲述了他们一家人——以身为豆瓣厂厂长的父亲为首,筹备奶奶80岁寿宴的一场闹剧。接下来颜歌写东街,经过短篇小说集《平乐镇伤心故事集》中五个小故事的热身,有了长篇小说《平乐县志》。 《平乐县志》的故事发生在2010年左右,从平乐镇农资公司的下岗女出纳叶小萱站在东门城墙下头跟人说哀怨,操心女儿婚事讲起,到女儿陈地菊与女婿傅丹心成婚,傅丹心的父亲、县志办副主任傅祺红在临退休前卷入单位争斗,再到傅丹心参与黑社会赌球操盘遭陷害欠下巨款,以及最终傅祺红自杀,陈地菊走上出国求学之路……这些人物命运令人唏嘘,但故事本身并不是这本小说最吸引人的地方。
《平乐县志》的故事发生在2010年左右,从平乐镇农资公司的下岗女出纳叶小萱站在东门城墙下头跟人说哀怨,操心女儿婚事讲起,到女儿陈地菊与女婿傅丹心成婚,傅丹心的父亲、县志办副主任傅祺红在临退休前卷入单位争斗,再到傅丹心参与黑社会赌球操盘遭陷害欠下巨款,以及最终傅祺红自杀,陈地菊走上出国求学之路……这些人物命运令人唏嘘,但故事本身并不是这本小说最吸引人的地方。为什么把当代的故事放在明清小说的叙述框架里?
“《平乐县志》最引人注目的大概是对明代话本小说叙事腔调的拟仿。”小说中虚拟说书的情境,频繁地使用“诸位看官”之类的套语,插入各种旧体诗词韵文。作家、评论家张定浩在评论文章中写道:“说书套语首先当然是在彰显叙事者的存在,这个叙事者在对着读者说话,提醒读者他是在听一个故事而非参与一个故事,引导他在沉浸式的细节体验之外,还要对人生意义进行更为广阔的思考。但这个叙事者与现代小说中的叙事者又完全不同,后者要么是作者的化身,要么是作者创造的一个人物,总之,是一个具有鲜明个性、意志和思想的个体,但说书套语却恰恰是要隐藏掉任何个体的身份,也就是说,他试图引导读者面对的,不是他个人的智识,而是某种更为普遍之物。”
《平乐县志》为什么要用这样的叙事腔调?这也是我在采访中问向颜歌的第一个问题。颜歌告诉我,她的确希望写作者能在小说中达到一种隐身的状态。“长篇小说是作者创造的一个世界,我希望它能够自行运转,而作者是被移除的。我不比任何人更聪明透彻,因此不想在小说中表达个人的评判,也一定不能通过小说去教化。归根结底,我就是为了呈现。至于我想要表达和探讨的所谓真相到底是什么——它一定是反语言表达的,不可能用一个自然段就讲清楚,因此才要用长篇小说这样的形式。”颜歌解释说,“我尽量呈现多人物、多声音、多个故事线,呈现一个万物蓬勃的世界,这让我感觉自己就像在制造一个球体,它有自己的中心,像一个星球,而作为小说家,与它的关系是无限接近,但永远不能触碰。”
对颜歌而言,模仿明清小说的表达方式,还有几个原因:一方面是她如今常年生活在英国,非中文的环境反而使她更想探索中文本身在文学中的质感和理念——“从这个角度,我肯定要回到‘五四’之前,做一个复兴——也不是真正的复兴,更应该说是一个后现代的模仿。”另一方面,颜歌发现,让她在2012年想要提笔书写的那个当下,其现实与明清小说中读到的繁杂现实极为相似,因此用“三言二拍”的形式装载非常贴切。同时,这样的形式还能提供一种距离感——“读明清小说的时候,我们清楚自己是在看过去的人和事,好像自己站在未来,故事中的美丑善恶痛苦喜悦都会自带一种美学上的距离感。把当代的故事放在明清小说的叙述框架里,进行一种历史视角的解构,读者也许就会发现,我们现在非常在乎的很多事,日常的喜怒哀乐和绝望,都会因为时间而灰飞烟灭。”
颜歌在乎小说的叙事形式,她书写平乐镇每条街的故事时,都试图寻找到一种更为恰当的叙事者的声音,它们无法彼此替代,也不能重复。她告诉我,假如用《我们家》的声音写《平乐县志》,读者一定会觉得有点儿齁得慌,太过鲜活的呈现会变成一种喧嚣,一种不加克制的狂欢,让人觉得很吵。而其他的形式,不管从什么人的角度去讲述,故事最后都会变得很平常,甚至过于庸俗市井。而“三言二拍”的范式就像是给她立了一个规矩,让她能将笔下的现实控制在极度鲜活和极度虚无渺小之间。
除此之外,《平乐县志》的另一个叙事声音,是县志办副主任傅祺红的日记,它几乎附在小说每一章节的末尾,贯穿始终。傅祺红的日记中有他自己的“今日工作”“今日学习”“今日膳食”和“今日琐记”,以及早年的工作和生活。其中有多少自欺欺人、多少与现实相悖之处,读者作为旁观者是一目了然的。“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小说中‘傅祺红日记’的部分实在是小说家泼给时下非虚构热潮的一盆兜头凉水:日记和县志当然都是非虚构,是如今的社会人类学者和田野工作者的最爱,但它们有可能也是虚伪的、浮泛的和无聊的,它提供的现实,有可能只是一种自我阉割的现实、一种鹦鹉学舌的现实和一种被意识形态强力冲刷过的宛若面具般的符号化现实。”
张定浩在评论中指出:“《平乐县志》因此就比它表面看起来的样子要复杂。它在放弃现代小说的个人叙事者声音之后,并非简单地回归到传统章回小说的集体叙事,而是同时给我们端出来两种集体叙事者的声音,其中话本叙事者代表着民间集体,而县志叙事者则代表官僚集体。小说家让我们看到两种集体声音之间在各个方面的撕裂,而这种撕裂才是普通人所生活其中的现实,它浩瀚而持久,正大而无形,与之相比,知识分子的那种躲在微信朋友圈和个人意识流里的忧国忧民实在微不足道。”
豆瓣有评论说:看完《平乐县志》竟没有一个自己喜欢的人物。颜歌不觉得这是负面评价,反倒是这部小说的一个优点。“你不需要去喜欢任何一个人物,这部小说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我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以庞杂的图像最大化地表达了庞杂的意义。”
颜歌告诉我,小说既然取名“县志”,就说明了她想要呈现的是那些看似不重要的、没有声音的人物。在此前那些平乐镇的故事中,她写过很多“向外”的人,比如《我们家》里的薛胜强,所谓“向外”是诸如他有钱、喜欢爆粗口之类的特质,使人容易印象深刻。“他是异人——你写一个人,头上有个角,马上大家就记住了。”颜歌觉得,写作这样的人物并不难,沾了人物本身的光。于是在写《平乐县志》时,就想给自己出出难题。
在颜歌看来,即便许许多多的人在现实中如蝼蚁一般,也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在统计数字中可以被随时抹去的小数点。作为一个描摹者,不管描摹的对象看起来有多么普通,也要去发现他们。“我所写的人物,都跟我自己没有差别,他们的挣扎,他们的瑕疵,甚至他们的丑恶,所有人性的弱点,他们有的,我都有。”这也是她书写傅祺红、陈地菊这样的人的意义。绝大多数时候,他们没有声音。就比如书中写到傅祺红的死——如果不是在小说中,他突然的死亡也许毫无意义,甚至都不会出现在统计数字之中。“我去写这样一个小人物莫名其妙微不足道的死亡,使他不但拥有名字,还拥有故事,其实是在向大家发出邀请。大多数人被生活挤压在一个紧迫的空间里,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共情他者,而写作者归根结底就是共情者。只有更多的人去共情,世界才能够继续存在。” 四川郫县马街(黄金国 摄/ 视觉中国 供图)如何用文学来写当下?
四川郫县马街(黄金国 摄/ 视觉中国 供图)如何用文学来写当下?
颜歌向我说起,疫情解封不久后的春天,她回过一次国,那时临近《平乐县志》交稿,她正在对小说做最后的修改。只有两个晚上能住在郫县,她用这两个晚上的时间走了走那些被她写进小说的路。主人公陈地菊每天上下班的路、回娘家的路,让书中的汪红燕触景伤情的倪家巷,等等,这些路该从哪里进哪里出,从哪里穿过去调个头之后能通往哪儿的路线,颜歌在英国诺里奇写作时,脑子里不知道走过多少遍。可真的走在路上,她才发现街道不是记忆中的样子,比如小时候郫县东西南北这几条老街上没什么树,如今却是巨木参天,仅这一样,街道的状态就很不一样。
转过年的秋天《平乐县志》出版,颜歌为宣传新书回国。因为腰伤,她先在郫县住了一周,每天爸爸带着她去做中医理疗,事无巨细地照顾陪伴,老同学聚会都带着她一起参加,颜歌觉得自己好像重新变回了一个什么都需要依靠大人的小孩子。对她来说这种感受很神奇,而真正让她觉得奇怪的是,不管走到哪儿,她心里想的都是她笔下的人物,脑中浮现出的最鲜明的图景都是《平乐县志》《我们家》和《五月女王》里的情节,自己真实的成长回忆反倒被掩盖了。
而写《平乐县志》的念头,最初是在2012年生发的,她当年给自己立下的目标是“用文学来写当下”。颜歌说,最后将它写完时,她其实是在扮演当时的自己,尽量地忽略当下——也就是2023年时的她。颜歌道出的这些复杂的感受,使得与《平乐县志》相关的时间线索变得庞杂倒错,也让我更好奇所谓“当下”——她在写作小说之初想要书写的当下,她退回时间想要寻找的当下,停笔时的她关心的当下,究竟都是什么?什么是她真正关心的问题?颜歌说,写《平乐县志》时,我们这一代的处境和父辈之间巨大的差别,以及它造成的鸿沟是她关心的问题之一。但小说收尾的时候,它已经不再是她的“当下”了。“10年时间,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我来说,最迫切的问题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可交流,是人类的环境危机,是如何面对虚拟的现实。不过不管写什么,都是给出我的问题,小说家永远不能提供答案。”建立属于自己的中心
平乐镇的故事在颜歌建构的文学版图中占有绝对重要的位置,但并不是她写作的全部。到现在为止,她在爱尔兰和英国生活了将近10年。大约从2016年起,她就一边用中文写平乐镇,一边开始尝试英语写作。
“所谓双语作家听起来很美,但其实是一个不可能的状态。因为人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能量。站在写作者的角度,我虽然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索的状态,但同时也觉得真是给自己挖了一个坑。”对颜歌来说,双语写作者的状态造成了很多问题,其中既有所谓存在主义的问题、艺术创作上的问题,也包括与经济公司打交道时实际操作层面的问题。
对颜歌来说,中英文写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彼此间不相通。英国的朋友对她的中文写作不了解,比如《平乐县志》出版,对她在英国的生活所能产生的影响几乎是零。同样,就算她在英国教三门课评两个文学奖,忙忙碌碌,也在相应的语境中受到认可,但这些在国内的影响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有时候我会觉得很疲惫,没有打通的世界之间有一种不可穿越的感觉,有很多误解、很多空白,要做很多的解释,甚至包括我的两个语言的人格,也有一种不太能流畅切换的状态。我也不知道最终能不能把这两个世界打通。”
所谓两个语言的人格,颜歌给我讲了两个小片段:《平乐县志》的第一场新书发布活动在成都,结束后,颜歌曾经的一个学生上前找她签名,她教授的是英文写作,因此这是他第一次听颜歌说中文:“说中文的你和说英文的你特别不一样。”他虽然只是表达惊讶,并没说究竟哪儿不一样,但颜歌理解,因为她也有同样的感受。另一个片段是关于一家以英文进行报道的国内媒体,采访时,记者用中文和颜歌聊《平乐县志》,谈到她的英语写作时又换作英文提问,颜歌也就跟着切换语言作答。对方说她在用中文表达时似乎就会变得比较软弱。报道刊发出来,颜歌发现,那一半中文的访谈一字没用。
她生出一种惭愧和对自己的失望:“我觉得我不会说普通话了。”所谓“不会”,是感到自己好像变回了20岁出头儿时的样子,一个26岁出国前的自己——言语中不断地夹杂着对不起,唯唯诺诺,很怕得罪人,不自觉地就会选用一种低姿态进行自我表达,而不会自信地阐述自己。这让她感到沮丧。
她确实有许多年几乎不使用普通话了,十几年时间从美国到爱尔兰再到如今生活的英国诺里奇,生活中全是英语,和家里人通话用的是四川话,她形容自己的“普通话人格”许久没有更新,和她当下的内在出现了错位。也因此,她一度对自己说:“中文的我已经完全枯萎了。”很长一段时间,她都坚信《平乐县志》会是她用中文写作的最后一本小说了。“快写完的时候我特别舍不得,对我来说,仅仅是进入中文的语境去描摹,仅仅是这个动作,就能让身在英国的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很怕一写完就再也没有回家的路径了。”直到为新书回国的二十几天“系统更新”,才让她感觉“又活了过来,我还是想用中文写作”。
至于为什么入坑双语写作,就要说英语写作的吸引力了,或者说是什么让颜歌认为值得探索:换一种语言写作,就等于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可以在其中找到一个新的身份,挖掘一些新的东西。英语写作世界拥有极大的丰富性,不同国家、地区,不同的语境之间有很大的差异,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叙事方式及其文学体系下的评价方式都不一样。这种差异不仅仅存在于例如美国写作者和南非写作者之间,也存在于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写作者之间,以及像她一般的中国的英语写作者和世界其他英语写作者之间,因此呈现出一种多声部的样貌。
更多的可能性摆在颜歌面前,她感到兴奋:“你会看到其他的人是怎样从不同的角度使用一种语言写出怎样的东西的,每一个作家都有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理念在对撞、对话,还可以这样玩儿?这是一件特别令人激动的事情,从叙事形式到故事选材,没有范式,不存在只有写什么样的东西才是好的,或者有什么不能写,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大的诱惑。”
颜歌解释说,在英语世界,假使某种写作范式被视为经典和中心,那么当下几乎所有写作者都在反抗中心,想要去解构它,或者重新建立属于自己的中心。也可以说,英语写作是一个多中心的状态,或者是在走向多中心的路上。就好比20年前,一个华裔作家需要去写些英语读者想看的、能理解的所谓“中国的故事”,其作品才能在英语世界发表、传播,再被慢慢接受。但是现在,当一个中国作家尝试英语写作,就比如她——她发现自己在文本中保留的反抗,拒绝英语读者理解的部分,竟都被他们欣然接受了。最好的证据就是她的首部英文短篇小说集Elsewhere能由英国Faber这样主流的老牌出版公司出版。
Elsewhere由九个故事组成,每一个都像是来自不同作家的声音。它们拥有不同的叙述风格、不同的故事背景,但彼此间也有某种连贯的线索。为了强调它们的不同,颜歌说:“如果你读它,可能会觉得这个作家有点儿人格分裂。”事实是,她什么都想尝试。比如书中的最后一篇故事,讲孔子和他的弟子。它不是一个力求真实的故事,更像是对现实的反讽。颜歌在故事中直接放入了大段汉字。她解释说,她将插入的汉字作为一种无意义的符号,将非中文读者的阅读空白作为叙事表达的重要组成,这种文本实验在某种意义上给汉字创造了新的意义,是她在中文写作中无法尝试的。
颜歌说,别说20年前,10年前的她也不能想象这样的尝试是可以被出版社允许的。换语种写小说,本质上最大的问题是写作者所面对的读者的改变。在2013年、2014年左右,颜歌的中文小说刚开始被翻译成英文时,编辑就曾建议她做出一些方便英语读者理解的改动。比如,小说《我们家》中有个人物叫周新玉,这名字就被翻译成了Jasmine。而现在,当颜歌在小说中写到子游、子路、子夏这些人名时,全用拼音。虽然对于英语读者来说,这些名字过于相似,一看就得蒙,但“时代变了”。颜歌打了个比方,“如果写作者和英语读者分别站在一座桥的两头,那么过去,英语读者会选择站着不动,写作者要为他们做出改变,走上前。但是现在,英语读者至少要走到桥的中间来”。 平乐县志颜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