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负担为何越减越重?
作者:魏倩 2023年10月底,河南郑州一小学女教师自杀离世,在遗书中提到“加班、写宣传稿教学之外的任务压力……只想安安静静教书”,引发广泛共鸣。关于中小学教师课外负担的讨论,也持续至今。
2023年10月底,河南郑州一小学女教师自杀离世,在遗书中提到“加班、写宣传稿教学之外的任务压力……只想安安静静教书”,引发广泛共鸣。关于中小学教师课外负担的讨论,也持续至今。教育研究者李镇西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做语文老师和班主任,之后在成都市武侯区教科院工作,曾担任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校长。2017年和2021年,他和团队先后两次在个人公众号上发起针对教师非教学负担的调查,采集样本数量接近一万人。李镇西发现,虽然国家相关部门在2019年就曾印发文件,明确提出为教师减负,但此后,中小学教师的“非教学事务压力”不是更小,而是更大了。就“教师负担为何越减越重”的话题,本刊记者对李镇西进行了专访。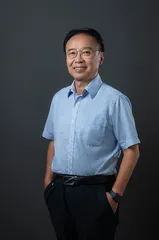 三联生活周刊:据你观察,义务教育阶段教师负担过重的现象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
三联生活周刊:据你观察,义务教育阶段教师负担过重的现象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
李镇西:其实教育界形式主义的情况一直都存在,只不过近几年这个现象更加突出了。我20世纪80年代开始做班主任,2000年左右开始做校长,那时学校里也会有一些检查,拉一些标语,但总体而言校园还是属于教师和学生的,氛围比较清爽。我是2015年后到了成都市武侯区教科院工作之后,开始逐渐听到老师们的反映,甚至有的年轻老师会说,他只有回到家里才能有时间认真备课,因为在学校里干扰太多了。老师们的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了一些所谓的“重要事情”上,比如各种检查材料、活动表格,上级部门都可以给学校派任务,比如消防“四个能力”建设、禁毒示范学校创建、“七五”普法档案、病媒生物防治等,这些任务都和学校的教学常态没多大关系。于是2017年就在我自己的微信公号“镇西茶馆”上做了一次“请问,是哪些因素让你的精力耗费在无效甚至无聊的忙碌中”的调查。
当时的调查数据样本并不算大,参与调查的人数一共2787人,但是覆盖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我一共设计了8个题目,主要针对基础教育领域的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阶段的教师,从其所在地域、学校、岗位、基本教学任务准备、教育教学研究、时间耗费等方面,对教师在校工作的实际情况做了调查分析。
三联生活周刊:你当时的调查有哪些发现?
李镇西:参与调查的2787名教师中,来自三、四线城市及其所属乡镇地区的教师占比88.46%,一线城市的教师仅占1.1%,这也代表了当时我国基层教师的基本分布状态。其中占比最大的还是小学和初中阶段的教师,分别是47.7%和34.3%,在这两个阶段出现的非教学事务现象比其他阶段更为突出,中小学教师的此项工作负担要比其他更为沉重。
我们设计的问题中,第一道就是:你觉得每天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进行基本教学任务的准备?回答“没有”的教师,占比达到52.6%。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教师都没有时间和精力完成我们教学活动中最基本的“备课”工作,他们都要通过在校加班、回家加班来完成基本工作,更不要说完成教学研究了。没有教学研究,又如何提高教学成效呢?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老师的时间具体都花在哪儿了呢?
李镇西:我们当时的调查中,“除基本教学任务”外,耗费教师时间最多的事项分别是:完成各级各类检查任务(占比68.4%)、参与学校临时交办的非教学类任务(占比54.1%)、完成各级各类的网上学习任务(占比41.1%)、参与各级各类会议或培训(占比33.1%)。之后才是批改作业、填写表单、处理特殊学生问题等。可以说,在那时候,“非教学任务”带来的教师负担已经很重了。
2021年,“双减”政策下达之后,各地的减负提质、课后服务、延时服务措施纷纷出台,这些都给教师带来了新的挑战,负担无形中增加了,于是我又在自己的公号上发起了一次“‘双减’政策背景下,中小学教师负担发生了哪些变化”的调查。那次我们收到的调查样本总数为6653份,同样覆盖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
最终发现,教师们的“事业发展类负担”中(多选),较之教师的学历提升与进修,教师的职称评聘(占比91.41%,6082人)成为更受关注的焦点。而在“社会事务类负担”中(多选),教师的非教育性社会事务与政府部门检查占比为90.37%(多达6012人),明显高于家校沟通占比的47.71%。另外,从时间方面来看,教师们的负担主要来源于节假日上班、开会或其他组织活动,而非正常教学时间内的早晚自习。
我们2021年的那次调查中,还有2942份主观样本,教师列举了很多突发性事务,甚至有教师用近600字篇幅描述,比如:紧急通知,督促学生和家长完成普法学习(禁毒、交通、消防、防疫等学习),要求全员参与,人人过关,次日统计全班完成情况;排查各班家长旅居史(骑车戴头盔情况、家长接种疫苗情况、学生假期到水边情况、学生特异体质、家长下载某App情况等),或者表册家长签名,下午截止,汇总上报;明天领导视察(绿色验收、达标、常规检查、现场会等),请每人准备公开课(推门课),学生统一校服红领巾。
最近我又重新翻看了当时的调查数据,可以说,现在情况基本没有什么变化,甚至可以说越来越严重了。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我们一般能想到的“非教学任务”,可能就是许多媒体都提到过的各种“进校园”活动。但你的调查似乎可以看出,“非教学任务”涉及的范围远比这些要大?
李镇西:是的。从老师们的留言中你能看出,单独把这些事务一项一项拎出来,似乎都是必要的工作。比如学习和培训。老师学习当然很重要,教师就要不停地提升自己,在这个时代,你不能仅靠上大学学到的那些知识了,那么培训肯定很必要吧?我们客观上没办法把老师们聚在一个地方进行培训,这时候用网上培训也很合理,是吧?包括各方面的“进校园”,你一问,他都是人人有责,说都有必要性。
事实上,从教师们的反映上来看,他们提到的“非教学任务”主要可以分成两方面,一种是他必须做,也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在考评和要求中把它形式化了,比如手写教案、各种学习和培训。我们是反对形式主义,但并不反对这种形式,比如备课上课这是我们必须做的,但是如果你备课的初衷变成了应付检查,要完成某种指标,这就成了一种作假和应付了。
另一种就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比如每一个部门都说要“从娃娃抓起”,各种活动都要进校园,就是我之前提到的消防、普法、病媒防治等。我想这个和每个部门的考核要求有关,比如很多上级的要求是要达到普及率百分之多少,在社会层面上学校是一个人比较多,管理相对容易的部门,那只要在学校发个通知,参与的人数多了,普及率也就达到了。当然这又是另一种形式主义。而且这些活动似乎也具有某种教育的正当性,比如环保、节能、垃圾分类,似乎也觉得这些应该让孩子们学习。再比如为了安全,很多地方要求老师们去巡河,你听起来好像都很合理,但这一股脑下去对老师的精力就是一种损耗。
当然我认为这两件事也都是紧紧缠绕在一起的,形式主义和“非教学任务”很难区分,互相影响,比如哪怕我们认为一些任务是为了教育必须做的,但如果初衷是为了完成指标,为了达到某个考核数据百分之多少,为了“留痕”、拍照,那它也可以视为形式主义。当这样的工作内容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又怎么能要求学校守住大门,不去完成来自其他部门的形式主义的任务呢?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造成这个问题的症结是什么?2019年,教育部曾颁发《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文件,为什么文件颁发后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李镇西:去年有个老师在网上发了一篇文章,在教育圈引起讨论,说他不参与“2.0培训”(全称“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2.0培训平台”)了。“2.0培训”是帮助教师熟悉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一个培训,要求所有老师同一时间打卡,计入继续教育系统。这位老师说其实他是一个很热爱学习的人,但他以后不再参与这个培训,他觉得这个对他没有必要。但同时他说,“我退出这个培训,以后我也就不参与评优晋级和职称评定了,我看淡了”。
这就是我们的老师面对的现状。这些我们所谓的“非教学任务”和形式主义的任务,是要和他的绩效考核、职称评审挂钩的,那老师想要获得某种空间和自由,就必须放弃自己的这部分追求。但这种“反抗”对于我们广大的基层教师和一线教师来说,显然是不现实的。一定要完成这些任务,原因何在,老师说这是校长施压,校长说他两头受气,局长给他压力,局长又把责任推给家长和社会身上,但最终默默承受一切的人是谁呢?是我们的孩子。
一方面我们的教育部门和学校缺少这种担当,只能通过考核和问责的方式把压力都加到老师身上,另一方面我们又不断在泛化学校教育的边界,学校的教书育人的核心和首要任务被挤压了。像我们之前说的,现在为了安全,课间十分钟孩子都不能到操场上去玩耍,各科老师更是要在课间还回到教室维持秩序,看管学生,否则一旦出问题,就要被家长和社会问责,这让他们怎么能安心备课,从事教学活动呢?
文件颁发后,各地也下发了教师减负清单,罗列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进校园”活动,要求各级部门配合守好学校大门,但这部分压力减下来之后,老师们的负担并没有减轻。因为另外的那些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层层加码的培训和学习,从社会各界转移来的教育压力并没有减少。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双减”后又做过一次关于教师负担的调查,那次调查的结果怎么样?“双减”之后教师非教学事务压力有什么变化吗?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双减”后又做过一次关于教师负担的调查,那次调查的结果怎么样?“双减”之后教师非教学事务压力有什么变化吗?
李镇西:2021年那次设计的题目一共30道,其中和教师负担来源有关的有6道,关于“双减”对学校迎检以及教师负担的影响的有2道。
我们发现,承担课后服务的教师为语文、数学、英语等教师占比高达56.53%,达3761人,物理、化学、生物、科学等教师占比为18.97%,由此可见语数英等主科老师还是承担课后服务的主力军。这些延时活动对老师们的具体观感则是:“工作时间延长,影响个人生活”“工作压力增大,职业幸福感降低”“工作强度变大,可是工资待遇没有变化”,占比分别为82.92%、77.30%、75.32%。
我们也设计了研修、作业管理等相关的题目,最终发现,其实“双减”本身并不是教师负担增加的核心因素。“双减”是给学生减负,这就给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老师的智慧、教学水平都是新的挑战,所以迫切地要求教师各方面的水平提升,但是我们并没有给老师留出这部分时间和精力,老师要有足够的时间做他的“正事”,而不是把其他不该他做的事都让他做了,那在面对更高要求的时候,自然会觉得压力更大。
当然,“双减”后的延时服务和课后托管,在一定程度上也挤占了他们的备课时间,但更重要的还是过去的形式主义的逻辑,面对新的政策,就要做各种学习、公示和培训,这些资料工程同样也是海量的。但我们并不能说是“双减”本身带来了问题,而是旧的问题没有得到正视和解决。
也包括很多人会提到是不是疫情的影响,我认为像“停课不停学”那段时间老师们要在线上课,教师们对不同工具的掌握程度不一样,这的确会增加教师的工作负担,但我觉得这些还是相对暂时的,现在社会已经恢复正常,那么就更应该回到教育的正常轨道,回归到教育的常态和常识上来。 三联生活周刊:你所说的常态和常识指的是什么?
三联生活周刊:你所说的常态和常识指的是什么?
李镇西:说白了,教师的工作就是教书育人,教书就是上课,育人就是给学生做思想工作,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是数字化时代,大家可以有一些手段的更新,可以有新的政策和建议,但是教育的本质不能变,不是把教育当成完成谁规定的任务,或者形式主义的纸面文章。
其实判断一件事情是否增加老师负担,最核心的是两点,第一,这事该不该做,第二,是主动还是被动。第一点的意思是,这件事是不是教育必须的,像我们说的,上课是必须的,备课是必须的,但应付检查就不是必须的。如果你是纯粹的为了应付,比如什么创卫、教师督促学生背那些条条款款、要检查要考核数据指标,这些就完全是不必要的了。
第二点,即便这件事是应该的、必须的,我们是强迫大家全部完成,还是应该有所选择?是不是可以允许一部分老师不做,或者采用正面激励和引导的方法来完成?这就是教师的自主权问题。比如我在上世纪80年代当老师的时候,我们班里有班歌、班服,其实后来所说的“班级文化建设”,那时候没有人做,但我觉得这个有意义有意思。再比如我会给学生写信,每天晚上要写五封信以上,还要提前打草稿,作为一种师生交流的方式。这些其实工作量都很大,但这是我自愿的事情,也是我的教育尝试,那么我就去做。但放到现在,如果这些变成“一刀切”的强制任务,要求每个老师每天给学生写一封信,要手写教案,要求每个老师每年都要去家访,要做班级文化建设,你出发点或许是好的,但最后就会变成一种强制,而后就滋生形式主义。我们老教师总说,他们过去的家访就是家访,不是为了拍照,不是为了填表。那时候读书就是读书,不是为了培训,不是为了绩效。但这背后其实是年轻教师们痛苦的根源,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按照自己的理想做教育了。
从更本质的意义上来看,这实际上是我们的学校究竟是为谁而办的问题。我可以举个例子,现在我们各地很多学校都会立陶行知像,往往是高大宏伟,展现人民教育家的气质。但是我们学校的陶行知塑像是一个坐像,就是他在花园里面和一群孩子聊天。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儿童视角。我们的学校是属于学生和老师的呀!但现在,我们在学校的宣传栏里看到的往往是什么办学理念、什么校长的照片,旁边介绍什么某某教育专家、什么级别的教师、什么国家课题。这些东西孩子们感兴趣吗?他们会在乎什么正高副高学历获奖吗?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些就是给上级检查的时候看的,是给外人看的。但参观者什么时候才来一次?我们的学生可是天天在这里生活的活生生的人啊!
我们的学校不是给上级、给领导办的学校,是给学生办的学校。我想只有把这个思想扭转过来了,才能守好校园的边界,才能让教师拿回自己的自主权。 李镇西教师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