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我的答案就是我的小说的答案
作者:孙若茜 采访进行到一半时,毕飞宇说:“我给你讲两个故事。”
采访进行到一半时,毕飞宇说:“我给你讲两个故事。”为了写作小说《欢迎来到人间》,他花了很长时间待在医院,和医生相处,所谓体验生活。有一次跟着医生进手术室,他被骂惨了。那是一场肾移植手术前的准备工作——“修肾”。为了让肾源达到能够移植的要求,医生要在移植前预先清除肾源上的脂肪,修剪血管的切口、尿管的长度之类。肾源从手提冰柜里被取出来后,毕飞宇发现了它的特殊之处——竟然有两根动脉血管,他条件反射地要抬手做出一个指它的动作,结果被带他进手术室的医生极其严厉地制止了。他们很熟,这更让毕飞宇觉得尴尬。他当时不理解,进手术室之前,他是严格执行了消毒的全部流程的。从手术室回到休息室,作为朋友的医生给毕飞宇冲了咖啡,又点上烟,说:“小毕,不能这样的。你根本看不见自己的手上有什么,哪怕一粒微尘掉下去,感染了,一条命就没了。”所以后来书里就有了这样一段:“傅睿左手托着左肾,右手托着右肾。它们像一对括号。傅睿有些亢奋,十分渴望张开自己的双臂,让这一对括号容纳进更多的内容。傅睿克制住了,他没有做多余的动作,他不能孟浪。”
以毕飞宇最初的设想,这部小说是要完全建构在医院之内的,他想把医院里面幽深的世界写透。但他后来发现自己不可能完成。他意识到他关于临床手术的医学知识储备,最多只能为他完成一到两章的供给。和其他行业不同,医院的规则严谨,没有丁点儿容错率,就像肾源容不得微尘。叙述因此也需要极其严谨,一字之差就能成为一个硬伤。于是,他把亲眼所见的手术细节原原本本地写进了小说,但又让小说里的人物走出了医院。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肾移植手术之后。医生喊他一同查房,一进门,毕飞宇先看见病床下面挂着的导尿袋,血红色。这是好事,说明被移植的肾已经开始为新主人的身体工作了。躺在病床上的女人45岁上下,医生找准她身上的位置,摁了摁,问:“疼吗?”“不疼。”她回答。毕飞宇一瞬间就被这两个字的发音震住了——地道的家乡方言。他觉得难以置信,前一天的下午,他才刚刚看着那两颗肾在医生手里颠来倒去,而此刻,肾脏已经有了力气,帮助一个人说着他的家乡话。“如果病人开口说的是普通话,我大概只会觉得‘生命就是这样的’。但我遇到的第一个肾移植手术成功的人,偏偏说了我的家乡话。”这样的时刻,让他在刹那间燃起某种敬畏心。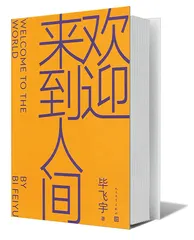 毕飞宇不止一次地说起,小说《欢迎来到人间》的写作过程,对他来说就是一场噩梦。从这场梦中醒来,他用了15年。在这之前,他耗时最长的一次写作是《平原》——三年零七个月。他说,那时提起笔,时间眨眼而过,就像是吃了一顿饭。写作《欢迎来到人间》,生理感受就完全不同了——永无止境的煎熬、自我怀疑,一点点挣扎着从中爬出来,像是过了无限辛劳的一生。停滞,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推翻,手起刀落间初稿的30万字就被他自己删得所剩无几,又从小说的第二章重新写起,然后再推翻。直到小说在《收获》杂志上发表的前一天,他还删掉了结尾的两万字,调整了一整段情节的位置。其间有十几次想要放弃,终于还是写完了,也许“不疼”的刹那,是种动力。
毕飞宇不止一次地说起,小说《欢迎来到人间》的写作过程,对他来说就是一场噩梦。从这场梦中醒来,他用了15年。在这之前,他耗时最长的一次写作是《平原》——三年零七个月。他说,那时提起笔,时间眨眼而过,就像是吃了一顿饭。写作《欢迎来到人间》,生理感受就完全不同了——永无止境的煎熬、自我怀疑,一点点挣扎着从中爬出来,像是过了无限辛劳的一生。停滞,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推翻,手起刀落间初稿的30万字就被他自己删得所剩无几,又从小说的第二章重新写起,然后再推翻。直到小说在《收获》杂志上发表的前一天,他还删掉了结尾的两万字,调整了一整段情节的位置。其间有十几次想要放弃,终于还是写完了,也许“不疼”的刹那,是种动力。
《欢迎来到人间》的故事发生在2003年,主人公是第一医院泌尿外科的医生傅睿。他出身优越,父亲是医院的前任书记,母亲是播音员,家庭和睦。他在外科专业上拥有天分又不失勤奋。他的衬衣永远熨得平整,裤子上的两条裤缝清晰可见。他的目光剔透、安稳,毫无喧嚣,就连皮肤上都干净得没什么斑点。他成功,体面。肾移植手术是第一医院的临床重点,但“非典”以来的短短几个月,医院接连出现了六例术后死亡。而后,等待肾移植手术的15岁患者田菲迎来了属于她的肾源。又一次面对死亡之后,傅睿展现在我们眼前的行为逐渐趋近疯狂。
傅睿的原型来自2006年毕飞宇在《扬子晚报》上看到的一则报道:一个外科医生面对患者的死亡,疯了。但是他的身边没有一个人发现。他始终表现得像个天使,做好事,无微不至地关心所有人。直到医院里面出现了一个意外,医生的精神状况才最终暴露出来。报道探讨的是外科医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呼吁国内加强心理干预。而毕飞宇被戳中的地方在于,没有一个人发觉这个医生病了。竟然会这样?那接下来会怎样呢?
深夜2点,小说里的傅睿到病人老赵的家里,数脉搏、看舌苔,他害怕老赵会死;路边的哥白尼雕塑被倾倒的水泥淹没,他看到它窒息的表情、求助的目光,对它展开急救;在他眼里护士小蔡对爱情的选择是被迫的,她被侮辱、被损害,灵魂堕落,因此让她坐上了自己驾驶的帕萨特在足球场上疾速地绕行,他认定车子接近侧翻的离心力可以甩出小蔡灵魂里的污渍……他迷恋拯救,行为早已超出医生拯救病人的专业范畴。但是,傅睿身边所有的人都看不出他的问题,不把他当作病人,只是忙着做一件事——道德评判。他们认为,他的病不是病,是一种高尚者的姿态。他是一个天使。他们被感动,于是急于传播傅睿、再造傅睿、追随傅睿……
三联生活周刊:你不止一次说起写这本书的过程像是一场噩梦,其中还经过两次大幅的删掉重写,这部小说为什么会那么难呢?
毕飞宇:这个问题我其实回答过多次了,无非是知识性障碍以及我的个人处境,当然,还有疫情。我今天就和你重点说一说我的个人处境吧。你知道的,这部作品几乎涵盖了我的50岁至60岁,用孔夫子的说法,这部作品行进在我的“知天命”与“耳顺”之间。问题是,一个自以为“知天命”的人他“不知”天命了,一个有可能“耳顺”的人突然发现他的耳朵并没有那么柔软,这就糟糕了。我清楚地知道了一件事,我违背了孔夫子所建立的、我们中国人所延续的生命逻辑。我逆生长了吗?显然没有。但是,我的内心有逆动,它的力量是如此的巨大,它甚至毁灭了我过往的小说修辞。我突然就不会写了。不会写我当然沮丧,沮丧到了一定的程度,难免也会偏激,谁说偏激不会成就一个小说家呢?《欢迎来到人间》出版以后,兴奋的朋友有,对我表达陌生的人也有。可我不打算对任何人说抱歉,我从来没有承诺过任何人,我不会向你保证我永远容颜依旧。我的生活变了,我的感知与表达也变了,事情就是这么一个事情。我的秘密就是我的小说的秘密,我的答案就是我的小说的答案。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看来,傅睿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身边的很多人都把他视作天使,但事实上显然不是。你在书里写“小混混有小混混的仗义,小青皮有小青皮的血性,傅睿没有这些”。傅睿有的是什么?
毕飞宇:我个人所建构的写作常识是这样的,你最好写你熟悉的和了解的人。我以往的写作历史就是这样,这个常识成就了我,这个常识也构成了我的局限。我不熟悉这个人,我不了解这个人,但是,我意识到他的存在,我想完成他,这可以不可以呢?我再问一遍,我可以不可以呢?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肯放弃这个作品吗?不是我不答应,是我渴望让大家认识傅睿的愿望不答应,我一厢情愿地认为,大伙儿想见到这个人。这个人对你有价值。有一件事想必你是知道的,按照新书的出版流程,《欢迎来到人间》出版之后,我应该一天到晚对付媒体才是,卖书嘛。可这一次我有点恐惧,我非常害怕外部世界,其实我是害怕一个问题——傅睿是谁?这个问题就是你的“傅睿有的是什么”。我知道你会问我这个问题的,我的答案是我祝你好运。我希望你永远也不要和傅睿相遇,我祝愿你远离这个拯救者。我愿意和你做一个遥远的相约:多年之后,如果你一直没有遇上他,我必须恭喜你。如果你遇上了,我最大的愿望是你不要成为第二个小蔡。
三联生活周刊:傅睿一边有着疯狂的拯救欲望,一边在每一次被谬赞的时候,又都能感到那些讴歌的残暴,于是如芒在背,身体奇痒难耐。他对自己的认识是什么样的?
毕飞宇:我不知道啊,我只能猜,他也许就生活在他的自我设定里,这个自我设定就是“被需要”,这给了他无比巨大的能量和巨大的虚妄,他唯一的现实就是虚妄。我真的不知道他是如何认识自己的,也许他从来都没有在意过“自我认知”,我能告诉你的是我对他的感受,我害怕他。我希望《欢迎来到人间》是我的一个梦,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我希望梦醒了,我长长地舒出一口气,一切都平安无事。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傅睿做自己,会是什么样的?
毕飞宇:他做的就是自己,他一直在做自己,谁也没有改变他。
三联生活周刊:大多数人物在这部小说里出场的时候,用的都是自己的名字,但是胡海出现,基本用的都是小蔡对他的称呼“先生”,为什么是“先生”?
毕飞宇:我出生在1964年,在我的童年时代,“先生”是特指的,它的所指或者说意指是教师,或者教书匠。等“先生”突破了教师这层含义的时候,改革开放已经开始到了相当的程度,这个时候的“先生”不再是教师,差不多已经和世界接轨了,它有两个意思:男士或者丈夫。你看,仅仅是一个词的词义变化,“先生”也已经冲出了历史,成了那个时代的时代标志。回过头来再说小蔡,这是一个时刻渴望着与“时代”接轨的乡村女子,在两性问题上,她盼望着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关系。小说的情节显示,胡海一出场我就用了“先生”,它表明了胡海既是一个男士,也为后来他成为小蔡的“准丈夫”留下了足够的空间。我喜欢你这个问题。小说是无所不在的,作家要做的,就是告诉读者小说“在”哪里。在胡海和小蔡的关系当中,“先生”就是小说的“在”,当然也是小说的可能和勃勃的生机。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傅睿,书里有几个一笔带过的小人物的确让我更感兴趣,比如郭鼎荣、比如监控室的保安之类。
毕飞宇:小说是要塑造人物的,可我一直强调“关系”。我甚至认为,小说就是“关系”。我还认为,小说基本上不可能完成人物的塑造,所谓塑造人物,就是揭示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人的小说也许很难存在。哪怕小说里只有一个人,它也会出现他人的指向。那么,小说如何去完成人物呢?——呈现关系。电影也呈现人物关系的,它会按照人物的权重去分配主角和配角。在我看来,主角与配角在小说里并不存在,他们属于同一个小说的美学系统。他们是等值的、均衡的。看完了一部电影你可以这样说:哪个演员演得好,哪个演员没演好。小说可不是这样,要好,他们一起好,要不好,他们一起不好。这里头还有一个小说的道德问题,那就是你如何面对你作品中的人物。对我来说,我有一个基本的愿望,既然一个人物在我的小说里诞生了,我就有责任让他成立,甚至发光,至少,我必须保证他的小说生命。能对小说人物负责任的只有作者,这是虚构的道德。虚构是权力,行使权力就必须推崇道德。
三联生活周刊:说到结构,小说前后的语言风格、节奏的变化让它分裂成了两部分,但其中又有诸多呼应,能看出来这种变化是有意为之的,能不能说说为什么要这样写?
毕飞宇:我也算老作家了,阅读经验不可谓不丰富。如果你长期和编辑或者批评家打交道,有一句话你一定非常熟悉:“这小说写得不错,就是后半部坍塌了。”这是长篇小说最为顽固的综合征。《欢迎来到人间》在我手上的时间比较长,有两件事我是不能允许的:一、语言没顶住;二、“就是后半部坍塌了”。这个我是不能允许的,也可以说,是我对这部作品的基本要求。是的,这部小说的前后不是很统一,我能不能再花半年的时间让它的风格统一起来呢?一点问题都没有。可是,有两部作品对我的刺激太大了,一个是汪曾祺的短篇《受戒》,另一个则是伟大的《局外人》,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这两部作品的前后不统一才构成了它们恒久的魅力。我想我也可以的。事实上,相比较于上半部,作品后半部格外地饱满。这是我渴望的。有一个非常熟悉我作品的朋友这样对我说,看这部小说的后半部应该吃饱了,否则,真顶不住。这句话让我开心了一个晚上,我希望我的朋友永远有好胃口。 毕飞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