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会被抛弃吗?
作者:薛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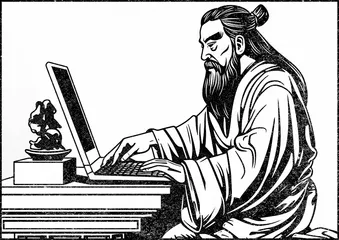 孔子教课是跟弟子对话、辩论,而他在授课之余,应该也有独自长时间读书、思考的时候,比如读《易经》《诗经》。普鲁斯特在《阅读的时日》一文中说,跟交谈不同,“读书时,我们每个人在接受他人思想交流的同时仍然保持孤独,即继续享受我们在孤独中享有的智性力量……对精神而言,阅读不过是最高贵的消遣,仅凭阅读和学识就能造就文质彬彬的心智。在阅读中,我们心灵的修养才得以形成”。
孔子教课是跟弟子对话、辩论,而他在授课之余,应该也有独自长时间读书、思考的时候,比如读《易经》《诗经》。普鲁斯特在《阅读的时日》一文中说,跟交谈不同,“读书时,我们每个人在接受他人思想交流的同时仍然保持孤独,即继续享受我们在孤独中享有的智性力量……对精神而言,阅读不过是最高贵的消遣,仅凭阅读和学识就能造就文质彬彬的心智。在阅读中,我们心灵的修养才得以形成”。学生经常看短视频,好像也能获取不少信息,但还会思考吗?《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西蒙·库珀在一篇文章中说,深度阅读的时代结束了。多家出版商、图书馆协会、学者签署的“卢布尔雅那读书宣言”说,批判性阅读、自觉阅读、慢阅读、长阅读减少了,如今人们大多在屏幕上读东西,这是肤浅、零散的阅读,“在手机上进行深度阅读就像用手机打网球一样困难”。而失去阅读能力的人也会失去思考能力,习惯于给复杂的问题提供简单的答案。
在屏幕上阅读时,我们的大脑要努力跟上眼睛。英国作家约翰·海利在《注意力危机》一书中说:“人们在生活中经历的最简单、最常见的心流形式之一是读书……对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读书是我们所经历的最深刻的专注形式。当我们在屏幕上阅读时,我们更倾向于浏览和略读,眼睛在信息上快速移动,以提取我们需要的内容。阅读不再是一种沉浸在另一个世界的愉悦,而变得更像是在一个繁忙的超市里跑来跑去,买自己需要的东西,然后离开。当我们开始从书本转向屏幕时,我们开始失去一些从书本中获得更深层次阅读的能力,而这反过来又使我们不太可能继续读书。就像你长胖后,锻炼就越来越难了。”更严重的恶性循环是,作者平时也是用屏幕看东西,其他作者看的都是这样的作者写出来的书。
牛津大学的莎士比亚专家爱玛·史密斯认为,我们的专注力也许并没有降低,只是转移了方向,深入阅读也是时代的产物,而不是人们主动的选择。“读书时沉浸式的专心并不是天生的、默认的模式。它也是习得的行为,是被一种新媒介推动的,被特定的历史和技术环境造就的。深入、专心的阅读是一种新技术的结果,那就是小说。18世纪中期,印刷铺印制的长篇小说也引发了道德恐慌。现在人们担心孩子不读书,而我们的先辈担心的是他们对小说上瘾,跟现实世界脱节,降低他们的视力和品德。”
在18世纪的阅读革命之前,人们是深入细致、反复地阅读少量作品,通常是道德或宗教劝诫的文字,这也是特定的态度和媒介决定的:在书页的边上写笔记、索引的出现帮助读者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页面,让人们能够像喜鹊一样阅读——收集那些闪亮的部分。16世纪的读者很少从头到尾看书,也不关注其复杂的叙事,而是摘录其中的金句和思想。“现代人对长篇电视剧和多集播客的狂热表明,我们并没有失去集中注意力的能力,只是把注意力转向了不同的媒体。当我们想集中注意力的时候,我们就会集中注意力。与专注相比,分心带来了不同的可能性,而不是更少的可能性。把一本书从头读到尾并不高尚。”
史密斯教授有些过于袒护当代人了。读书时我们会掩卷沉思,你看见过有人息屏思考吗?手机不换,屏幕不息。 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