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愤怒
作者:徐菁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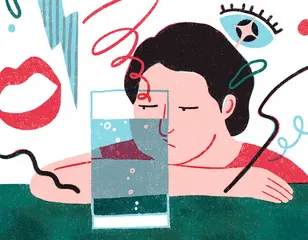 我们也许有一百种理由拒绝愤怒:愤怒会毁坏人际关系;愤怒使你不能专注于重要的事情;愤怒还很容易导致攻击行为,新闻中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多与愤怒有关;愤怒还损害你的身体健康:由于血压突然升高,血液流经动脉的力度加强,会使光滑的动脉血管壁受到磨损,产生凹痕,脂肪酸、葡萄糖及血液中的其他物质就会更容易粘在损坏的血管壁上。这就是所谓的动脉粥样硬化,它将导致冠心病、心肌缺血或其他严重的心脏病。
我们也许有一百种理由拒绝愤怒:愤怒会毁坏人际关系;愤怒使你不能专注于重要的事情;愤怒还很容易导致攻击行为,新闻中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多与愤怒有关;愤怒还损害你的身体健康:由于血压突然升高,血液流经动脉的力度加强,会使光滑的动脉血管壁受到磨损,产生凹痕,脂肪酸、葡萄糖及血液中的其他物质就会更容易粘在损坏的血管壁上。这就是所谓的动脉粥样硬化,它将导致冠心病、心肌缺血或其他严重的心脏病。时常发怒还会让你陷入痛苦的恶性循环:当你因愤怒而遭受损失时,很容易会变得心情沮丧,与此同时受到愤怒与抑郁情绪的折磨。这些不愉快,又可能将你带入下一次的愤怒。
但是,愤怒并非没有价值。如果你根本不会感到愤怒,那情况可能更糟糕。
人到中年的男子桑迪感到自己在生活中处处碰壁。他打算结束持续了十几年的婚姻。在这段婚姻里,他遭遇了无数带有敌意的批评和身体攻击。他与商业伙伴的关系模式也让他精疲力竭。因为对待合作伙伴,他也像对待妻子一样胆怯和恭顺。他没有办法取得事业上的成功。他是一个颇有才华的工程师,有一系列极具前景的发明。但是,他害怕接近投资者,在给重要的人打电话时就会焦虑,而且无法站在一群人面前描述他的发明。因为他害怕任何可能导致冲突或失败的事情。每当他预料到冲突可能会发生时,他就会逃避。
这是美国佩珀代因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路易斯·科佐利诺(Louis Cozolino)记录在书中的一个案例。科佐利诺有近40年的心理咨询工作经验。他发现,很多来访者的痛苦来源于他们在社会关系结构里是一个服从者。服从者的角色通常会走向两个极端。一种服从者被挫折和无力感压垮时,他们会产生无能为力的愤怒,然后把它发泄到身边最亲近、最脆弱的人身上,比如孩子、动物、伴侣。但其实更多时候,人们陷入了另一个极端:恐惧使人们无法意识到自己的愤怒。
桑迪的这种人际交往模式根植于他的家庭。他的父亲擅长身体虐待和情感虐待。直到桑迪离家上大学之前,父亲一直是他的恐惧的根源。他还有一个隐忍忠诚的母亲,哪怕牺牲自己的身体健康和情感健康,也要维系家庭的完整性。桑迪认同他的母亲,并接受了她在面对冲突时的回避行为。他成为一个深受控制的服从者。 作为孩子的时候,我们往往不被允许生气,必须掩藏自己的愤怒。尤其是那些和施虐的父母一同生活的小孩,对他们来说,隐藏和忘却愤怒,是为了生存必须做的事。科佐利诺指出,服从者地位的设定,在大脑中的记忆和储存与创伤经历类似。为了不激怒他们的“领导者”,服从者的大脑把自信和愤怒,等同于危险和恐惧。但当我们放弃愤怒时,我们也放弃了自信,放弃了让自己被他人看到的力量和能力。
作为孩子的时候,我们往往不被允许生气,必须掩藏自己的愤怒。尤其是那些和施虐的父母一同生活的小孩,对他们来说,隐藏和忘却愤怒,是为了生存必须做的事。科佐利诺指出,服从者地位的设定,在大脑中的记忆和储存与创伤经历类似。为了不激怒他们的“领导者”,服从者的大脑把自信和愤怒,等同于危险和恐惧。但当我们放弃愤怒时,我们也放弃了自信,放弃了让自己被他人看到的力量和能力。
在桑迪的这个案例里,科佐利诺在心理治疗中做的一件重要的事,就是让桑迪体验愤怒的感觉,重新认识自己。
科佐利诺让桑迪想象一个场景:孩子们到便利店买零食。突然,桑迪看到一个男人试图把他的女儿抓走。想象这个场景时,桑迪的眼里噙满了泪水,同时感到害怕和愤怒。最后,父爱占了上风,桑迪说,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在,就不可能让人带走自己的女儿。如果有必要,他会用牙齿把对方脖子上的血管咬开。
科佐利诺提示桑迪,他一直把自己视为懦夫,但这并不是他的全部形象,他需要记住此刻体会到的愤怒带来的力量。恐惧情绪偷走了桑迪的生命,现在他需要变成自己的领导者。
相比男性,女性更容易陷入桑迪的困境。美国女性心理学家哈丽特·勒纳(Harriet Lerner)指出,长久以来,女性被期待做一个养育者,负责抚慰、缔造及平和地稳住局面。取悦、保护和安抚好像是女性的天职。当女性直截了当地表达愤怒,尤其当这种愤怒指向男人时,会被认为是不得体、没有母性、缺乏性吸引力。各种语言中都存在着大量谴责女性愤怒的表达,比如泼妇、女魔头、母夜叉。愤怒的女人被视为危险的,而内疚、抑郁或自我怀疑的女人则被认为是正常的,因为在这些情况下,女性只是在和自己作对,不会采取行动,要求别人改变。“淑女”不擅长于体会愤怒,但她们是体验愧疚的专家。当她们感到压抑、受伤时,通过萌生内疚,得以摆脱对愤怒的觉察。
其实不论男女,“内核不稳”的人总是在纠结于一个问题:“究竟应该听谁的?”他们总在陷入自我怀疑:“一定是我做错了。”他们放弃做自己的“领导者”,因为他们对自我需求和自我价值判断不明。体会愤怒正是帮我们理解自己的重要帮手。心理学认为,大部分的愤怒情绪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其本质是被压抑的心理需求无法满足而产生的焦虑情绪。
愤怒也并非一定会产生破坏性的结果。麻省大学心理学教授詹姆斯·艾维利(James Averill)是最早发现愤怒的积极作用的心理学家之一。1977年,艾维利调查了一个名叫格林菲尔德的小镇(Greenfield)。这个中产阶级聚居的小镇有1.8万人,教堂数量是酒吧的两倍,是典型的宁静、宜居之地,艾维利原本认为,这里的居民一定脾气温顺。然而调查结果与此恰恰相反:大部分人经常为一些小事发怒——比如谁去扔垃圾、孩子几点回家、饭桌上的政治等。但是,这些愤怒实际上获得了不错的结果:双方事后会变得更愿意倾听、更放松。超过三分之二的被发火对象表示“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艾维利总结道:愤怒是信息密度最高的沟通方式之一,能够迫使我们彼此倾听、直面问题。
后来的一些心理学研究佐证了他的发现:人们通常会将权利和地位给予那些能够适度表达愤怒的人。人们会倾向于认为那些善于表达愤怒的人更有能力、更强大,适合成为领袖。在谈判中能够表达适度愤怒的人往往会得到更多自己想要的东西。
格林菲尔德小镇的秘密在哪里?艾维利说,居民们虽然时常愤怒,但他们知道如何理性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要。换句话说,学会愤怒,一是要感受它,二是要掌控它。
我们的逻辑和判断等理性思维依赖于大脑皮层,它是大脑的策略和控制中心。大脑边缘系统内有一个叫作杏仁核的小结构,它掌管着我们的自然生存本能——愤怒就是其中一种。杏仁核的反应比皮层更快。也不是每个人的大脑都经过了良好的训练,使得皮层能够很好地抑制杏仁核。因此,愤怒常常会转化为大喊大叫、不耐烦、沮丧和伤人的话。
一味的发泄不会让事情变好。发泄只会维持,甚至僵化一段关系中原有的规则和模式。哈丽特·勒纳说,当我们的怨气没有以清晰的语言表达出来,这不但不能唤起他人的同情,反而会带来嫌恶。我们由此感到更加难过、不公。这些回合下来,原本引起我们愤怒的问题不但没有被识别,我们还有可能成为替罪羊的不二人选。
哈丽特·勒纳给出的建议是,在感到愤怒的时候,我们应该问自己对的问题。一些人会问自己:“我的愤怒合理吗?”“我有权生气吗?”“我生气有什么用呢?”这些问题是错误的,它阻碍我们体验愤怒,促使我们觉得生气是不合理的,试图将愤怒阻挡在意识之外。愤怒的存在必然出于某些原因,理应得到我们的尊重和关注。
真正值得一问的问题是:“此时此刻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我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是什么?”“我想争取的是什么?”“哪些人应该对哪些事情负责?”“什么是我特别想要改变的?”“我愿意做什么,哪些我不愿做?”
这些问题看上去很简单,但只要你去思考它们,就会发现,其实每一个问题都很复杂。哈丽特·勒纳说:“当我们能够表达自己的感受,而不认为别人应当对我们的感受负责;当别人对我们做出某种回应时,我们也不会因此责备自己——这时,我们才能摆平愤怒,有所进取。”
(参考书籍:[美]路易斯·科佐利诺(Louis Cozolino):《心理治疗为什么有用:从疗愈心灵到改变大脑的神经机制》(Why Therapy Works: Using Our Minds to Change Our Brains),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23年版;[美]哈丽特·勒纳(Harriet Lerner):《愤怒之舞:亲密关系中情绪表达的艺术》(Dance of Anger: A Woman's Guide to Changing the Patterns of Intimate Relationships),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版) 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