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年:借书园
作者:卜键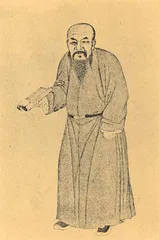 五征君中的周永年较为特别。他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书生,为方便世人阅读,曾发愿编纂《儒藏》,发愿多建借书园,皆未能实现;他在科举上蹉跎久之,42岁考中辛卯恩科二甲进士,却又与同年邵晋涵一样,得了个“归班铨选”,不异一瓢冷水。幸亏朝廷兴办《四库全书》,给了他一份差事,也给了一个人生大舞台,因此显得格外珍惜和认真。如果说五征君在众多纂修分校中是突出的,则永年在五人中应是用心和用功的第一人。
五征君中的周永年较为特别。他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书生,为方便世人阅读,曾发愿编纂《儒藏》,发愿多建借书园,皆未能实现;他在科举上蹉跎久之,42岁考中辛卯恩科二甲进士,却又与同年邵晋涵一样,得了个“归班铨选”,不异一瓢冷水。幸亏朝廷兴办《四库全书》,给了他一份差事,也给了一个人生大舞台,因此显得格外珍惜和认真。如果说五征君在众多纂修分校中是突出的,则永年在五人中应是用心和用功的第一人。关乎周永年家世生平的记载不多,仅知其祖籍浙江余姚,高祖一辈于明末移居济南,在军中担任都司,乃父周堂靠祖母、母亲抚育长大,后来做贸易,家境渐至丰裕。《续历城县志》说周堂生性节俭,身穿敝衣烂衫就上街,却舍得花钱给儿子永年买书。一次遇邻居诉苦,说挣点钱都给儿子还了赌债,他也跟着诉苦,说家里的钱都给儿子还了书债,街巷传为趣事。大学者沈起元主持泺源书院时,对周永年备加称许:“余来主泺源书院讲席,得周生永年,其文矫然,其气凝然。百无嗜好,独嗜书。历下古书不易得,生故贫,见则脱衣典质,务必得,得则卒业乃已。今所藏经史子集、二氏百家之书,已数千卷,皆能言其义者。”起元为康熙六十年二甲进士,选庶吉士,由吏部员外郎外任知府,仕至直隶布政使、光禄寺卿,后主持多家书院,识人多矣,而对永年极为欣赏,期许甚高,也透露出其家境已至拮据。济南南部多山,年轻学子周永年在30余里外的白云山般若寺侧建房(或租房)读书,号曰“林汲山房”,旁边有其他学子之舍如“爱山庐”等,沈起元也会应邀前来,师生同游,论学亦在其中。乾隆十九年考选贡生,泺源书院有27人入选,永年不在其内,沈起元有些意外,也只是要其学会承受。未久起元移教扬州,但一直关心永年的状况,闻知他因病迷恋上释道的养生术,有些着急,在信中写道:“年兄向有务博之病,近乃有逃虚之病,恐于身心毫无裨益耳。年兄前日只欲求养生却疾之术,遂惑于其说。愚昔二十四五岁尝大失血几殆,愚写非礼勿视四句于座右,时时体察,遂觉心清气静,病亦渐瘳。始悟心广体胖四字,吾儒具有养生之道,何必二氏也?”关切之情跃然纸上。
乾隆二十五年秋,周永年得中副贡,亦即登上了乡试的副榜,可以入国子监读书,却不知是否进京就读。那段时间,他的心思可能全在借书园上,不再以读书应试为主。周永年曾在与同学的信中追怀往事,说“弟少壮失学,今悔之而无及”,所指应是离院后的十余年,详情已不可尽知,推测应与其谋划和经营借书园相关。应是痛感在北方访书、借书和买书的不易,永年想兴建借书园,不是一所,而是一批,搜集儒学及各类书籍于其间,招收年轻学子,并延聘饱学之士讲授。据其好友桂馥记述:“先生于衣服饮食声色玩好一不问,但喜买书。有贾客出入大姓故家,得书辄归先生,凡积五万卷。先生见收藏家易散,有感于曹石仓及释道藏,作《儒藏说》。约余买田,筑借书园,祠汉经师伏生等,聚书其中,招致来学,苦力屈不就。顾余所得书,悉属之矣。”桂馥别号萧然山外史,曲阜人,训诂学家,小永年六岁。他在文中没说此事发生在何时何地,推测是永年30岁之后所为。周永年志向远大,一腔热血,然囊中羞涩,拉着好朋友一起干,结果是跌入自己挖的坑。今人称周永年为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先驱,诚哉斯言,但那需要强有力的资金支撑,恰恰又是他所缺乏的。
周永年的科举之路也充满坎坷,至乾隆三十五年秋才通过顺天乡试,已然41岁。他是为何和如何到顺天应试的,看不到记述,仅知考中第八名举人,次年辛卯恩科连捷进士,为二甲三十一名。同治《湘乡县志》卷十七,记该房师邓文泮阅卷时的喜悦,“辛卯分校礼闱,得山左一卷,诧为奇才,力荐于总裁,谓此必名士,及揭晓乃宿儒周永年也。相国刘文正公呼为巨眼”。曹锡宝在自撰年谱中,也称得“老名宿周永年等九人”。而以周永年的年龄,一般不会入选庶吉士,但不予授职,令回乡等待安排,也使之大失所望,心绪烦乱。桂馥时在京师,作《送周进士永年》:
声名动日下,君心冲若虚。脱然返故乡,惟载满船书。徂徕山色好,独往治田庐。石室数万卷,愿为后人储。传之待其人,犹胜儿孙愚。来者未可知,此心与之俱……
可知二人分别之际,说的最多的还是借书园。回到济南后,他又开始为之奔波选址,所选之地改为泰山北麓的肃然山。永年自记:“壬辰之秋,南川家松崖明府将为余置别业,建借书园。余素耳肃然山阳丘壑林麓之美,因往游焉。”似乎找到了一个有力者,而最后仍是未成。
那时的(当然也包括现在的)文人绝大多数是务实的,周永年则始终怀抱理想,借书园就是他的人生理想,是他的梦。
乾隆三十八年春接到朝廷征召,与邵晋涵、戴震等入四库馆编书,对周永年的命运带来巨大改变。他是一个真正的读书种子,最大的乐趣就在于买书、抄书、读书和聚书,这次算是掉进了书窝里,不仅可从《永乐大典》中辑录珍稀古本,也得窥内府和各省呈送之书,眼界豁然开朗。而其兴建借书园、招收贫寒学子就读的理念并未失去,常对不多几位好友谈起,其中就包括游学京师的章学诚。章氏在为他的书目题序,在为之书传时都提到借书园,施以重墨,曰:
藉书园者,书昌之志也。书昌故温饱,橐馁于书,积卷殆近十万,不欲自私,故以藉书名园。藉者,借也。尝以其意,请余为藉书目录之序。余序之曰:书昌尝患学之不明,由于书之不备;书之不备,由于聚之无方。故竭数十年博采旁搜之力,弃产营书,久而始萃。而旧藏古椠,缮钞稀觏之本,亦略具焉。然书昌之志,盖欲构室而藏,托之名山;又欲强有力者为之赡其经费,立为法守,而使学者于以习其业,传钞者于以流通其书,而儒家乃失其法,因著儒藏之说十八篇,冠于书首,以为永久法式。呜呼,书昌于斯,可谓勤矣!
由于邵晋涵的关系,章学诚与周永年相识并成为挚交,对他的为人为学大加赞扬,也不无惋惜。在由浙东走出的学诚眼中,永年的图书收藏实在算不上珍稀,其兴办借书园的设想也有些迂,但那种传承儒家经典和普惠的精神,那份专注执着,则使之深深感动。 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