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酉阳杂俎》:人情化的妖怪
作者:艾江涛 唐人小说,在传统志怪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传奇一体,与诗歌一起,成为后世难以企及的高峰。然而,唐人志怪同样不可忽略,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这部记录仙佛鬼怪、人事乃至动植物、酒食的包罗万象的笔记小说,在鲁迅眼中,“所涉既广,遂多珍异,为世爱玩,与传奇并驱争先矣”。
唐人小说,在传统志怪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传奇一体,与诗歌一起,成为后世难以企及的高峰。然而,唐人志怪同样不可忽略,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这部记录仙佛鬼怪、人事乃至动植物、酒食的包罗万象的笔记小说,在鲁迅眼中,“所涉既广,遂多珍异,为世爱玩,与传奇并驱争先矣”。《酉阳杂俎》的驳杂,从书名也可窥见一斑。“酉阳”典出梁元帝“访酉阳之逸典”,即藏诸世外的秘籍奇书;“俎”本为古代祭祀宴会中盛放牲肉的礼器,“杂俎”则意为天地之间凡百奇味,杂然前陈,无所不包。这部驳杂的大书中,历来为研究小说者所推重的主要是以“诺皋”为题,包括《诺皋记》(上下)、《支诺皋》(上中下)中记录鬼神妖怪的志怪,其中一些篇目因为篇幅铺陈,叙述生动,纳入唐传奇也无不可。说到这里,又得谈到“诺皋”一题的含义,据近人谭嗣同研究,其为巫师在诵念禁咒召唤鬼神时的发语辞。生活在中晚唐时期的段成式,出身世家,青年时期随官至宰相的父亲流宦各方,后以荫入仕,曾任秘书省校书郎。他广泛游历,加之遍阅密藏,博学强记,因此让《酉阳杂俎》这本书在词句上颇为奥博,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它更为广泛的传布。
《酉阳杂俎》与之前的志怪描写有何不同?学者刘勇强告诉我,他在研究神怪小说时,特别强调其背后信仰背景的变化。“六朝志怪小说,一般的认识,会引用干宝在《搜神记》序言中的看法,‘发明神道之不诬’,也就是说他们总体倾向于相信神异的东西。唐代佛教、道教等宗教都有了一些变化,从宗教角度讲,唐人对鬼神谱系的利用,更加自觉化、体系化,这其实与理性化联系在一起,他们有意识地利用神怪形象,弥补想象的缺失,神怪想象其实提供了社会书写的一种方式。”
在《酉阳杂俎》卷八中,段成式记载了一段话:“成式以君子‘耻一物而不知’,陶贞白每云‘一事不知,以为深耻’。况相定黥布当王,淫著红花欲落,刑之墨属,布在典册乎?偶录所记,寄同志,愁者一展眉头也。”刘勇强将此视为段成式编纂志怪小说的原则:“一、重视知识性;二、关注真实性,补文献之阙;三、兼顾娱乐性。”从中不难看出,既有对传统志怪写作的继承,又有近世小说注重娱乐、令人展眉的特点。这其实与中晚唐的社会风气有着极大关系,在不少学者看来,这也是唐代小说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
“安史之乱”爆发的第二年,玄宗皇帝在四川剑阁颁布《幸普安郡制》,自此各地藩镇正式拥有财产与辟署权,众多节度使府大量征辟人才,大量士子流动于藩镇幕府之间,也使他们相互交流奇闻趣事的机会大大增加。李鹏飞在《唐代小说繁荣的原因新探》中就谈道:“如果统计一下中晚唐小说作者的生平经历,就会发现绝大部分人都有过入幕任职的经历,比如李公佐、沈亚之、牛僧孺、段成式这些著名小说家都是如此。”士子们相互交流逸闻,形诸笔端,成为传奇志怪;反过来,有意识地搜集编纂小说集,也具有应付在闲谈场合讲故事的需要。段成式所谓“寄同志,愁者一展眉头”,当作此观。士子们之间编纂传奇志怪,互相传看,作为谈资,倒与诗歌唱和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小说创作也由此一新。那么,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记录的妖怪,究竟有何不同呢?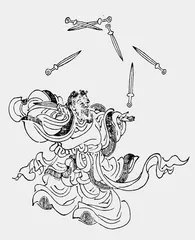 翻开《酉阳杂俎》的诺皋篇,会发现其中有不少恐怖的妖怪故事,这也符合人们对妖怪的传统想象。《续集卷二·支诺皋中》便记录了这样一则耸人的故事:唐贞元年间,家住望苑驿附近的百姓王申,经常在夏天送浆水给路人喝,他13岁的儿子也经常一起帮忙照顾客人。一天,一个穿着绿色短衣、头戴白巾的年轻女子路过讨食,自称丈夫已经去世,服丧期满,要去马嵬驿走亲戚。王申于是留她吃饭,当晚还留她过夜。王申的妻子请她帮忙缝衣服,看她手工精妙,特别喜欢,两口子一商量,就问她是否愿意留下做儿媳。女子爽快答应后,王申当晚就为两人举办婚礼。睡到半夜,王申的妻子忽然梦到儿子披头散发哭诉:“我快被吃光了。”妻子要起身去看,王申还叱责她多虑,可她刚睡下,又梦到相同情形。两口子打开儿子房门,发现有个怪物圆瞪双眼,齿长如凿,遍体蓝色,夺门而出,再看他们的儿子,已被吃得只剩下头骨和头发。
翻开《酉阳杂俎》的诺皋篇,会发现其中有不少恐怖的妖怪故事,这也符合人们对妖怪的传统想象。《续集卷二·支诺皋中》便记录了这样一则耸人的故事:唐贞元年间,家住望苑驿附近的百姓王申,经常在夏天送浆水给路人喝,他13岁的儿子也经常一起帮忙照顾客人。一天,一个穿着绿色短衣、头戴白巾的年轻女子路过讨食,自称丈夫已经去世,服丧期满,要去马嵬驿走亲戚。王申于是留她吃饭,当晚还留她过夜。王申的妻子请她帮忙缝衣服,看她手工精妙,特别喜欢,两口子一商量,就问她是否愿意留下做儿媳。女子爽快答应后,王申当晚就为两人举办婚礼。睡到半夜,王申的妻子忽然梦到儿子披头散发哭诉:“我快被吃光了。”妻子要起身去看,王申还叱责她多虑,可她刚睡下,又梦到相同情形。两口子打开儿子房门,发现有个怪物圆瞪双眼,齿长如凿,遍体蓝色,夺门而出,再看他们的儿子,已被吃得只剩下头骨和头发。
在前集卷十四《诺皋记上》的一则大历年间的记述中,一位士人在京城生病去世后,妻子柳氏搬到丈夫在渭南的庄园居住。一天夜里,家中婢女被一个长着獠牙、嘴大如簸箕的白衣老者啃食殆尽,只剩骨头。几个月后,柳氏被一颗不断变大的胡桃,把头夹得四分五裂,血肉横飞。这些故事中,段成式对妖怪的描写非常具体,令人感到恐怖。
不过,在《酉阳杂俎》中,让我印象格外深的还有不少非常有趣、富有人情化的妖怪。这些妖怪上门的目的,颇有点像后来《聊斋志异》中的狐妖鬼怪,多少出于寂寞或者对士人的钦慕,并没有什么恶意。
在前集卷十四《诺皋记上》中便有这样一个可爱的木耳精。唐代名臣郭代公曾在山间隐居,半夜时,房间忽然出现一个人脸如圆盘,在灯光下眨着眼睛。代公毫无惧色,慢悠悠地以笔蘸墨,在它的面颊上题写了一句自己的得意之作:“久戍人偏老,长征马不肥。”写完之后郭代公反复吟诵,怪物便消失不见了。几天后,郭代公跟着樵夫在山间散步,看见一棵大树上长着有几斗大的白木耳,再一看,他题写的诗句还在上面。
在续集卷一《支诺皋上》中,所描写的树精则有些憨态可掬。话说在山间一座寺院中,智通和尚常常持念《法华经》入定。一天夜间,智通正在念经,忽然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如是三晚。智通终于忍耐不住,回话道:“你喊我何事,不妨进屋说话。”只见进来一个六尺多高、黑衣青面、长着鼓目大嘴的怪物,见了智通还合掌行礼。智通端详了半天,让它烤火。怪物坐下来烤火,智通只管念经。那怪物在温暖的炉火边竟打鼾入睡。智通于是将炭火塞进它的嘴巴,怪物疼后起身跑了,还在门槛上摔了一跤,掉下一块树皮。天亮后,智通带人在后山找寻,发现一棵大青铜树,刚好掉了一块树皮,树干半腰还有炭火发出的火光。智通烧树之后,怪物自此绝迹。
这类妖怪形象的变化,在刘勇强看来,背后有信仰背景的变化。“在魏晋时期,物老成精,所有的东西年头久了,都可能成精作怪,而且成精以后,妖祟肯定要害人。这样一种观念,可能到唐代有些变化,有些小说在处理妖怪形象时,可能并不会特别渲染它的恐怖、危害性的一面,会描写它与普通人相似的情感特点。”
有唐一代,社会开放,中外文化交流活跃。《酉阳杂俎》中多次出现的夜(野)叉,便取自域外佛典。在前集卷十四《诺皋记上》中记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夜叉形象。在这个故事中,外形凶恶又有奇术异能的夜叉,在梦中将一个村女掳走为妻,在村女发现它的真实身份后,坚持把她送回,同时谢绝与她同居人间,因为这样便会给村子带来瘟疫,后来它又授村女青石解毒,分明是一个不失多情、谨守缘分的妖怪形象。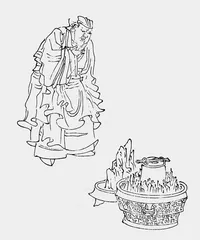 尽管段成式笔下的妖怪形象已开始跳脱出传统妖怪害人的窠臼,接着的问题却是,人与妖究竟能否和平共处?
尽管段成式笔下的妖怪形象已开始跳脱出传统妖怪害人的窠臼,接着的问题却是,人与妖究竟能否和平共处?
在《酉阳杂俎》中,我们虽能发现许多具有人情化的妖怪形象,但人妖殊途,就算妖怪不害人,害怕它们作祟的人类多半也会除之而后快。在前集卷十五《诺皋记下》中,一位寄居在亲友庄园修习学业的士子,因为没有礼遇上门陪伴的壁虎精,被拉入壁虎王国叱责,恐惧的士子谢罪之后才被放还。天亮以后,士子在墙外土堆中挖到十多石的壁虎,一把火将其烧光。前文提到的树精,最后的结局也是被智通和尚一把火烧掉。
但有一些篇目中,段成式所描写的精怪已有人的情感,面对这些精怪遇难,故事的主人公不再果断除之,而是对其充满同情。前集卷十四《诺皋记上》中便记述了一个虾精组成的“长须国”的故事。武周时期,有位士人随同新罗使节乘船,被大风吹到一个叫长须国的地方。士人在那里备受礼遇,还被招为驸马。生活十多年后,士人还和公主生了一儿二女,唯一让他不满的地方是,妻子也像这个国家所有人一样,长着胡须。一次宴会上,他忍不住赋诗一首:“花无蕊不美,女无须就丑。丈人试让拔完,未必不如有须。”后来王国即将遭难,国王因为士子来自大唐,派他向东海龙王求救。士子到那儿才发现,长须国的国民全是龙王每月所食的虾。见到在锅中蹦跳求救的虾精,士人不觉悲从中来,潸然落泪,后来在他的请求下,虾王一家被放走,士子也在龙王护送下返回中土。
可见在这个故事中,人类与虾精共同生活,不仅没有损害,还可结婚生子。而在上文夜叉的故事中,与夜叉生活几年的女子,在回家后则需要将夜叉赠她的青石磨成粉末服下,排泄出一斗多青泥样的秽物,方能解毒。
不论是人妖还是人鬼结合,人类最大的担心莫过于损害身体。在唐传奇《任氏传》中,狐狸精任氏重情重义,为了郎君最后不惜身死。她便谈到人们对精怪通常的认识:“大凡我们这一类人,被人厌恶忌讳的原因,不是别的,为的是会伤人。我却不是这样的。如果您不嫌弃,我愿终身侍奉您。”
人情化的妖怪描写,或许正是唐代志怪的最大贡献。与传奇一起,它们共同指向那个即将没落的盛世所拥有的豪情、义气、豁朗。人妖虽然殊途,却自此多了一份温情。
(本文参考段成式著、张仲裁译注《酉阳杂俎》) 妖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