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初到北大
作者:吴琪/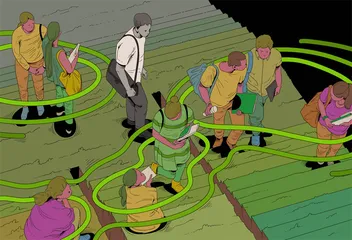 吴谢宇是福州一中最耀眼的学生,高考前,福州一中的校长推荐了他,他成为北京大学的自主招生的目标。吴谢宇的大学同班同学林贤春,也是通过自主招生进北大的,她回忆起那时候的情景,北大招生组把要报北大的同学带到酒店的广场,然后挨个问:“你排名是全省第几?”她高考所在的地区是考后填报志愿,招生老师跟大家说:第一档是光华学院、法学院;第二档是社科,就是“政管国关”;第三档是纯人文的,文史哲。老师的意思是,你考在后面的,就别想报前面的。“前面的就业好,说出去又好听。”林贤春说,“北大招生组也有KPI,就是他们要招到更好的学生,和另外一所大学竞争生源。他们在不同的地区招生时,要想很多办法。”
吴谢宇是福州一中最耀眼的学生,高考前,福州一中的校长推荐了他,他成为北京大学的自主招生的目标。吴谢宇的大学同班同学林贤春,也是通过自主招生进北大的,她回忆起那时候的情景,北大招生组把要报北大的同学带到酒店的广场,然后挨个问:“你排名是全省第几?”她高考所在的地区是考后填报志愿,招生老师跟大家说:第一档是光华学院、法学院;第二档是社科,就是“政管国关”;第三档是纯人文的,文史哲。老师的意思是,你考在后面的,就别想报前面的。“前面的就业好,说出去又好听。”林贤春说,“北大招生组也有KPI,就是他们要招到更好的学生,和另外一所大学竞争生源。他们在不同的地区招生时,要想很多办法。”谢天琴后来向马老师提到,选北大的经济学院,因为这是“最好的”。谢天琴的语气很平淡,但有一丝忍不住的自豪,“都是小宇和我商量着定的”。北大经济学院的自主招生需要面试,那时候谢天琴正在带高三毕业班,工作负责的她不愿意请假。所以2012年初,马老师带着吴谢宇到北大走了一趟。这一趟出门,马老师对小宇评价很高,看他在飞机上跟空姐聊天,在北京跟饭店服务员搭话,觉得他比一般孩子成熟,出门办事很老练。吴谢宇爱学习的形象仍然很稳,“他背着好大一个书包,特别沉,全部是各种深奥的书”。
吴志坚单位在北京的分公司,还特意把职工考上北京的孩子们,召集在一起见了一次。吴谢宇和另一个男孩,都是通过提前招生,定下了北京的好学校。在和爸爸同事老王聊天的过程中,吴谢宇显得特别大方自信,一副知识非常渊博的样子,另一个同龄人似乎怯场得多。老王后来向张力文转述时,直夸吴谢宇,张力文听了也很高兴。
吴谢宇顺利通过了面试,自主招生这关过了,经济学院录取他的时候,会在他高考成绩上加60分。北大通过自主招生的方式,尽力把全国最好的生源给提前“掐尖”。虽然高考前就定下了这条路,但真要考试了,吴谢宇心理素质的不足体现了出来,他后来在自述材料中说,他把高考看成最为重要的一场战役。高考总复习时,他总是觉得心脏难受。谢天琴带他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只是心律不齐,但吴谢宇还是觉得很不舒服,住院了一段时间。
“我高考考砸了,省里才100多名,比原来退步太多,妈妈没说什么,但我总觉得妈妈对我失望了。”多年后提起自己的高考成绩,吴谢宇仍然很不满意。由于有自主招生的加分,他顺利进了北大经济学院。但是对吴谢宇来说,似乎绝对高分才重要,即使上大学的结果是很好的,他也沉浸在对分数的不满当中。分数不仅仅是手段,对他意味着绝对价值。
为什么要学经济呢?吴谢宇的高中室友说,虽然他和吴谢宇的化学成绩都很好,但大学都没读化学。那时候流行学经管,吴谢宇大学时向这个同学借学术期刊账号,聊天时吴谢宇说他以后不想工作,想做教授。
吴谢宇的大学同学林贤春说,她觉得她选经济学院,仅仅因为这是热门专业,高分才能去读。“我们之前从来没接触过职业,两三天时间定个志愿,学起来就是好多年。”等以后明白过来,很多人会觉得报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专业,一开始就犯错了。“怎么保证选一个喜欢的专业?如果想转专业该怎么做?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高中的时候学得好,分数高。至于喜不喜欢,好像没几个人去想这个问题。”
对于考进北大这样一件人生大事,谢天琴似乎没有向儿子表达过肯定。2021年给小姨写信的时候,吴谢宇还沉浸在失败的体验中,认为妈妈很不满,“我就是台考试机器,除了考试我什么都不会,除了能考第一名,我一无是处,考第一名就是我对妈妈的唯一意义,是我让妈妈为我骄傲的唯一方式,一旦考不了第一名,我就对妈妈失去了一切意义了”。
但在外人看来,没有感觉谢天琴有任何不满。2012年秋天,她把儿子送到北大上学。吴谢宇的寝室四人一间,刚好都是从福建考来的,同学之外还多层老乡关系。杨冬明和吴谢宇一屋,他记得谢天琴给吴谢宇打扫柜子,擦得很干净,底部和侧面都贴上墙纸一样的东西。杨冬明的柜子和吴谢宇挨着,谢天琴也给打扫得干干净净。杨冬明对谢天琴的印象是,“瘦瘦的,戴个眼镜,比较吃苦耐劳的那种,不是能言善道的家长”。杨冬明之前多次到过北京,所以上大学没让父母送,自己拿着行李就来了。
在新生的破冰活动中,很多寝室都选择了唱歌,吴谢宇寝室是跳海带舞,给一些同学留下了印象,“觉得他们还挺有新意的”。 18岁的吴谢宇进入了一个更大的同龄人世界。从地理空间上看,他从福州到了北京,从管理严格的高中宿舍到了宽松得多的大学校园。全国各地的学霸们来到这里,将共同度过18岁到22岁的人生,他们以出色的考试能力得到了北大的入门券。大学到底能给一个人的人生带来什么?一群优秀的年轻人只是在这里竞争分数,还是真的发生头脑和灵魂间的碰撞?新生们并不知晓。
18岁的吴谢宇进入了一个更大的同龄人世界。从地理空间上看,他从福州到了北京,从管理严格的高中宿舍到了宽松得多的大学校园。全国各地的学霸们来到这里,将共同度过18岁到22岁的人生,他们以出色的考试能力得到了北大的入门券。大学到底能给一个人的人生带来什么?一群优秀的年轻人只是在这里竞争分数,还是真的发生头脑和灵魂间的碰撞?新生们并不知晓。
经济学院180人左右,6个班,吴谢宇的作息时间非常固定,体现了少见的纪律性。他每天晚上11:00一定会躺到床上去,早上7:00一定会起床,周末也不会有太大变化。室友偶尔打游戏,但吴谢宇从不打。杨冬明说:“整个学院来看,我觉得这种人都是很少见的。他会把自己的生活列成一个表,心里好像有一个表。”
虽然大学具体成绩不公布,但大家也能感觉到,一年级的时候,吴谢宇的成绩在班上排前三,在年级180名学生里边,他能排到前10%。很多同学面对考试都是临时抱佛脚,考前猛冲刺,但吴谢宇是那种细水长流的类型,一直在学。他不去教室上自习,基本都是待在寝室里学习。
吴谢宇的师兄李又廷提到,北大还有一种学生,大学之前被压制了,老师和家长不让打游戏。他们进大学后买的是高配电脑,显卡特别好,上面装了十几二十个游戏。这样的学生很快就挂科三四门,最终被北大退学。但吴谢宇是完全不同的类型,他一直延续着高中勤奋的学习状态,把大一读成了“高四”。
吴谢宇的精神状态是饱满的,同学发现他干什么事情都很专注。哪怕是大一上学期的歌咏比赛,一般同学很不在意,但他“唱得特别专注,而且是排练的时候,在一排人里面特别用力、特别突出”。
北大经济学院的学生,在大学二年级分专业。杨冬明选了金融系,吴谢宇是在经济系。杨冬明说,前两年大家基本处于体验大学的状态,一般不会先定死目标。本科毕业之后,无非是直接工作、国内升学或是出国。国内升学和出国升学又可以继续分成,你是走硕士还是直接读博士?如果希望今后在高校谋取一个教职,就应该选择直接去读博士。对于吴谢宇的多数同学来说,这条路并不急着求个答案,很多人在大三甚至大四才确定怎么发展。
而吴谢宇显得目标清晰而明确,没有一般新生的犹豫和试探。他看重每门课的学习,大学二年级开始准备托福和雅思。在大家看来,他的目标是出国深造,进入学界,谋取一个高校的教职。他没有主动说这个事儿,但杨冬明说:“我们平时开玩笑,就管他叫‘教授’或者是‘大师’,总觉得他未来会是一个在高校里任职的学究型人物。我们跟他说,‘你以后当教授给我小孩写个推荐信’。”另外一个同学告诉我们,“我记得有老师夸他,说他很有才华。不是一个两个,是很多老师都还挺喜欢他,会在课上表扬”。
吴谢宇表现得也很愿意帮别人学习。他上课做的笔记,愿意分享给同学。如果有人问他问题,他也毫无保留地回答。杨冬明记得,有一门课“是那种德高望重的老师,讲课的信息量非常大”。吴谢宇去现场听了几次,他觉得这个课程很重要,现场听课会漏一些东西,所以他就提出和室友来分工。早上8点的课,他问室友能不能早点去,往前坐,把老师讲课的内容录下来。之后他在宿舍慢慢听录音,他觉得听录音的过程可以停下来记笔记,更有效率。吴谢宇把老师讲的内容整理出一个文字稿,分享给室友。“他这方面性格非常好,很哥们儿,给人有求必应的感觉。”
一名女同学也记得,吴谢宇学业上很主动,很多同学只选经院课,但他选了光华的课。“我记得他发过朋友圈,是营销学原理。”非典型的北大生
选“营销学原理”这门课,在高吴谢宇两届的李又廷看来,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这门选修课有120人到150人的规模,低年级的学生只占15%左右。虽然算不上是一门“虐课”,但是“对于大一大二的菜鸟来说,肯定不会轻松”。
吴谢宇成了课堂上最活跃的学生,每堂课上发言,李又廷强调说,“the only one”。吴谢宇一定坐在前两排,穿着类似POLO衫一样的绿领衣服,下摆塞进裤子里,系一条皮带。后来天气冷了,吴谢宇常穿暗红色或深绿色的高领毛衣。他每次都会站起来回答问题,音调高,情绪高昂,全班每个同学都能听到他的声音。
他给同学留下勇于表达的印象,即便想法不成熟,吴谢宇也会在委婉表达自己的“不自信”之后,滔滔不绝说出来。他的表达总是启发一轮又一轮的课堂思考和大讨论。李又廷说,像他自己当时作为大四的学生,工作已经找好了,对这门课就不太积极,也懒得与老师互动。吴谢宇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感染力,回答问题的准确率很高,而且始终保持着高度的专注力和鲜明的想法,他也不吝大胆质疑老师的观点。这门课的老师是位著名教授,非常忙,这种大课叫不出几位同学的名字。但是他很快就记住了吴谢宇的名字,仅仅在第二次或是第三次上课,就亲切地叫他“谢宇”。李又廷说:“某种程度上来说,都让人怀疑吴谢宇是这门课请来的托儿。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张力文记得,吴谢宇专门为学好营销学原理课程,给他打过电话。在大学期间,吴谢宇遇到逢年过节或是自己有了好的成绩,会给爸爸的几位朋友发个信息,这几位叔叔感觉他很懂事。张力文做了多年的销售工作,所以吴谢宇认为应该向他请教,营销的根本原理是什么,有哪些典型的案例。吴谢宇给张力文打过很长的电话探讨问题,后来还给张力文发来邮件,详细地讲自己对这门课的理解,让张力文印象深刻。
在活跃表现的背后,同学也能感觉到吴谢宇的一点炫耀之心。“老师抛一个问题出来的话,大家三四句话都能讲清楚的,他会描述得特别细致,把老师的问题进行下一步的拆解。这样是在体现他逻辑的清晰和结构化,多多少少能让人感觉到,他有一种寻求老师认可和表扬的心态。”李又廷觉得吴谢宇是在用中学生模式,过大学生生活。这样的学生是中学模式的受益者,所以也本能地依赖过去的方式。
但吴谢宇表现出来的能力,还是显而易见的。营销学原理之外,老师还讲了很多商业案例,通过大量实证的案例分析,来讲这门课。吴谢宇回答问题的旁征博引,经过了自己的融合思考,也研究了一些类似的案例来分析和举证,李又廷说:“他不是本本主义,如果只知道读死书,到达不了他的深度。”
大学里,一部分学生在课堂上表现活跃,他们积极回答问题,频繁与教授沟通,最后拿一个很高的绩点。一旦成绩到手,就不会再跟教授产生任何交集。他们感兴趣的是高分,而不是这门课本身。吴谢宇是否真的对营销学感兴趣,同学们也不了解,但是从他在这门课从头到尾高投入的表现来说,他确实对学习很认真。
李又廷一方面认同吴谢宇在课堂上表现出的能力,一方面又坚定地认为,“他是一个不太典型的北大学生”。他说,如果说一般社会是一个纺锤形结构,头部和底部都很尖,那么北大学生的构成是反过来的。他觉得北大顶部拔尖的人多,尾部的人也多,中间这种“上不去也下不来的”,占比很小。“真正的大神,上课的时候基本都是不吭声的。” 在外形上,吴谢宇比较朴素,同学说他穿衣服以实用为主,羽绒就是羽绒服,短袖就是短袖,颜色一般是纯色系,没有要彰显个性的样子。杨冬明说:“我们大学生自己去买衣服都喜欢标新立异,尽量别大家一样。”吴谢宇的衣服是他妈妈买好后,从老家寄过来的。
在外形上,吴谢宇比较朴素,同学说他穿衣服以实用为主,羽绒就是羽绒服,短袖就是短袖,颜色一般是纯色系,没有要彰显个性的样子。杨冬明说:“我们大学生自己去买衣服都喜欢标新立异,尽量别大家一样。”吴谢宇的衣服是他妈妈买好后,从老家寄过来的。
大一大二的时候,吴谢宇同寝室的同学经常一起去食堂吃饭。但是大家从来没有一起外出玩过。室友之间,既不会聊各自发展的打算,也不聊家里的事。杨冬明解释这种界限感,“毕竟家庭的事情,怕问到一些人家不方便说的情况”。所以大家也不知道,吴谢宇的爸爸在他高中时去世了。吴谢宇也从来没有提过父亲。从他去食堂吃饭来看,他是比较节俭的。大家可能都会偏向于选肉菜,吴谢宇吃的素菜多一些。他很少吃一份份的小炒,基本上去窗口一格一格地打菜。
这个时期的吴谢宇,情绪上显得比较开朗。但是当几年后吴谢宇弑母的新闻让大家深感震惊后,再回忆起吴谢宇,杨冬明觉得,“他平时见到一个人,很热情地打招呼,其实我觉得只能说是他很有礼貌。他上来就拍你肩膀,感觉他跟你很亲近,但并没有分享自己内心的东西。聊天的时候,他很少把话题转移到自己身上”。
吴谢宇确实不会与人进行情感交流。即使他每天都要跟妈妈打电话,看上去比一般母子亲密很多,多年后他才意识到,事实上他跟妈妈之间始终没有真的去交流内心想法,这似乎是一种他们母子都无法具有的能力。
上北大后,每天晚上一个固定时间,吴谢宇会到阳台或走廊上,给妈妈打电话。杨冬明说,“雷打不动”。汇报的内容很详细,比如说今天上了什么课、晚饭吃了什么,但是基本是在说事情,而不是谈论感受和内心想法。同学们也弄不清,到底是吴谢宇主动要打这些电话,还是他妈妈有要求。大家也开玩笑问过,“为什么你这么大,还跟你妈汇报这么多?”吴谢宇没说什么。
吴谢宇认为妈妈非常需要他,或许是他心理上离不开妈妈的一种体现。2013年3月6日,吴谢宇在人人网上转发了一段话:“如果拿你身上20斤肉换取母亲的10年长寿,你愿意吗?”他借此表达了自己极度地爱妈妈。
高中住校的三年时光,吴谢宇在地理上距离妈妈远了,他却并没有体现出任何独立的愿望。本来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借着离开父母的机会,向外探索世界和向内体察自己,才是成长的必要阶段。但是不管吴谢宇走多远,他的内心世界,似乎永远拘禁在从小长大的那套房子里。一个个体把握自己人生的主动性,在他身上看不出来,即使他已经是北大的学生。
2021年在跟舅舅写信时,他提到自己的依赖,“我已经不是一个小孩了,过去我总不愿长大,躲在妈妈的羽翼之下依赖着妈妈,在身边同龄人已经成长成熟承担起自己责任的时候,我却还不肯自立自强”。
在人生早期,谢天琴对儿子严格管束,使他的心思基本花在了学习上,没有真实的人际交往。根据马老师的表述,随着吴谢宇成绩越来越好,谢天琴对儿子没有太多要求。但是吴谢宇似乎很不习惯妈妈不提要求,他后来在给小姨的信里提到,考上北大都不能让妈妈满意了,“到大学我拼了命也考不了第一名了,妈妈没说什么,但我总觉得妈妈对我失望了”。
根据吴谢宇的自述材料,他在头脑里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他对妈妈的唯一意义就是考第一名,如果妈妈不提要求,就是放弃自己了。虽然已经在北京上了大学,吴谢宇对自己价值的认知,仍然停留在那个试图讨好妈妈的幼童心理上。就像他提到非常害怕面对病重的父亲一样,吴谢宇对于自己走向独立的恐惧也很大。妈妈对他来说,既是一个真实的个体,也是一种逃遁现实的情感依赖。有妈妈在,他的自我似乎永远不需要破壳而出。而一旦没有了挡在他和现实之间的“妈妈”,他的内心就很容易失去平衡。
吴谢宇的一位同学任雯,大学期间没跟他直接交流过,她反而是通过各种媒体报道了解吴谢宇的内心世界后,觉得仅仅就不会跟人打交道这点来说,这是某一类学霸的通病。她自己就不会跟同龄人交流,因为“上高中时目标很单纯,我顾不上别人喜不喜欢我,就是求一个高分。只需要花全部精力做题,只有这一件事情需要摸清规则。但大学需要你跟周围人不断互动,你需要知道这个老师认为的重点和可能的考点,你需要找前排的人要笔记。你需要跟你们寝室的其他人相处,这在我前面十几年接受的教育里,是缺失的。大学里需要面对的各种情况,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之前没有人告诉我这些”。
任雯不像吴谢宇这样,对妈妈的世界很执着。她知道自己必须改变,但是不知道如何开始与他人建立关联,于是花了很多时间看书甚至是看综艺,学习人和人之间是怎么相处的。“我是后来才开始看综艺的,我之前从来不看。特别是恋爱以后,你会发现,两个人一天下来哪有那么多事?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一起看综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看综艺就是看人,对不对?”
任雯还按照理论,把人与人的关系分为弱连接和强连接。如果她觉得是强连接的朋友,她会非常花心思认真维系感情,每天都会和这样的朋友聊聊天。“我觉得我应该能从他们身上看到我为什么失败了,所以从来没有放弃跟他们交朋友。”任雯非常羡慕有些人只说两三句话,就能拉近人与人之间心灵的能力。她觉得这个能力是可以学来的。而她与厉害的人交朋友,会使她感觉自己没有那么差。“我觉得说到底大家都渴望被关注,也希望自己能够被需要,都是人。”
这些听起来有些刻意的为人处世方法,是任雯在大学里受挫之后,痛定思痛悟出来的。上大学之前,她唯一的使命就是埋头做题。待到快20岁时,要学着建立人际关系了,她的方法听起来比较学究化,“网络经济学里面还说,强连接对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很重要,对他的自我认知也很重要,因为它基本上反映了你对你自己的态度。但是从求职的角度来讲,弱连接是最有效的。所以我觉得走入社会这个阶段,人需要不断强化自己周围的强连接,你需要一个守望相助的感觉,那是对你最关键的几个人给你的一个支持网。”
吴谢宇在成长过程中错过了同龄人之间真实的碰撞,他没有体会过交往中的期望、失望、冲突、和解。只有与他人产生碰撞,通过反弹回来的力,一个人进而理解“我何以为我”。如果没有真实的生活体验,一个人就像被抽干了情感的机器。所以有同学偶尔窥见吴谢宇内心的孤独感,他与所有男生拍肩膀进行寒暄,反而是他不会与人亲近才有的举动,“其他人都不会这么做,我心里觉得他挺奇怪的”。
在我们记者跨越几年联系吴谢宇同学、师兄师姐的过程中,也始终感觉到他们互相之间以及对记者采访的明确界限感。尤其是2016年吴谢宇作为弑母嫌疑人被通缉时,他北大的同学们正在读大四。一方面学校不让他们接受采访,而他们也正处在各自忙碌地奔向前程的时候。吴谢宇的案件让他们震惊,但不少同学也本能地回避,大家似乎都表现得对他不太熟悉、对这件事情显得冷漠的感觉。大学同学之间的关系,与一般人想象中的亲密感觉不一样。
安宏林是吴谢宇同级的同学,说到在大学里有没有好朋友时,他反问记者,“我想问一下,你最好的朋友是你的同事吗?”
安宏林说,同学之间有竞争关系,比如评奖评优。“我们以院级为单位,或者以系、以班为单位,肯定有竞争。跟谁一个专业,跟谁一个学院不是你可以选择的。但是你的朋友是你可以选择的。我们的情感可能是自己跟学院的情感,自己跟学校情感,但可能不是人之间的。”哀伤中的妈妈
吴谢宇没怎么提到他在大学里与人交往的受挫,他的认知里,还只能以分数衡量一切。本来年轻人到了大学,应该像放飞的鸟儿,但他天天在心里牵挂着不开心的妈妈。妈妈的意义太过重大,“我从小那么拼命读书就是为了拿第一名让妈妈开心让妈妈骄傲啊,我活着就是为了妈妈而活啊”。
2010年初吴志坚去世后,吴谢宇感觉妈妈进一步封闭了自己。本来马老师和其他几位老师,既是邻居、同事,也是谢天琴的老朋友。谢天琴当面跟她们一起聊天散步,可是在儿子面前却埋怨她们,“她经常给我抱怨,说那几个人好烦,整天敲门打电话来打扰我们。还会说她与她们以前发生的一些不愉快的往事。这一切,让我觉得,她似乎没把她们这些十几二十年的老相识当朋友”。邻居来敲门,谢天琴调小电视机的声音,手放在嘴唇上做出“嘘”的样子,不让儿子出声,不愿意与人接触。
马老师一直认为谢天琴把她当很好的朋友,因为遇到各种事情,谢天琴还是找马老师商量。比如吴志坚过世后不久,大姐的儿子阿勤找谢天琴借车开,谢天琴问马老师该怎么办。马老师建议她把车卖了。本来谢天琴留着车,是方便周末去福州一中接送小宇,可是吴志坚的侄子惦记着,她就下决心卖车。2022年夏天我们去找马老师采访时,另一位老师说起谢天琴当年卖车的事,她曾经想买,但是她老公说了句“不吉利”,所以没买。谢天琴担心的“孤儿寡母”被人看不起,也不完全是她自己的心理在作怪。但是谢天琴会把这种感觉扩大,包括窗户下停了几辆车,她都认为,“看来这个日子是没法过了。我恨所有的人,大家都要来欺负我们孤儿寡母的”。
她也在日记里哀叹,“我四十多岁了,出身于那样的家庭,又遭遇太多的苦难,从小到大,就遇不到一个好人,小时候被邻居欺负,现在失去丈夫后被邻居、同事欺负,而且,你走后,你所有的同学、朋友、同事没有一个人照顾过我们。我真的不知道人世间还有温情在,在哪儿?”
她一方面不喜欢外人联系她,但另一方面又感慨大家都忘记吴志坚了,“世态炎凉,人们的记忆止于权贵,罢了”。本来是谢天琴自己跟马老师表示,她不愿意申请高级职称。可是在日记里,她对于自己只是中级职称非常在意,说没脸见人。谢天琴浓重的负面情绪,使她看什么都不顺眼。她写到过了一个“阴暗、可怖的春节”;她买鸡给儿子熬汤,“买了一只不中意的鸡”;买了一套衣服,也是“一套不可心的衣服”。
吴志坚留下的车卖了5万多元,很快大姐阿花以她要翻盖房子的名义,找谢天琴借了7万元。就如阿花所说,在钱方面,谢天琴从不小气。但是谢天琴的手头并不宽裕。吴志坚去世后,他的朋友们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再加上吴志坚的抚恤金,加在一起也就大概7万元。
本来谢天琴不愿意过手这些钱,想让婆婆直接拿着。但是有生活智慧的婆婆,非要把钱放在谢天琴那里,让她每个月当作生活费给自己。谢天琴不解,马老师看出了她婆婆的用意,说,吴志坚的姐姐妹妹哪个不缺钱?放在婆婆手里,这钱很快留不住,在谢天琴手里,老人家每个月的生活费还能有保障。但是没多久,大姐因为修房子,这7万元也没留住。谢天琴应该是接着在用自己的工资负担婆婆的生活,因为她日记里对死去的丈夫提到“我的工资足以应付日常所需以及给你妈的费用”。
所以谢天琴在写给吴志坚的信里,提到他希望儿子小宇不要像他那样,有这么重的家庭负担。她和吴志坚的几次争吵,发生在他生命后期。谢天琴认为吴家的贫穷对老公的拖累太深,使得他的病总也治不好。她希望儿子做一个无情无义的人,不要被拖累。
谢天琴的要强也体现在评职称上,她由于是本科学历,中级职称很顺利得到了。待到评高级职称这事上,她不愿意申报。谢天琴在学院发论文就能评高级职称,这事一点也不难,但她就是不做。马老师说她理解谢天琴,一个家里男人没了,她本来出身贫寒,又无权无势,“她要跟你诉说,就好像要博得你的同情,她不需要别人同情,她是这种心理,我能理解”。
谢天琴的悲观在丈夫去世后达到极致,她写道:“像我这样的女人能否继续存活?我在心里问了自己好多次,始终无答案。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我是个彻底的失败者,一无所有,一辈子什么也没有,没有了丈夫,没有朋友,没有亲情,没有事业。”
2012年2月的日记,谢天琴提到觉得自己的心理状态不正常,“对于生活,对于生命,我已经完全失去热情与自信……打扫房间,永远无法干净;洗衣服,永远无法干净……每一件事做之前要犹豫很久,做之后要后悔很久。我也知道我心理不太正常,需要看心理医生,但我知道这些病症的成因在于你的离去……现在的我无法正常了,除非跟随你而去。我困惑,我该不该去找你,你会等我吗?”考第一的执念
吴谢宇特别在意妈妈的情绪,他说父亲去世后,他更是放大妈妈的每一丝情绪。高一丧父,整个高中阶段本应该是吴谢宇失去父亲最痛苦的时期,但是在福州一中因为成绩第一带来的光环,吴谢宇认为那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时段。在北大的日子,他期盼的光环一直没有来到,妈妈不快乐,他仍然想着用“第一名”,换来妈妈的笑脸。
但是到了大学阶段,同学之间的背景差距,关乎地域之间、家境之间、认知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年轻人来说,很难面对。吴谢宇在高中以分数来获取绝对优势的体验,在这里完全不存在了。
吴谢宇的师姐萧丽丽说,成为北大学生之后,她才发现,真正通过高考这个途径进入北大的,仅仅是一部分同学。还有不少同学,通过参加竞赛进来,或是通过特长生渠道进来的。这么多的渠道背后,是不同的资源,它意味着:进了北大之后,大家的未来更不是只由学习成绩决定的。
萧丽丽说:“我们班有各种行长的儿子,大律师的闺女,还有父母都是企业家的,你会发现,你看到的,都是自己以往通过学习不可企及的资源。真的内心落差很大。你会发现,好像自己能做的就只有这么一条路,那就是继续学习,这是好学生擅长的。但是社会上‘寒门难出贵子’的言论,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而吴谢宇的认知里边,依然只有学习这一条路。越是觉得比不过别人,他越是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学习上,更加关注分数。可是北大学生的评价体系非常多元化,萧丽丽说她很快意识到,“成绩好的学生,我们会称为‘大神’‘大牛’,但他们的人生并不一定会走得很远”。而吴谢宇即使在北大专攻学习,也到不了被同学称为“大神”“大牛”的程度。
在李又廷看来,“在北大如果只是学习好,北大学生其实心里会给你加一个标签——小镇做题家。不会认可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或者说不认为你能作为北大学生代表,打心眼里不认的”。
李又廷分析到,他们班四十多人,符合“小镇做题家”标签的有三四个。“我没有贬低他们的意思,但是通常他们的画像是这样的:首先不是来自经济特别发达的地区;第二,他高中也确实尝到了刷题模式的甜头,在大学的话他重复这套也有一定效果;第三,他们至少把70%的时间都花在学习上,20%用来参与少得可怜的社团活动,还有10%谈谈恋爱什么的。”
为什么这样的同学不会被新群体推崇呢?李又廷说:“我们会认为这样的人没有太多的创新意识。学习好,就是高中你能获得成功,或者说你能被北大录取的原因,对吧?拼命刷题进了北大清华,可是真的到了北大,它其实跟社会更近了一层。如果你只是会做题的话,你这个人还在用老套路去寻求成功。可是社会没有题给你做,你终将没办法很好地适应这个社会,所以大家有时不太愿意跟这样的人一起玩。” 大学吴谢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