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永恒困境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布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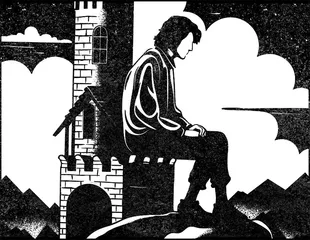 在文化人的表达里,“困境”是个非常受欢迎的高频词。无论话题关于政治还是社会,生活还是情感,科学还是艺术,最后十有八九会出现这句:“它表达了某种困境。”而且,困境都是“当下”的,没有人讨论“曾经的某种困境”。神奇的是,那些困境不管是多少年前被提出来的,却始终适用于今天。也就是对困境来说,“当下”两个字永远有效。还有,困境都是“普遍”的,没有人讨论个别人的某种特殊的困境。它一定是人类共有的、互通的、普遍存在的。你可以凡尔赛假装自己没有,但其实谁都有。困境面前,人人平等。
在文化人的表达里,“困境”是个非常受欢迎的高频词。无论话题关于政治还是社会,生活还是情感,科学还是艺术,最后十有八九会出现这句:“它表达了某种困境。”而且,困境都是“当下”的,没有人讨论“曾经的某种困境”。神奇的是,那些困境不管是多少年前被提出来的,却始终适用于今天。也就是对困境来说,“当下”两个字永远有效。还有,困境都是“普遍”的,没有人讨论个别人的某种特殊的困境。它一定是人类共有的、互通的、普遍存在的。你可以凡尔赛假装自己没有,但其实谁都有。困境面前,人人平等。
这样一来,有关困境那句高频表述的完整版应该是“它表达了当下某种普遍存在的人类困境”。在任何一场讨论里,只要此话一出,一切都拔高了,时髦说法是被赋能了。哪怕是一场酒桌争论或者路边闲聊,也顿时会有策展的感觉。但它只能被一个人说一次,晚了就没机会了。更不能一上来就说,那会搅了一群人的智识盛宴,属于演技太嫩。必须时刻动态关注,根据对话走势拿捏到最恰当的一刻,抛出“困境说”,占领巅峰,把剩余对话扫入收尾的垃圾时间。
这事儿不容易。但既然事关“困境”,怎么可能容易呢?否则就不会普遍存在并永远有效了。不信咱们看看那些著名的、经典的困境。比如钱锺书的“围城困境”,里边的想出去,外边的想进来,反正总是那边的好。卡夫卡的“城堡困境”,城堡就在那儿,K为了进去而尝试各种折腾,可就是进不去。加缪的“局外人困境”,默尔索越是对一切漠不关心,就越招致所有人对他的关心。昆德拉的“轻重困境”,萨宾娜追求轻盈不停地离开,到最后无处可去,回忆成了她挥之不去的重压;托马斯无惧沉重,宁可放弃自由也要回来,最后却在田园牧歌里落得一身轻松。你看,这些困境今天都有。所谓别人家的孩子,这是围城困境。一办事就四处碰壁,一看病就疑难杂症,这是城堡困境。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这是轻重困境。
当然,还有当下最被热议的一类困境。只要一看到“那些裸辞去环游世界的年轻人,现在咋样了”,或者“逃离北上广,你后悔了吗”这种标题,就知道这是讨论理想和现实的困境,也就是“娜拉困境”。娜拉觉醒了,于是出走了。随之引出了大量追问,比如鲁迅那篇著名演讲的题目《娜拉走后怎样》。
“困境说”虽然上档次,但也着实让人恼火,因为大家只忙着提出困境,而不给出方案。好像除非一死,否则困境是无解的。《局外人》的最后,默尔索在异口同声中被处死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最后,托马斯开车掉山下摔死了。《城堡》里K到死也没进入城堡,甚至没等这本书写完卡夫卡自己也死了。《玩偶之家》倒是没把娜拉写死,但同样无解。全剧在决绝的关门声中落幕了,所以才引出大家纷纷“求解”,追问她之后咋样了。这么一看还是鲁迅清醒并且敢说——“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