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纂修(下)
作者:卜键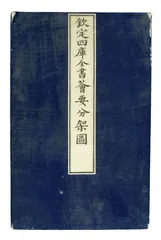 四库馆的纂修官和分校官,职责有区别也有重合。通过王际华的奏折,可知武英殿修书处十二纂修也是《四库荟要》的分校,管理200名誊录,每个纂修负责一股,对他们所录文稿统计字数,核校后上缴提调,并做记录。姚岐谟旷课数月、无人报告一事发生后,王际华随即提出整改措施:
四库馆的纂修官和分校官,职责有区别也有重合。通过王际华的奏折,可知武英殿修书处十二纂修也是《四库荟要》的分校,管理200名誊录,每个纂修负责一股,对他们所录文稿统计字数,核校后上缴提调,并做记录。姚岐谟旷课数月、无人报告一事发生后,王际华随即提出整改措施:嗣后各分校所收誊录课程,按期校毕,应令即送提调,核明并无短缺,再发复校官复阅,俾提调得以按月查核,倘有亏短不清,仍即时揭报,以凭参处。
此一段文字应予重视,涉及修书处的工作程序:提调将课程(应誊抄的稿件)下发各分校——分校再分给本股誊录——誊录完成后缴回——分校审核文字后上缴提调——提调勘验后交复校官复核——返回提调处验明——装订成书并留档——上缴分管的总裁官,稽核后进呈皇上。
武英殿的所有纂修,开始时应全力办理《四库荟要》,而分校之外又有复校,复校之后还有总校,叠床架屋,看似多了把关的层级,实则往往造成互相依赖,谁都不尽责。过了一年多,于敏中、王际华又请求删去复校的环节,奏称:“查本处额设分校官二十二员,复校官十二员。向以分校收校誊录之书,以复校稽核分校之书,层层相临,原期毫无舛误。但行之既久,觉多一层转折,即多数日稽迟,且或分校、复校彼此互相倚恃,反致多有挂漏。应请将《荟要》复校通改为分校,所有誊录二百人,均匀分派,每员约管六人,则每日仅各收缮书六千字,尽可从容详校。其中缮写平常者,亦责令即行驳换,以便及时赔写。”二人还表示,倘若还有纂修像以前那样草率,或迟迟不能完成工作定额,以及缮录不合规矩等,查出后即加处分,轻则记过退缺,重则据实参奏,以期人人谨凛,不敢苟且塞责。
十二纂修中的其他六位翰林,以三十六年、三十七年两科进士为主,在仕途的发展略好一些,故事也较多——
李光云,福建闽县人,三十六年二甲三十七名进士,散馆授编修。有关他的记载很少,似乎没啥成就,两次翰詹大考皆列在三等,几乎被逐出翰林。而后来不知为何被和珅看重,受邀在和府兼职家教,算是上了和珅的贼船。乾隆晚期和大人权势日涨,而卖身投靠者并不算多,李光云担任通政司副使、太仆寺卿,背后都有和珅的推助。太上皇帝崩逝后,嘉庆帝宣布和珅二十大罪,其中就有“侍郎吴省兰、李潢、太仆寺卿李光云、皆曾在伊家教读,并保列卿贰,兼任学政”。那时李光云正在广东学政任上,命以原品致仕。
龚大万,湖南武陵人,三十六年三甲进士,庶常散馆后授检讨。有评介称其“沉浮馆阁几二十年,未展所学”,实则大万在四十二年五月即为广西正考官。以检讨主持乡试者甚少,体现了乾隆帝也包括阁部大员的看重。龚大万性格豪爽,意气风发,也喜欢臧否人物,本可有一番作为,却在五十年二月举行的翰詹大考中栽了跟头,直接被免职回家。
郭寅,山东历城人,三十四年三甲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时授检讨。进入四库馆约两年,已升编修的他因丁忧返乡,很可能没有再回任。官场历来将丁忧视为一个大坎,上升的势头突然中断,待三年(实际为二十七个月)服丧期满回京,还要等候出缺,有时要等很久。郭寅应是想明白了,不再出山,而四库馆臣表上有他的名字,称为“原任翰林院检讨”,应是其入馆时的职务。
许兆椿,湖北云梦人,三十七年二甲第九名进士,26岁,散馆授编修。兆椿仪表堂堂,精明强干,担任武英殿纂修后勤奋尽心,孰料与郭寅几乎同时遇到亲丧,只能回乡丁忧。等他服满回京,已是乾隆四十三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而在四十七年正月文渊阁本告成引见时,许兆椿列在一等。必须说明的是,在四库馆数百名纂校人员中,列在一等者仅仅22人,武英殿的十二纂修,只有他一人享此殊荣。
这样的荣誉对未来前程自会产生积极影响,许兆椿不免兴奋,却很快陷入一个大麻烦。那是当年四月的一次常朝(例行朝见),接受召见的官员在太和殿丹墀两旁候驾,分文武班次站好,不得站错,不得逾越,不许交谈,一个个肃穆而立。许兆椿在散朝后对人说,行谢恩礼时,见一穿二品武职补服者竟然越班走过甬道,实乃大不敬。皇上接奏报后大为光火,即令军机大臣传询许兆椿,复将当日参加谢恩礼的六名二品武官叫来,如内阁学士兼副都统成策、镶黄旗汉军二等男宝柱、镶黄旗副都统恒瑞等,站成一排,命他上前指认。事情闹到这样一步,许兆椿始料不及,面对一排怒目而视的满大人,也不敢盯着细看,只得说自己离得较远,又是在背后,实在无法确认。皇上并未怪罪兆椿,却认为一定有此事,责令六武臣老实交代,又要周围的人揭发检举,最终还是不了了之。这次事件后不久,许兆椿就改为福建道掌印监察御史,历任松江府知府、江宁府知府、漕运总督、刑部侍郎、浙江巡抚等职,所至官声皆好,为嘉庆间名臣。
朱依鲁,与李光云同年,同入庶常馆,散馆后同为翰林院编修。不同的是,此人乃明朝靖江王后裔,易代之际,本支先祖历尽艰险,从桂林朱紫巷逃出,于水田中筑屋居住,故名田心村。至乾隆十年,依鲁之父朱若东考取乙丑科二甲进士,王际华为该科探花,散馆后同留翰林院。而不久遇上翰詹大考,王际华考列一等,升授侍读学士;若东考在第四等,被罚俸一年。后朱若东选任御史,历工科掌印给事中,山东、河南、江苏等地道员,两个儿子依鲁、依炅也先后得中进士,授翰林,人称“父子三翰林”。朱依鲁在四库馆待了多久、具体的表现皆不得而知,馆臣表上未见列名,完成文渊阁本后的论功行赏时,一等、二等也没有他的名字。
就在乾隆四十七年,在许兆椿那次惹事议论之次月,已任云南道监察御史的朱依鲁上奏,参劾修书处督催供事乖谬刁玩:
武英殿办理四库全书提调、督催二处,各派供事承值,而督催处稽查功课,按季奏报,向由提调处供事开送。兹有承办督催事务编修祥庆,于前月抄查出月报字数册内有私自改增之处,询知月报清单系提调处供事杨承业开写遗漏,因自知错误,不敢回明本官,私向督催处之供事庄宝符、陈三聘二人商同更正,亦未回明祥庆。祥庆当将庄宝符、陈三聘并杨承业一并责打,讵杨承业自恃非祥庆所管,语言顶触。维时提调处之供事多人,朋争不服,声言集聚于西华门外等候祥庆,欲加凌辱。祥庆闻风畏惧,潜散回家。是日,杨承业即赴提调处告退,未经该提调究办。次日,祥庆忽又向提调代求免革,似此情节,种种乖谬,殊骇听闻。查祥庆身任督催,于所管供事私改档册,自当按法责处,杨承业系提调处供事,亦当移付讯究,乃胡涂任性,既经责处,又复畏惧求情,有玷官箴,相应请旨交部察议。至供事杨承业等虽非本管之官,因查出隐误被责,輙敢于殿廷禁地聚众喧争,更属目无法纪。但恐其中或有别情,非审讯不足以示惩警。
据此可知在兴修四库期间,武英殿还下设提调处和督催处,互相制衡,结果两部分打起来了。朱依鲁虽不在现场,但显然对此一事件听闻甚详,指名道姓,应是很难编造出来的。可到了调查阶段,“经王大臣等提集人证质讯,并无确据”,念在“朱依鲁所奏尚无挟私情弊,着从宽免其深究”。那时的很多举报都是这样难以落实,想起乾隆常责斥科道官不敢说真话、硬碰硬,只能是呵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