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伤医案调查
作者:魏倩 在北陵大街上,你不能随便停车。这儿是沈阳南北中轴线“金廊”的起始路段,也是城市金融区(CBD)与省级政务区的交汇处。从省公安厅一路往北,经过气派的大商场“沈阳天地”、包红色LED屏广告的写字楼,不到半小时,就能走到辽宁省人民政府大楼,然后是始建于300多年前的清昭陵。
在北陵大街上,你不能随便停车。这儿是沈阳南北中轴线“金廊”的起始路段,也是城市金融区(CBD)与省级政务区的交汇处。从省公安厅一路往北,经过气派的大商场“沈阳天地”、包红色LED屏广告的写字楼,不到半小时,就能走到辽宁省人民政府大楼,然后是始建于300多年前的清昭陵。
当然,在这条路上,任何人都不会错过辽宁省中医院(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那幢有着白色外墙的15层住院部大楼,上面竖有2米多高的楼宇立牌,小心绕过翻修建筑围挡,旁边是只比它稍矮一点的医院门诊部。每天清晨不到8点,大厅已是人挤人。
在飘满艾灸味道的大楼里,和人群一起绕着蛇形围栏排队,坐电梯一路上行到9层,右转是医院脾胃科——这家医院的重点科室之一,2月中旬刚刚获得2022年度全国中医医院学科学术影响力第8名。工作日上午,走廊里的候诊椅坐得很满,诊室门前的电子屏显示坐诊医生的正装照片,下方滚动着患者排号。每天早8点到晚5点,它们会一直亮着。
9号诊室除外。2023年2月2日之后,这里的电子屏就一直没再亮。这间诊室属于科主任白光。
事发突然。2月2日——春节假期后上班的第6天——上午9点53分,诊室门开着,白光和往常一样面向门口等待患者,一名没有挂号的男子猛地冲进诊室,用一把手持射钉枪迎面击中了他。“枪钉直接打进医生的眼睛里,血崩了我一身。”一位目击者正好从走廊里经过,震惊之下,她本能地逃开,后来发生的事情回忆起来都是断断续续的:科室乱作一团,有护士躲进楼体另一侧的卫生间,也有人立刻报警。听到尖叫,医生们从各自诊室里跑出来,赶紧把患者疏散到电梯口。
袭击者没有逃窜,随后赶来的警察控制住了他。白光则被立刻推进急救室,到当晚8点仍在抢救。该院一名医生翻拍了他的头颅核磁平片,右眼位置的颅骨已完全缺损,额枕贯通伤,蛛网膜下腔广泛出血,抢救难度很大。当晚院里就有传言他“不幸去世”,但又很快被辟谣,“命保住了,但生命体征靠机器维持”,“情况不乐观”。医生
受伤前,白光是个挺“利整”的人。在沈阳人口中,那是干净、讲规矩的意思。直到今天,他的照片还挂在医院大厅扶梯旁“科室专家简介”的棕色展板上。他方圆脸,短发,戴眼镜,抿嘴,睁大眼睛,穿一件长袖白大褂,显得权威而精神。照片下面是他的姓名、职位,还有他最擅长治疗的病种:消化系统常见病和疑难病,慢性胃炎,慢性萎缩性胃炎,胃食管返流病,溃疡性结肠炎,胃肠道肿瘤术后调理……那是他迄今54年人生的奋斗成果。
除了外表,勤奋是白光给很多人留下的第一印象。他每周二、四出门诊,总是第一个开诊室的门,有时候上午患者太多,全部看完得到下午两三点钟,午饭就在科里随便对付一顿。科里下班晚的同事也总能看见他诊室的灯到晚上6点还亮着。门诊结束后,他还要去住院楼的病房再转一圈才回家。一位在科里住院的老患者是这样发现他“出事”的:“我就问护士,怎么这段日子都看不见你们主任来病房了?”
在伤医事件发生前,勤奋给他的人生带来的是完全正向的影响。他1992年考入辽宁中医学院(现在的“辽宁中医药大学”),1996年读研究生,毕业后就在其附属医院工作,算起来已经在科里待了24年。这期间,他拜中医药管理局评出的“第三届国医大师”周学文为师,后来又考了本院的博士,开始自己带硕士生。
白光尤其擅长治疗溃疡性结肠炎,被不少患者认为是“省内顶级专家”。一位查出这种病的沈阳本地患者在腹泻近20天后向他求治,虽然病区没有床位,但还是很快被加床收治——患者特别向我们强调,“是在没有托人也没送钱”的情况下。她听白光私下对学生说:“我们就是研究‘溃结’的,遇到这样的病人一定要收。没有床位也要想办法,哪怕把休息室腾出来给病人住。”
他在这方面确实有办法。患者住院20天,又连续吃了4个月的中药,之后连续三年都没再复发。她在网上和其他地区的患者聊天,发现白光用的治疗手段挺特别,除了传统的“喝汤药”外,还给她开了特制的中药药液灌肠,以期药物直达溃疡患处。这些药剂,据说也是科里自己研制的。
白光和他的同事们还研究了别的中药方剂。2020年,专门用来平湿气的“运脾和胃贴”拿到了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他带的硕士生花10个月的时间总结他治疗慢性便秘的用药特点,研究出“肺脾同治”的治疗理论,觉得他比其他老师更“敢创新”。
白光信任自己一点一点挣得的东西:学生、论文、专利。他给自己的微信取名“我行我术”。科里有医生走传统路线,平时也穿带盘扣的绸质上衣在院外开诊,但白光的注意力不在这儿,他忙着发文章,近几年尤其喜欢用数据分析用药规律。他的另外一项技能是“懂开刀”。在这家靠中西医结合疗法吸引患者的医院里,像他这样热衷手术的中医是榜样性的。2017年,他参加了医院的首例经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2021年又开始尝试黏膜内镜下剥离术,外出讲课时,他对循证医学和生物制剂也表现出不同于其他中医的兴趣。一位曾和他同在周学文门下求教的医生认为,正是凭借这一点,他才越过科里其他年资更高的医生当上了主任——只靠号脉开方撑不起一间科室。直到今天,内镜中心依然是脾胃科待诊患者最多的地方。
慕名而来的患者不少,有时候“脾胃科半个走廊都是挂他号的人”。有些患者从市里最好的“医大一”(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盛京医院被推荐过来,还有人从临近的本溪市、抚顺市过来求诊。在愿意接受采访的患者口中,白光大部分时候是和善的、关心人的,甚至是幽默的。有一次,一位患有萎缩性胃炎的老年患者在诊室里放松不下来,随口说自己平时不吃肉,白光问:“那阿姨你是得信点儿啥不?”那天听说白光遇袭后,这位患者到凌晨3点都没睡着觉。
当然,诊室外的喧嚷中,也有些关于他的批评,其中最主要的是挂号费。脾胃科12位开诊医生,挂号费从14.4元到96元不等,最高的那位是国家脾胃病重点专科学术带头人,其余大多数为19.9元,而白光的诊费是60元。一位曾在他处“调理肠胃”的患者向我抱怨,每见他一次就得花60元——她和病友甚至因此戏称白光为“六十的”——再加上诊断、抓药,每月至少要花2000元,因为经济上吃不消,她如今已换了另一位医生看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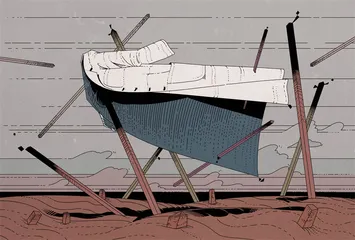 离开辽宁省中医院拥挤的住院部,以及寸土寸金的北陵大街,“富商巨贾大展宏图的黄金宝地”,稍微往城市东北角行进一程,如果恰好在夜间行车,你会发现眼前的一切在慢慢变暗,直到路灯的亮光几乎消失的时候,也就抵达了位于沈阳市大东区的上园小区。
离开辽宁省中医院拥挤的住院部,以及寸土寸金的北陵大街,“富商巨贾大展宏图的黄金宝地”,稍微往城市东北角行进一程,如果恰好在夜间行车,你会发现眼前的一切在慢慢变暗,直到路灯的亮光几乎消失的时候,也就抵达了位于沈阳市大东区的上园小区。
经过放学后空无一人的沈阳市第一一一中学,再绕过那家正在招租的超市、玻璃门脏得看不清人影的打印店,小心招牌边的水管,在台阶油污发黏的麻辣烫店门口右转,就能看见三栋东西向的楼房,最中间的那一栋,往上数7层,肉色窗帘半掩着的那间,就是犯罪嫌疑人“马某某”的家。据沈阳市公安局2月2日当天发布的警情通报,他是一名男性,今年66岁。这是目前我们得知的关于他的全部信息。
2月中旬,春天还没抵达沈阳。天气又冷又阴,到处灰蒙蒙。主城区最东北角的上园,几乎没有人在室外活动,只有收劳工手套和旧衣服的小三轮车一圈一圈地绕,一家搬家公司忙着干活。这儿已经被列入大东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住着3000余户人家,而“马某某”的家所在的那三栋是全小区唯一“全是单间”的楼房。顺着层距过高的楼梯往上走,每一户人家的门上都糊满小广告,门锁锈蚀。层高比一般楼房高出一些,楼道空荡荡的,静得只有回声,即使是有阳光的下午也显得不洁、阴森。
比起发生在中医院的伤医事件,附近的居民们更熟悉马某某的另一桩行动:袭击白光被抓获后,他主动向警方交代,自己在家里用同一把射钉枪杀害了一位“酒友”。两周前特警带着他来指认现场,那天街边所有店铺的店主都出去张望了几分钟。
但人们对这宗命案的兴趣也就到此为止了。用一位在楼下健身器材处晒太阳的妇人的话说就是:“这年头,死个人算什么事儿呢?”那神情不是因困窘而不愿谈及,而是纯粹的不感兴趣。
一位中介则是这儿唯一一个提到辽宁省中医院伤医案的人。在他口中,马某某是一个蓄意行凶的“小老头”,“也可能是喝多了,但肯定不是神经病”。因为他的攻击有指向,“社会危害性不大”。因此他并不担心发生在楼里的凶杀案会影响自己的生意,尽管那些房间每一个都充满灰尘、油烟、84消毒液和霉味,灯管几乎亮不起来,蹲厕高高地架在房间一角,但“附近到哪儿都找不到比这更便宜的房子”。他说,要是附近的一家大汽车贸易公司没倒闭,这里的租金还会更贵些,可以到650元一个月。但如果愿意把暖气停掉,房东还可以把取暖费折进租金里。在东北的数九寒天里,楼里很多租户都是这么做的。
事件发生后,围绕“马某某为何行凶”,警方尚未给出确切的调查结果,但本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两种说法。第一种是,马某某的儿子曾经是白光的患者,他在中医院脾胃科做过胃镜,多年后查出癌症,怀疑是当时的治疗导致的结果,存心报复;第二种是,马某某的儿子被推荐到白光处治疗消化道癌症,后者服药后未按标准流程定期复查,最终病情恶化死亡。那位科室的知情者给出的则是一个模棱两可的解释:“白医生耽误了这个嫌疑人一名直系亲属的最佳抢救时机导致死亡(具体原因不好细说,但实际上医生本人没有过错)。”
但邻居们谁都不记得马某某还有个儿子,他们甚至没法确切描述他本人的长相。楼下的超市招牌掉了就再也没挂起来,窗户栏杆铁锈的颜色盖过油漆,老住户早就都逃离了这里。新冠疫情期间,社区给楼里拉过一个群,但楼里空房子多,外地的汽修小伙子来了又走,那个群没什么人说话。楼下邻居们打开手机找,并不知道哪个头像属于马某某,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在群里。没人知道他的真名,中介说,7楼的房间永远空着。医院
晚9点,辽宁省中医院住院大楼,两名保安从屋里搬了把椅子放在刷卡机旁,挥动黑色金属探测仪,指示来人绕一旁的“安检门”。上一休二,值班的日子是24小时岗,晚上两人轮值。白天,门诊大楼前的安检机器要更新一些,安检通道上方“测试”的字样都还没摘。知情人说,以前院里也有安检,“但不经常开”,如今每通过一个人,保安都会要求“大小包要过安检”,他们对每个包里的东西都看得很仔细,偶尔见到屏幕上有不认识的东西,还会大声讨论。
除此之外,医院里一切都如往昔。大厅里熏艾的味道经久不散,二楼取药处的长椅上挤满了等待“智能颗粒药房”窗口喊自己名字的患者。这是近几年中医院的时髦产物,不用抓药代煎,医生开方后半小时,患者就能取到分格包装好的配方颗粒,回家直接开水冲服即可。2021年,药监局发布《关于结束中药配方颗粒试点工作的公告》,辽宁省中医院走在了前面。比起院外取代煎药的拥挤队伍,人们更欢迎这类颗粒剂,尽管它并不便宜——7天药量要花费近200元。2020年辽宁省中医院总收入15亿元,在全省专科医院里处于拔尖位置。
主任不在了,9楼的脾胃科依然照常运转。内镜中心一周内预约人数就超过了三位数,科里尽全力发展的“脾胃病外治中心”直到下午6点还有患者就诊,他们用针灸、艾灸、穴位贴敷的方式帮助患者“调理肠胃”。仅隔着一道走廊,白光的同事们依然按时上班、看诊,穿着皱巴巴汗湿后背的白大褂去卫生间,加班,写病历,在走廊里吃盒饭。
但有的患者感受到了变化。2月21日晚,一位在住院区大厅里偷偷抽烟的患者告诉我,他和病友们最近都发现,医生和护士的态度变得比以前客气了许多,“就像是怕得罪谁似的”。
变暗的不仅是白光诊室门口的那块电子屏,他的同事,包括和他一起在论文上署名、一起在手术台上工作的人们也坚决不对这件事发表任何意见。其他行政部门的态度与之类似。整整五天工作日,位于住院部一楼的医患关系办公室始终大门紧闭,电话无人接听。
在被连续拒绝了三天后,我终于拨通了科室里一位医生的电话,他没像其他人一样立刻挂断,或是对着电话破口大骂,晚7点刚刚下班离开医院的他说:“我不是在乎医院发现我是谁,我只是还没有做好准备,应该用什么样的状态去面对和安放这件事。”他在当晚通过了我的微信好友请求,又在第二天中午拉黑了我。
来自厦门大学附属医院急诊ICU的一份研究显示,医院从业人员目睹暴力伤医事件后,超过三分之一的人会产生情绪衰竭、情感疏远,大部分人都会出现回避/麻木、警觉性提高等反应,如果不加干预,长此以往会产生职业厌倦感,对医疗系统缺乏信心,有强烈的离职意愿,即使进行心理干预,这种状态也至少需要数月才能恢复。而据一位白光科室同事对我们的说法,直到案发20天后,除了“严禁接受采访”的指令外,医院没有给科室里的员工提供任何心理支援,他们甚至没有得到一个关于事件的完整解释。
但如今的白光已经顾不上这些。他留在学术期刊上的电话号码再没人接听,微信也沉寂下来,他仍躺在ICU病房里,接受一天半小时不到的探视。科里那位直到最后都不愿意透露自己性别和身份的知情者说,他现在情况还算稳定,是“半植物人状态”。
(感谢印柏同、罗方丹对采访的帮助) 医院伤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