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日常里,公共性何处觅?
作者:蒲实摄影·白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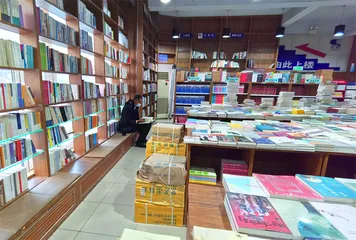 现代城市中孤独个体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是陌生的,这种陌生感使得个体心理安全感极大地寄托于家庭,对于人的公共性却缺乏认识。徐前进在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任教。在给大学生上课的时候,他举了两个例子来从社区层面构建历史场景。一个例子是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写的奥斯维辛,犹太人在集中营中集体保持了沉默,何以如此?另一个例子是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旅顺口大屠杀时受害者束手被害的状况,在那种场景下,你会如何做?是接受死亡,还是起而反抗?
现代城市中孤独个体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是陌生的,这种陌生感使得个体心理安全感极大地寄托于家庭,对于人的公共性却缺乏认识。徐前进在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任教。在给大学生上课的时候,他举了两个例子来从社区层面构建历史场景。一个例子是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写的奥斯维辛,犹太人在集中营中集体保持了沉默,何以如此?另一个例子是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旅顺口大屠杀时受害者束手被害的状况,在那种场景下,你会如何做?是接受死亡,还是起而反抗?
在课堂上,他引用了英国人詹姆士·艾伦在旅顺口的经历,来创造讨论的机会。时下读到这段经历,感触颇深,也在这里将这段经历作为这篇专访的思考线索。艾伦目睹了日本人屠杀毫无抵抗之意的中国平民时,很多人是“预先俯伏在地上,以这种状态被杀的”。而这位美国轮船运输公司的小职员却决定投入战斗,用力将在近处用枪瞄准他的日本兵的枪杆打掉,重击其鼻梁,得以逃脱,其后在一个巷子里杀掉一个狭路相逢的日本兵,换上他的衣服夜行逃走。徐前进问:为什么这个小职员敢于在危险处境中反抗,而在另一些场景下,人们却无法联合起来反抗?两种不同的行为模式的心理和环境因素是什么?没有学生回答他的问题。他认为,独立意识与反抗精神的缺失,与家庭公共性的欠缺有关,而这本该是在社区公共生活中培养的。
这正是《流动的丰盈》这本充斥着对日常生活场景事无巨细记录、初读起来缺乏严谨逻辑和因果关系的书的意义:在那些我们每天都经过、看到与听到的,司空见惯和重复性极高的场景里,蕴含着未来的视野;只有当这些重复性的景观消失后,它们的价值才显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徐前进的这部作品是一本馈赠于未来之人的书,旨在为检索我们这个时代历史档案的后人留下空白之处的一鳞半爪。
 三联生活周刊:你能否举几个具体的例子,讲一讲日常生活的“人物和事件处在一个无法通向文字制度的封闭空间”该如何理解,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往常我们对一个时代日常生活的了解,通常会通过文学、书信、日记等这样的文本来进入,也有一些历史学家会用如县志、日志等来写小人物。这些形式与你所写到的历史写作的“文字制度”有何不同?
三联生活周刊:你能否举几个具体的例子,讲一讲日常生活的“人物和事件处在一个无法通向文字制度的封闭空间”该如何理解,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往常我们对一个时代日常生活的了解,通常会通过文学、书信、日记等这样的文本来进入,也有一些历史学家会用如县志、日志等来写小人物。这些形式与你所写到的历史写作的“文字制度”有何不同?
徐前进:这部作品表面上是对一个小区日常景观的描写,实际上是对文字制度的思考。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是我们十分熟悉的,也就是关于政治或经济的行为规则。文字也有内在的规则,我称之为文字制度,例如良好的修辞、密切的逻辑和因果关系,以及对于惊奇、断裂、伟大的热爱等。如果不符合这些规则,我们写的东西就会被文字制度排斥。在自然科学方面,文字制度的力量十分清晰,在人文科学方面也是如此。诗歌是个例外,但在现代社会已经越来越少。之前,我没有注意这个问题,但觉察到这个问题后,我开始思考文字制度的规则。
目前微观史研究有很大的影响,《王氏之死》《漫长的余生》属于这一类,还有很多其他作品,例如《蒙塔尤》《马丁盖尔归来》等都是出色的作品,扩大了传统研究的范围。而在文字制度的意义上,这些作品并不具有突破的意义,它们似乎是在证明文字制度的有效性,回避文字制度的无效性。也就是说,那些质疑文字制度缺点的人,你们看,文字还是能够记录小人物或小事件的。
所以对于文字制度的反思,就要走到文字制度之外,观察那些被文字制度删除的部分,包括无数的人、无数的事、无数的物质、无数的语言,还有被无限改造的空间。在人类历史上,这些因素不只是在一个时代里被忽视,而是在很多时代都被忽视。我们对于民国时代的美化与文字制度有关。在那个时代,有能力写作、阅读的都是社会上流,多数普通人不识字,他们的生活无法进入文字制度,从此消失不见。现在,我们根据遗留的文字理解民国时代,实际上看到的是上流社会的生活,普通人的劳累与艰辛是不可见的,优雅、高贵、博学的民国时代也就成了一个文字制度制造的幻象,它排斥不识字的人,排斥写作能力不好的人,排斥重复的场景,排斥暂时不清晰的意义,排斥无逻辑和因果关系不明显的状态。
写作这部作品时,我试着描写一些缺乏严谨逻辑和因果关系的日常生活场景,这些场景本来不会进入文字制度,以前它们变成了空白,现在还在变成空白。出版后,一些读者对此不满,例如“散乱”“缺少逻辑”“平淡无奇”等。这些批评合情合理,是在为文字制度辩护。
但为什么我要继续写呢?我想克服文字制度的一个弱点,即无限度的选择与删除。文字制度喜欢惊奇、断裂、伟大,不喜欢平淡、重复、微小,所以战争、革命等事件会进入历史,但这些事件是异常的,与多数人没有多大关系,他们日如一日地维持自己的生活,平淡、重复,在宏观历史趋势中缺乏意义,多数人的日常状态,以及伟大人物的多数时刻都被文字制度删除了。对此,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历史档案中有一个人类生存状态的空白领域:“当时的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住什么?在传统历史的书本上,人是从来不吃不喝的。”在一个时代普遍存在的日常生活在另一个时代几乎都消失不见,所以我们不知道仁义礼智信是孔子的理想还是春秋时代的真实风俗,也不知道屈原为什么感慨“鸾鸟凤皇,日以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对于理解春秋时代的风俗而言,这并不是一个小问题。
2009~2013年,我在北京大学攻读法国史博士,论文题目是《一七六六年的卢梭》。为了这篇论文,我读了很多历史档案,同时也耗费了大量时间,从构思到出版,大约七年时间。我以极为细致的方式进入历史,不再满足于对于重大问题的宏观解读,也不再满足于用西方理论解读,我想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因为在中国学术界,很多领域还是习惯借用西方理论去解释问题。在卢梭问题上,如果这样做,意义并不大。论文是从身体、交往、舆论等角度解读卢梭的生存状态,但法国启蒙时代的日常生活仍然难以复原。他在什么情况下提出自己的观点?他的观点为什么与众不同?这是难以实现的目的。我已经进入了法国深层档案体系,但仍旧无法展示卢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也不知道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生活状态,更不知道那时的人生活在什么样的巴黎、住什么样的房子、遇到哪些日常事件和社会关系、这些如何影响了他们对于时代的理解。咖啡馆是启蒙时代重要思想的生产场所。我搜集了很多档案,但只有零星的发现,例如那时的人喜欢吃牛奶鸡蛋汤。
2016年,我的孩子出生了,我要耗费大量时间照顾她。在长达四年时间里,天气好的时候,我几乎都会抱着她在小区里玩,接触了很多人,看到了很多事件从开始到结束,然后彻底消失的过程。由于照看孩子的需要,我观察日常生活的方式变了,从间断性的方式变成连续性和高密度的方式。在这个小区里,我所经历的事情、听到的语言、看到的场景,在当下无处不在,之后却会彻底消失。它们之所以消失,不是因为不重要,而是因为太普通,在视觉意义上没有新奇感,在情感意义上没有起伏,在思想意义上缺少显而易见的意义,也就不符合文字制度的要求。然而,一旦时代变了,新的事件类型出现了,旧的事件类型的意义才会显现出来,人们却无法回溯已消失的场景。所以,我记录这些日常事件,避免它们的消失。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到“当下不断重复的困难,即日常生活无法形成历史经验而引起的现代性的单调感”。在《流动的丰盈》里,你写诸如穿着警服的巡警、大树、广告的入侵这些私人与公共空间之间的地带。你是如何观察和处理日常生活与历史、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过渡带这个问题的?当疫情这样的事件发生时,这个过渡带发生了什么变化、呈现了什么意义?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到“当下不断重复的困难,即日常生活无法形成历史经验而引起的现代性的单调感”。在《流动的丰盈》里,你写诸如穿着警服的巡警、大树、广告的入侵这些私人与公共空间之间的地带。你是如何观察和处理日常生活与历史、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过渡带这个问题的?当疫情这样的事件发生时,这个过渡带发生了什么变化、呈现了什么意义?
徐前进:19世纪以来,“现代性”一直是个重要问题,但由于现代社会不断变化,这个词的内涵也在变化。引起变化的因素很多,政治权力、经济制度、技术革新等,这是宏观分析视野;在微观意义上,这种变化表现在日常生活领域。
现代性的单调感来自于消费主义的影响。消费行为不仅仅是物质交换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心理现象,能够主导人的心理变化,让一个人高兴、难过,也能让他充满信心。物质变成了日常生活领域中的信仰。如果这个过程始终处在文字制度之外,我们就缺少了思考的第一视角,生活变得单调,每天努力工作,仅仅能从消费模式中获得存在感。而在这个时代之后,未来的人几乎无法理解这个时代的人与物质的关系,就像我们不能理解凡勃仑在《有闲阶级论》中描写的法国国王,他认为不劳动是一种荣誉,所以即使被火烤死也不移动身体:“这位国王在没有侍从官在场的情况下,坐在火炉前,竟然毫无抱怨地忍受烈火的烘烤,这使得他尊贵的躯体难以复原,但他保住了其最神圣之躯,免受卑贱的玷污。”如果文字制度进入这个领域,制造消费主义叙事,我们就有了思考的前提,以后的人也能清晰地理解消费主义时代的各种观念,例如消费行为是否具有政治功能,消费主义是深化了自由精神还是异化了自由精神等。
我还面对着一个矛盾:记录这些场景和事件到底有什么意义?它们太普通了,太微小了,每天都重复出现。即使不记录,这个世界依然存在,这个小区也一如往常,住在这里的人也照常生活。这种声音经常出现,让我不断地自我怀疑,但另一个声音也会出现:如果不记录,这些场景将会永远消失。未来的人就不会了解这个时代的基本状况。两种声音总在斗争,最后我认同了后一个声音。
这是在日常生活领域制造历史档案的尝试。由于文字制度的选择性,历史档案与当时的日常生活状态并不对应,所以现代人在梳理历史时会受到很多制约。如果一个领域中的档案很多,选择的机会就多;如果档案很少,分析的视野就会很局促。尽管历史学家已展示了微观分析的力量,但他们很难说自己对于一个微观领域的结论是准确的。
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是来自西方的两个概念。据我在英国和法国留学和生活的经历,这两个概念在生活中很重要,甚至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或日常意识形态。私人空间是独立的,公共权力不可侵入;公共空间也是独立的,私人空间不能侵入。但在中国,两个概念并不清晰;不能说这是负面问题,却可以说是一种差异。两个概念的界线之所以不清晰,与我们的习俗密切相关,例如大学宿舍有四人间、六人间、八人间,这种住宿方式没有私人空间的独立性;与之相对应的是,公共空间的边界也不清晰。当公共空间需要保护时,私人空间还是有侵入的可能。
中国的习俗中有很多稳定因素很少受到外在事件的干扰,例如对于家庭的保护,父母为了孩子可以不顾一切。近三年的疫情在事件意义上改变了小区的生活节奏,例如不可预测的封闭管理、高频率的核酸检测等。在变化中,一些深层的文化习俗再次展现,例如集体意识高于个体意识,在特定时刻,个体意识要完全服从于集体意识等。对于这个小区而言,新冠疫情所展示的首先是集体意识与个体意识的关系,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关系是次要的问题。
如果我们有意避开西方理论,还能不能讨论问题?德国学术界和法国学术界在人文科学领域是比较独立的。他们希望从自己的视野出发去认识世界、阐释世界,实际上他们也是这样做的;法国和德国的人文研究不但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而且在很多方面塑造了这个世界的思想状况。鉴于此,我想从一个具体的领域出发,抛开西方理论,设定问题,解决问题,根据我所生活的小区空间的具体状况进行具体的分析,例如有偿公共空间问题、玩物或食物在对话中的重要功能、临时公共空间的意外出现等。
在相关分析中,我没有受制于西方理论关于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设定或比例关系。公共空间在西方现代生活中有重要功能,例如在巴黎,晚上10点以后,一些街头空间基本上成为单身者的领地,喝酒、跳舞、聊天,从陌生人那里获得短暂的情感等。在中国文化机制中,这种公共空间是否是必需的,这个问题无法受制于西方理论。如果将这个小区的空间问题放在更大的分析范畴中,我认为以家庭为主体的私人空间是这个小区的主导空间,公共空间处在附属的角色,可有可无。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书中写到,普通人能够在社区中分享常识,这在一定程度上改观了他们的生存状况。这种分享常识和信息的获得与传播,你认为带着一些乡村和小镇交流方式的影子吗?在这三年疫情的过程中,你对社区的自发力量有何种观察?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书中写到,普通人能够在社区中分享常识,这在一定程度上改观了他们的生存状况。这种分享常识和信息的获得与传播,你认为带着一些乡村和小镇交流方式的影子吗?在这三年疫情的过程中,你对社区的自发力量有何种观察?
徐前进:这部作品对这个小区的深层文化状态提出了一个结论:“在日常生活中,沉默与忍耐是公共空间的主要格调。在历史意义上,这类品质有时候很伟大,它们能给予制度改革以最大的宽容,并以个体牺牲以及牺牲后的沉默去化解社会不公所造成的破坏性冲突。另一方面,它们也饱受批评,因其得过且过,无是无非,不坚守善与恶的界限,妨碍普遍正义的实践。这种批评有合理性,但不能就此否认这类品质在宏观历史趋势中所具有的宽容和博爱的内涵。”
这种宽容在中国是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可以理解为忍耐、妥协、没有原则,但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历史性的品质。西方现代政治理论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因为它是一个高于政治理论的问题:原谅那些不可原谅的,宽容那些不能宽容的。尽管在现实中,这种精神有时会遇到背叛,却是一种深奥的历史理性。
我所在的小区具备的自发力量在日常生活中很少出现。鉴于此,中国学术界一直有一个愿望,呼吁社区自治。杨玉圣对此有过相关的实践,出版了作品《小区善治研究》,但小区的物业与居民需求之间总是无法完全对应。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更好的观点;但如果换一个角度看,这应该是塑造人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在个体流动性加速的时代,传统的亲缘关系基本上已经失效,每个人面对的都是陌生人社会。在这个陌生人社会中,我们遇到了困难首先想到的不是父母,不是兄弟姐妹,而是制度,每件事背后都有相应的制度,它会提供最直接的解决方案。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的观察中,现阶段的社区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更加原子化,还是更加紧密?社区的角色在逐渐强化,还是逐渐弱化?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的观察中,现阶段的社区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更加原子化,还是更加紧密?社区的角色在逐渐强化,还是逐渐弱化?
徐前进:我在这个小区里已经生活了九年,对于这个微小空间的分析,这仍旧是一个短时段的视野。即使如此,我仍旧观察到了几个深层现象。
首先,这个小区是一个典型的现代陌生人社会,不具备自我管理能力。在情感意义上,这个小区并没有形成一个情感、理性或感觉的共同体。它的存在状态完全依靠社区政府的管理,包括建筑维修、卫生管理、公共设施的修建等。如果没有社区政府的主导,这个小区可能会陷入失序状态。
其次,社区政府为这个小区配备了大量工作人员,承担日常管理工作。即使如此,他们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在微信群里经常受到指责。与之相关的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现象是:他们用一种隐忍的态度对待这些无礼的指责。所以,这个微小空间展示了中国政治理念的一些本质问题。政治既是一个理性问题,也是一个情感问题,这种情感表现为无限度的宽容,这是西方政治学所无法解释的;这是一个人类学问题,中国自古就存在。
接着是现代陌生状态导致了个体情感隐藏。在这个小区里,尽管人与人相互陌生,甚至他们有意制造陌生,但在一些突发事件中,例如撞车、丢手机、丢钥匙等,这些人会瞬间丢掉陌生,相互帮助。我忘记过两次钥匙,但每一次都会得到陌生人的无私帮助。这些人我以前没有见过,以后也没有见过。在这些时刻,这些人可能有一种共同的情感心理,即帮助那些陷入困境中的人。
最后,由于公共观看机制的稳定存在,尤其是监控器的大量使用,这个小区是安全的,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可以自由通行,没有危险。但对于小孩来说,小区的公共空间反而减少了。一些技术保护了这个微小的公共空间,另一些技术却在其中成了危险因素,尤其是来来往往的汽车;正是由于汽车的普及,小区里独行的孩子越来越少。飞驰的汽车不是一个法律问题,也不是一个道德问题,是技术变革引起的现象,社区政府无力干预。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文化体,在中国的任何一个角落,我们可以感受到几乎相同的习俗,我们可以无障碍地与来自任何一个角落的人交往,从言谈举止的表象觉察他们的内心。我在一个东北的居住小区里观察到的很可能也适用于其他地区的居住小区,无论是西南、东南还是西北。 徐前进公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