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尹吉男:文人书房的功能维度
作者:薛芃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通常认为,书房是承载文人精神活动的空间,这种精神性的界定是如何发展而来的?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通常认为,书房是承载文人精神活动的空间,这种精神性的界定是如何发展而来的?
尹吉男:我们现在去看书房,首先还是跟藏书有关,因为书房得有书,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发生在书房里的活动,早期书房的功能就是教书、读书、写书,这是最主要的功能。先秦时期,书房跟私塾紧密相关,那时候书的形式是竹简,体量是非常大的,假如说这个书房是用来存放竹简的,那么我想这不会是一个小空间,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空间。当然这也没有太多的材料去证实,只是推测。或许有没有可能藏书跟书房是分开的,就是说要读哪一卷书就拿哪一卷书,它会有一个功能上的空间划分。
在纸出现之前,有一种替代竹简的读物是帛书。马王堆就有帛书出土,从出土物来看,帛书很薄,体量不大,比较节省空间。而且可以推断出,在马王堆所属的西汉时期,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帛书了,但这些书不是一般人读得起的,只有王公贵族才有资格使用。因此,可以推断,当时可能会出现真正意义上比较精致的藏书室,专门来收藏这些帛书。
《史记》中有一段记载,说刘邦去攻沛县,当时它是叫“书帛射城上”,就是他给沛县城里的父老写了一封动员信,这个信就是写在帛上的。这时若是用简牍就不太容易射到城上去了,因为它是有重量的,用帛书绑在箭头上就容易射得多。所以我们可以推断,在秦末的时候,帛书的形式不算少见。书的形式的变化,就关乎书房体量的变化。当纸开始普遍应用之后,最先出现的纸书是卷子书,或者叫手卷书,从汉至隋唐主流的书籍一直都是卷子书,而不是我们后来讲的册子书,也就是函装的线装书。卷子书的存放方式与函册书不同,因此也决定了书房内书架、格局的不同。至于这些书籍的形式具体是在什么时间节点发生变化的,不好明确下判断,但可以从文献里找到一些线索,比如在杜甫的时代还在使用卷子书,因为他有一句诗叫“读书破万卷”,这个“卷”就是指卷子书。
我们很容易去狭义地理解书房,认为它只是一个室内空间,但其实不一定,很多书房其实是在室外的,在园林中的,比如草堂,像是唐代的卢鸿草堂、杜甫草堂;还有一方面经常被忽略,就是很多寺庙、道观都有藏经阁,收藏历代佛家经典和道藏著作。所以书房只能用功能来定义,没法用一个绝对空间去定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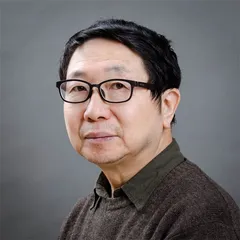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到园林中的书房,怎么理解?雅集的演变是否也与此有关?
尹吉男:中国一直有山水文化,由山水文化又衍生出园林文化,这些后来对欧洲都有不小影响,比如欧洲18世纪流行中国风的时期,也会模仿中国园林,甚至包括中国式书房。文征明所画的《真赏斋图》表现的就是苏州的大收藏家华夏的书斋,书斋在园林之中。中国书房会有一些固定陈列,不论是在室内还是室外,都会有屏风、案几、文房,还有一些博古的器物,文人很喜爱投壶运动,所以经常可以看到投壶,当然还会饮酒、焚香等等。这些活动很多是在室外完成的,比如赏画,通常认为是在室内进行的,其实不一定,它也可以是开放性的,在园林中进行。宋画中经常出现一个场景,就是挑竿赏画,这就是在室外几人一起赏画的情景,在画作拖尾的部分会留出给这些人写观后感的地方,也就出现了很多题跋。这些其实都是雅集场景。
明代的雅集已经非常普遍了,但在清代出现了一些变化,比如扬州城的一些雅集,不再是完全由文人参加,而是开始有商人加入,扬州有“二马”,即马曰琯、马曰璐两兄弟,是侨居在扬州的大盐商,非常有钱,赞助了很多扬州画派的画家,也收藏古画,因此也成为了当地很重要的文化人物,尽管身为商人,他们既藏书又出版书。他们的书房很有名,叫小玲珑山馆。叶芳林《九日行庵文宴图》里边就有“二马”和文人雅集的形象。但早期政治人物是不喜欢商人的,到了宋元明时期文人也不喜欢商人,到了清中期,商人开始介入雅集,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变化。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画作以此为题材。
尹吉男:这种画非常多,在明中期更是普遍,书斋场景甚至已经成为文人梦想中的状态,人们可以不断去想象他有很多书房,可以看到有的人有室名、别号100多个,但现实生活中,应该不可能有这么多斋、室,所以这需要辨析。这也说明这种格局和模式,已经从中央到地方精英,下沉到地方上去了,成为一个相对普及的、流行的形态。
三联生活周刊:故宫收藏有一类帝王读书图,为什么清代帝王如此热衷于请画师绘制自己的阅读场景?
尹吉男:雍正和乾隆这父子俩特别喜欢做“模仿秀”。这个喜好从雍正开始,你看他的画像,一会儿把自己打扮成道士,一会儿又是喇嘛,一会儿打扮成西洋贵族,戴着假发、拿着叉子去刺老虎,一会儿又是一个渔翁在河边钓鱼。他爱扮演各种形象。他其实也扮过苏东坡,因为画中他戴的斗笠是东坡笠。苏东坡有两个标志,东坡巾和东坡笠,东坡笠通常会出现在雨中,一般情况下就会戴东坡巾。其实东坡巾是更常见的,乾隆有一张画就是模仿苏东坡,是在园子里赏画鉴古,他穿着文人服饰,戴的是东坡巾。乾隆的读书赏画活动就是在园子里进行的。
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历史上,帝王都有两重性,一方面是帝王,一方面想当文人,也要习画作诗,因此乾隆留下的字画、题跋非常多,这些行为都是在模仿中国传统文人,他的书斋生活就显得格外重要。基本上从宋开始,历代帝王都有赏古书画的习惯,宋徽宗是一个高峰,而乾隆达到了宫廷收藏的顶峰,收藏非常多,一个地方也放不下,这些宝贝都是散放在不同空间的,各处放一点。也就是说,文人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对帝王产生了巨大影响,影响越大,他就越想融入到文人的世界里,这些画像也就是他对文人世界的向往。“雅集”的政治维度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新书《知识生成的图像史》中讨论了明代艺术家谢环的创作,在三个章节中,他都是重要的研究对象。在观看此次故宫书房展的时候,我意识到谢环与其中作品的关联。一是米友仁《潇湘奇观图》,在上世纪80年代江苏淮安明代王镇墓的出土物中,发现有宫廷画家谢环的仿米氏云山风格的山水画,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他是米氏风格的追随者;二是作为书房空间的室外环境和活动的延伸,雅集一直是古代文人喜爱的交际活动,在展览中也有所体现,谢环绘有《杏园雅集图》,是这一母题的重要作品。这两点都是你在研究中谈到的。由此首先想请问,为什么会关注到谢环?他的特殊性在哪里?

 尹吉男:淮安王镇墓出土的这几件作品确实引起了关注,这里有一件谢环的。一般认为他是个普通的宫廷画家,应该画马远、夏圭那路子的,不太可能画米氏云山,但是出土的这张画就给历代的鉴藏家打了脸。这张要不是墓里出土的,大家都会认为是假的,因为王镇墓时间较早,是弘治九年(1496)下葬的,但这张画又跟我们常见的那些画的印章都是一样的。后来国家古代书画鉴定组也做了鉴定,认为是真迹无疑。
尹吉男:淮安王镇墓出土的这几件作品确实引起了关注,这里有一件谢环的。一般认为他是个普通的宫廷画家,应该画马远、夏圭那路子的,不太可能画米氏云山,但是出土的这张画就给历代的鉴藏家打了脸。这张要不是墓里出土的,大家都会认为是假的,因为王镇墓时间较早,是弘治九年(1496)下葬的,但这张画又跟我们常见的那些画的印章都是一样的。后来国家古代书画鉴定组也做了鉴定,认为是真迹无疑。
但是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谢环要画米氏云山。因为我们过去容易把宫廷画家职业化、本质化,总认为他们上班画宫廷绘画,下班也画,睡觉也画,没有休息日,365天都在画,这是一个想象,我们不了解宫廷画家的业余生活,他业余时间画的不一定就是宫廷风格,有可能是另外一种。
另一方面,我们经常忽略他的身份。因为谢环本人就是文人,他们家是永嘉谢氏,是谢灵运的后裔,祖上是大诗人谢灵运,所以这个家族在宋元这个时期非常有影响力。谢环本身综合文化修养很高,金寔在他的《翰墨林七更》里描述得很详尽,可以看出谢环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我们从前太低估他了。那里面他谈到了文字学史、思想史、书法史、绘画史,很庞杂。金寔向谢环提了很多刁难他的问题,而谢环一一解答、一一破解,有点古代佛道论战的意思。所以这个文献也引起了我对谢环的关注。
三联生活周刊:他对米氏的追随,是否也意味着在当时这是一股风气?
尹吉男:后来在研究中我意识到,永嘉这个地方,其实只是一个小地方,而非大城市,这里也是流传着米氏云山风格的;再比如福建地区,在明初的时候就流行米氏云山的风格,说明这的确是一个下沉的审美风格的流行。永乐年间有一位福建诗人高棅,编纂过《唐诗品汇》,我们现在把唐诗分为初、盛、中、晚这种分期,都和他有关。高棅就痴迷于画米氏云山,他后来把自己的名改为“廷礼”,而米芾就曾用过“廷礼”为字号。
三联生活周刊:你指出在《杏园雅集图》里,“政治隐藏在娱乐中”,文官对宦官的情绪暗藏其中,这是否会给我们观看其他雅集图带来新的思考维度?
尹吉男:实际上,杏园的主人是杨荣,而在杏园进行的雅集与书斋之内的雅集性质一样。饮酒、赋诗、赏画。通常会把杏园雅集和西园雅集来比对,西园雅集中有司马光、苏轼、米芾、黄庭坚、李公麟等16位名士,他们饮酒、吟诗、作画,但现在有关西园雅集是否真实存在过是有争议的,很可能是虚构的。判断一个雅集是否存在,要先找雅集诗,如果找不到雅集诗,那基本上就是虚构的。雅集之后不见得所有诗文都能留下来,但至少也会残存几首。
再说回来,杏园雅集的概念表面上看是在模仿西园雅集,但诗文中却多次提到唐代的香山九老会。白居易曾经居住在现在龙门石窟对面的香山,他在那里常举办雅集,叫香山九老会,都是年过七十的人在那儿聚会,这里其实也是一个书斋与园林的结合,是半公开性质的。根据现藏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宋代马兴祖《香山九老图》来看,其中有一处后世题跋永乐时期和正统初期文官与宦官的对立与斗争,而在《杏园雅集图》中,也暗示了当时“江西文官集团”这一主题的馆阁诸公的力量,这正是今后的隐忧,所以这种现实意义就暗藏在古典意义之中了,绘画的可读性也变得更加丰富。 尹吉男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