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小时待命,不仅是出卖时间
作者:魏倩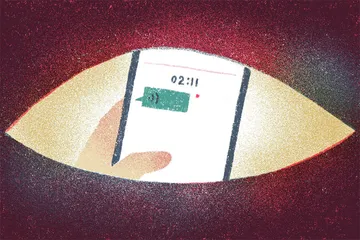 周六晚约朋友看电影,灯光调黑,人舒舒服服往后背一靠,很快进入状态。可还没看到半个小时,朋友那边手机亮起来,她匆匆回复,把屏按灭。10分钟后灯又亮,反复几次,椅背连带着整排座椅晃动,身边的人不满:“有啥大不了的事儿啊非得现在回?!”朋友连声抱歉,拿着包弯腰离开座席,轻声跟我说:“领导联系,我看不了了,大厅等你吧。”
周六晚约朋友看电影,灯光调黑,人舒舒服服往后背一靠,很快进入状态。可还没看到半个小时,朋友那边手机亮起来,她匆匆回复,把屏按灭。10分钟后灯又亮,反复几次,椅背连带着整排座椅晃动,身边的人不满:“有啥大不了的事儿啊非得现在回?!”朋友连声抱歉,拿着包弯腰离开座席,轻声跟我说:“领导联系,我看不了了,大厅等你吧。”
自去年起,朋友接下单位的微信公号,因为人手紧缺,有时连排版带推送都靠一个人。微信内容要经好几道领导审核,随便经手哪一位耽误了,她就得在办公室干等上好几个钟头。别人能耽误,她却一分钟都拖不得,遇上主管部门发布重大消息,领导一个电话过来,不管在逛街还是睡觉,都得马上进入工作状态。那之后我们见面,她出门必带两部手机,方便扫码推送,或者干脆背电脑出发,好几次下班约饭,点完菜后来条微信,她马上掏出电脑在桌上编排,餐厅气氛随之肃穆。大家对她表示同情,她说,餐桌还是小事,要是遇上地铁里没信号,就得一手举着手机连热点,一手小心翼翼刷新排版,那场面才叫紧张。这还不算,其他离谱的工作场所还有:共享单车车座、健身房更衣室、马路牙子、医院走廊……
她的状态并不是新鲜事,离开办公室就结束工作的时代早就一去不复返了。2018年,英国求职网站totaljobs向7000名上班族发起调查,发现有1/3的受访者经常在非工作时间收到老板的工作传唤,其中有一半人会马上着手处理。在国内,由于大部分人都没有邮箱办公的习惯,微信等即时通讯软件的流行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工作和生活混杂在一起,老板随时能找到你,所以必须24小时待命”的工作状态。早在20年前,海德堡大学的研究员就发现,移动技术大幅提高了人们对工作效率的期望值,“老板和同事都希望你可以随时工作”。
待命让人焦虑。就像我的朋友一样,为了减少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惴惴不安,她可以放弃一整部电影,甚至干脆在待命期(即使是周末)拒绝出门社交,靴子不落地,她几乎不能做除了等待之外的任何事情。
科学家曾在研究中量化过这种焦虑感。2016年,几位德国社会心理学家为132位志愿者进行了一项测试,第一个4天,受试者被要求24小时随时应答,第二个4天,他们在非工作时间可以选择不应答。他们发现,当要求随叫随到时,受试者清晨的皮质醇水平会比不需要应答时上升得更快,即使那天他们并没有任何工作。
皮质醇是人体内调节“战斗或逃跑”反应的重要激素,主要用于提高人们在压力之下的反应能力。正常情况下,人的皮质醇水平会在清晨达到峰值,随着时间推移慢慢降低,而科学家们的研究证明,当人预计自己会度过充满压力的一天,它的水平会比平时上升得更快。处于长期高皮质醇水平状态,人会患上“倦怠综合征”——睡眠紊乱、情绪失控、免疫力低下,记忆力和反应力降低。简单来说,就是“麻了”。
除此之外,待命状态下的人还会需要更多时间来恢复元气。研究者发现,“仅仅因为存在‘被召唤的可能’,都会影响员工的恢复能力”。当精神或身体健康状况不佳时,这种状况会变得更加严重,很多人甚至会直接选择旷工或失联。因为在他们心中,待命的时间并不真正属于自己,它既不是休闲,又不能被视为工作,那种不可预测性会带来压倒性的疲惫感。
这里还涉及人们对待命工作的一种普遍误解,认为只有实际的工作时间可以被视为“真的在工作”,难道他们不可以在等待的时候做些别的事儿吗?我曾采访过一位在急救中心工作的医生,他的工作时间被分为一个早班、一个晚班,之后可以休息两天,但任务紧张的时候,也需要24小时待命。他告诉我,一旦进入值班室,就很少能真正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件事情上,好像已经有程序在后台运行着的手机,没法再腾出空间带动更大的应用,站里的两位担架工经常靠睡觉来逃避等待,而他习惯打小游戏、刷短视频,做一切不用动脑子的事情,好让这段煎熬的时间尽快过去。
人命关天,如果说他的工作还具有“应急”的价值,多少能为无聊的等待赋予点意义,其他很多24小时待命的工作召唤几乎可以算是纯粹的精神暴力。那天把朋友逼出影院的连环call最终被证明是个乌龙。原来是领导A发微信她没回,找到领导B,后者不明所以,连打四个微信语音要求她马上回电,她不知出了什么事,慌忙打过去,领导A却说没啥大事,只是突然想起有个表她还没填。我看完电影出来,见她神情落寞地坐在大厅椅子上,抱着电脑问我:“他们怎么不考虑今天是周末呢?难道我把自己卖给他们了吗?”
24小时待命的人们经常提到这种“自我出卖”的感觉。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家提出,资本家购买了劳动力在一个工作日内的使用价值,因此资本家有权要求工人在约定时间内为他做工,围绕这个“约定时间”,双方曾经发生过激烈争执,最终确立了“8小时工作制”的共识。它也随之划出一条分明的界限:对劳动力的出卖至此时为止,剩余时间供劳动力自我恢复、自我确认和自我生产。
到了21世纪,我们不再需要在纺纱工厂里劳作,却比那时的人们更缺乏对个人时间的控制能力,由它带来的负面感受,比如沮丧和无助,很容易让人想起工业革命兴起之前对奴隶的控制,毕竟只有在那时,奴隶主才占有其附庸的全部。事实上,当上司丝毫不考虑受雇者的日常安排,要求对方24小时待命时,实际上还隐含了一种价值评判,即“我的时间比你的更宝贵”。而这关乎尊严,无法被交易。
自移动技术被发明,尤其新冠疫情引起的远程办公兴起以来,我们已经看到过太多给随时待命工作者的建议,帮助他们“平衡工作与生活”,再不济也要“从精神上将工作与非工作分开”。比如给自己设定一个关机时间,这之后不再回复邮件和信息,再比如增加心理弹性、每周运动三次、学习冥想之类。
但不少受雇者相信,这种现象的根治办法其实就在他们的雇主身上。2021年,《休斯敦纪事报》(Houston Chronicle)刊登过一篇名为《全天候工作的缺点》的文章,作者在文中专门列出了几个给雇主的忠告(你可以把它们转给你的老板):
一、告诉您的员工或下属您拥有他们的空闲时间,最终会导致员工离开。因为您不仅会使他们筋疲力尽,还在人格上侮辱了他们;
二、如果你是一名白天有太多工作要做的经理,你需要学习时间管理技能,弄清楚如何更有效地利用自己的时间,而不是让你的员工在他们的空闲时间为你收拾残局,这会显得你很不专业。
最后,文章作者提议,每次在下班时间后发送电子邮件或联系同事或下属时,请先问问自己:“我一定要现在发送这份文本吗?收到它的人会怎么看我?” 工作待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