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灭与重生的地球“密码”
作者:邢海洋 茫茫宇宙中,我们的地球是个极其独特的存在,否则也不会孕育出人类。今天我们有幸在这里回顾史前时代的生物大灭绝,也是拜地球这种独特性所赐。这里就试图寻找那些让生物历经磨难却又生生不息的地球在地球物理和地质学上的密码,从内因上剖析我们今年能生活在这里的原因。
茫茫宇宙中,我们的地球是个极其独特的存在,否则也不会孕育出人类。今天我们有幸在这里回顾史前时代的生物大灭绝,也是拜地球这种独特性所赐。这里就试图寻找那些让生物历经磨难却又生生不息的地球在地球物理和地质学上的密码,从内因上剖析我们今年能生活在这里的原因。
太阳系中地球其实也并不很孤单,地球轨道的内侧是金星,外侧是火星,它们都是固态行星,也叫类地行星,从大的分类上看,它们和我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46亿年前,宇宙的尘埃互相吸引,聚合在一起形成了太阳系,构成类地行星的物质应该是相似的。从宇宙尘埃抱团、碰撞形成熔融态的球体到如今三颗类地行星展现出完全不同的样貌,是有很多因素值得分析的。
具体到地球,地球发展史上的第一个大事件当然是冷却,能量辐射出去后,地表形成了固态地壳。另一个大事件则是一颗巨大的小行星撞击过来,把地球的一部分撞出去,碎片在太空中聚合成月亮。月亮围绕地球转,以潮汐力的方式,持久地影响着地球表面物体的运动。这件事儿居然是西方现代哲学开山鼻祖康德首次提出来的,他最早意识到在月球潮汐力的“刹车”作用下,地球会越转越慢。现在我们知道,地球最开始每6个小时自转一周,也就是说,6小时是一天,现在是24小时一天。
随后,地球经历的是一个彗星送水过程,从太阳系外部轨道飞驰而来的慧星送来巨量的水源,但最初这些水是以水汽的方式悬浮在大气中的。随着地球逐渐降温,一场维持了200万年的豪雨终于把地球变成了一个蔚蓝色的星球。再后来38亿年前蓝藻出现了。至于为什么地球上的植物选择了光谱中红光和蓝紫光作为主要的生长能量,地球从蓝色星球又变成了绿色星球,这里或有偶然成分。无论如何,一幅美丽的画卷以亿年为单位缓慢展开。
太阳起初并不如现在这样“亮”、这样热,辐射出的热量是现在的七成,这意味着靠太阳更近的金星更温暖或更适合生物生存,毕竟普遍认可液态水的存在是生命存在的一个重要条件。体积是地球的0.88倍,质量为地球的4/5,金星曾经带给人类很美好的憧憬,以为那里是地球人最理想的“殖民地”。可上世纪60年代末苏联的探测器前往观测时,还没有完全降落就被金星表面高温的腐蚀性气体弄报废了,从此人类只好把“殖民”的希望寄托在了离太阳更远的火星上。
金星表面有浓稠的大气,大气压是我们地球的500余倍。那么,当我们的地球最初形成时,是否也有着如此浓稠的大气呢?答案是肯定的,但地球的幸运就在于,它离太阳要比金星更远,温度更容易降到水的沸点下,水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以及岩石里的金属离子发生反应就产生了大量的碳酸盐,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就这样被锁定在了岩石里。及至生物出现,生物也在固碳,将二氧化碳变成沉积岩。持续了几十亿年的光合作用还不断把二氧化碳转化成氧气,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这种温室气体才能够保持在一个稳定同时也含量颇低的状态,地球的温度因此不至于太高,生命无法存活。
印象中,火山喷发遮天蔽日,是地球环境的破坏性力量。但其实,当地球进入冰河期被彻底冰封住,地球内部的热量很难通过板块运动释放出来,积聚的能量达到阈值便会集中爆发,形成一场持久的火山大喷发。火山喷发夹带出的二氧化碳和甲烷都是温室气体。温室气体中的二氧化碳就是曾经被封存在岩石里的二氧化碳气体,当地球面临着长期被冰封,碳循环以极端的方式将温室气体释放出来,完成一波对地球的拯救。
我们生活的这颗蓝色星球,其独特之处就在于它不大不小,位置恰好。地球的邻居火星因为个子太小很快就冷却了,内部变成实心的固体芯。没有了铁水的流动,也就没有办法产生能够抵御太阳风的磁场,火星大气在太阳风的持久攻击下耗散在茫茫的宇宙里,如今火星的大气密度只有地球的1%。没有了温室气体的保温作用,火星当然也不会有流动的水存在,更不会因为有水和内部熔岩的双重作用,而拥有板块运动。在火星地核还活跃的时候,无从释放的能量以火山的形式喷发出太阳系最高的山奥林帕斯山,但现在的火星一片沉寂。
直到今天,46亿年之后,地球内核的温度只比最初降低了500摄氏度,地壳之下仍是一个炽热的液态岩浆池。相对于地球6000余公里的半径,平均17公里厚的地壳比鸡蛋壳还薄还脆,而海洋下面洋壳的厚度只有5~10公里。洋壳之上,海洋的水体平均4公里深。天空之上则是一颗硕大的卫星月球环绕转动,要知道,金星是没有卫星的。上下皆液体,且是被月球潮汐力带动的液体,薄如蛋壳的地壳于是维持着自己“摇篮”中的运动。
看似不起眼的缓慢运动中,竟然隐藏着生命生生灭灭的密码。
 地球环绕太阳运动,运动的轨迹亘古不变。而太阳作为一个从青春期向着成年期稳步走来的恒星,虽然形成之初太阳的亮度只有现在的七成,但放在长时间尺度上,十亿年十分之一的亮度渐变,短期看太阳发出的光和热也是稳定的。当一次次生物大灭绝揭示出来,我们很容易联想到诸如小行星撞击或者大规模火山爆发等突发因素招致的灾难。确实,类似的偶发事件肯定影响甚至主宰了地球上生命演化的进程,但如果把地球上的生命放在一个38亿年的大的时间尺度上,反而是那些缓慢却持续发生着的地质演化、生命演替起到了更为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使是大灾难的发生,也和这些微观的作用有关系,日积月累,量变转化为质变。
地球环绕太阳运动,运动的轨迹亘古不变。而太阳作为一个从青春期向着成年期稳步走来的恒星,虽然形成之初太阳的亮度只有现在的七成,但放在长时间尺度上,十亿年十分之一的亮度渐变,短期看太阳发出的光和热也是稳定的。当一次次生物大灭绝揭示出来,我们很容易联想到诸如小行星撞击或者大规模火山爆发等突发因素招致的灾难。确实,类似的偶发事件肯定影响甚至主宰了地球上生命演化的进程,但如果把地球上的生命放在一个38亿年的大的时间尺度上,反而是那些缓慢却持续发生着的地质演化、生命演替起到了更为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使是大灾难的发生,也和这些微观的作用有关系,日积月累,量变转化为质变。
对于大尺度的气候变化,科学家们一直很是迷惑,直到上世纪50年代南斯拉夫气象学家米兰科维奇提出的米氏周期理论。他从全球尺度上研究日射量与地球气候之间的关系,地球并非完全恒定地绕地轴运动,正如我们看到的陀螺,即便轻微,但自传的时候还是会有摆动。换言之,我们经常看到赤道和南北回归线有纪念性标志,可实际上太阳的直射点每年都会有所不同,不会是一个绝对的点。每隔2万年,地球的自转轴进动变化一个周期(称为岁差);每隔4万年,地球黄道与赤道的交角变化一个周期;每隔10万年,地球公转轨道的偏心率变化一个周期。
即使太阳辐射角度有周期变化,如果地球是均一的球体,它接受的能量也是不会有差别的。差异就来自陆地,按米兰科维奇的解释,单一敏感区的触发驱动机制,即北半球高纬度地区气候变化信号被放大、传输进而影响全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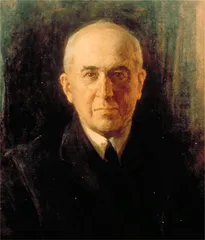 米兰科维奇理论是用来解释第四季冰期的气候变化的,放在遥远的几亿年前的古气候,恐怕解释起来都难“给力”了。
米兰科维奇理论是用来解释第四季冰期的气候变化的,放在遥远的几亿年前的古气候,恐怕解释起来都难“给力”了。
在讲述地球上漫长的地质和生命演化的时候,我想请大家观察一下自己的指甲,不是看它们长什么样,而是观察它们长的速度。当然肉眼是看不出来的,你只有在它长得碍事的时候才意识到它长了。好吧,那就干脆想一想,你多久剪一次指甲。
一般来说,成人的手指甲每周会长1~1.4毫米。这里只需要知道,指甲生长的速度和我们脚下的陆地,也就是板块移动的速度大致相仿。看着你手指尖上的指甲,再看看脚下的大地,你浮想联翩了吗?实际上,我们脚下的土地,也就是大陆板块是比较稳定的。否则,我们也就不敢铺设连伸缩缝也没有的高铁铁轨了。
不稳定的是海洋板块。在太平洋、大西洋等海洋的大洋中脊,地球内部火热的岩浆上涌,形成新的洋壳,推动着海洋的“地板”向着两边扩展,在与大陆板块抵触的地方,因为洋壳比陆壳更沉,它们就俯冲到了地壳深处,被熔融态的地幔物质加热“烤化”,最终融入地幔里。以如此龟速,海洋“换一次地板”两亿年也就过去了。
其实地球最初是没有陆地的。地球上最早的大陆克拉通(Craton),在何时以怎样的方式从海洋中浮现,是一个仍未确定的问题,过去的研究认为,它的出现大约始于25亿年前,也有一种说法是32亿年前就出现了陆地。
陆地是太阳系送给地球的礼物,这样说并非是因为其他类地行星上没有陆地,而是因为它们的表面没有地壳物质的分异,它们有的很快就冷却了,地壳不再发育;有的因为没有水没有板块活动。其实火星金星乃至月球上的化学元素和地球都是相似的,地球的原初状态就是各种元素形成的化合物抱在一团的滚烫的粥,重的物质向下沉,轻的向上浮。最初地壳冷却形成的是相对均一的岩石物质,如玄武岩和橄榄岩,它们构成了海洋板块的地壳。
陆地地壳的出现,是在地球冷却十几亿年后才发生的事儿。要知道构成陆地的主要物质花岗岩,在太阳系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无论是玄武岩、橄榄岩还是花岗岩,其实它们都是火成岩,也就是由岩浆冷却而成的岩石。不同的是,花岗岩是原始的海洋地壳整体被加热到熔融态后再分异出来的岩石,重一些的金属成分变少了,轻的二氧化硅矿物的比例更多。花岗岩的比重是2.7,比橄榄岩(3.2)轻多了,所以陆地如同洗澡时产生的泡沫飘在了地幔之上。并且随着时间推移,洗出的泡沫越来越多,漂浮于海洋上的陆地面积也日趋壮大了。
地壳下面是一个软流层,这里是流淌着的如同高炉里的铁水一样的岩浆。但软流层里的物质也并非全是液态的,有些是液态,有些是固态,是混沌的。我们知道,水结成冰体积会增大,但水是很特殊的一种存在,绝大多数物体固态是要比液态比重更大。比如高炉里的铁水冷却成铁块,体积会减小1/34。岩石的成分基本也是固体比液体重的,也就是说,一旦“冻”住体积会减小,比重增加,于是固态就有下沉的倾向,可越向下沉越热,固态就会又变成液态上浮,这就构成了软流层里一种生生不息的运动动力。至于这些动力的源泉,则既有地球形成之初保留下来的热能,也有元素衰变释放出的核能。在能量自给自足的封闭的软流层中,矿物质得以充分地移动、交换和组合,更轻的花岗岩得以产生。
当我们低下头看到广场上斑斑点点,红色的、黑白色或淡粉色花岗岩石板的时候,当我们观看冬奥会惊叹于冰壶比赛中冰壶美丽的材质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到,这是我们地球独有的造化神功。
 我们的脚下,地球的内部能量生生不息,推动着板块运动。而板块运动的规律,按照地质学家揭示出来的历史印记,地球上的陆地是分分合合的。
我们的脚下,地球的内部能量生生不息,推动着板块运动。而板块运动的规律,按照地质学家揭示出来的历史印记,地球上的陆地是分分合合的。
地球上的陆地既然起源于地壳岩石的不断融化与重结晶,这个过程就不可能只发生在某些区域,而是大面积的散状分布。表现在地表上,相信在几十亿年前地球的陆地也会是以岛屿状态凸露在海面上,而非像现在这样一块大陆几千公里纵深。事实上也是如此,地球上的陆地面积最初是比较小的,且是分散的。
30余亿年的时间里,陆地分分合合,已经有三个轮回。最早形成的是存在于15亿到18亿年前古元时代的哥伦比亚超大陆,从北到南跨越12900公里,从东到西最宽处4800公里。随后分裂开再聚合就是11亿年前形成的罗迪尼亚超大陆,此后又有冈瓦纳大陆。离我们最近的则是3.35亿~1.75亿年前的盘古大陆。
盘古大陆是提出了大陆漂移说的德国气象学家魏格纳的假想产物,后被考古发现所证实。100年前这位气象学家偶染疾病,养病的床位恰巧面对一张世界地图,而欧洲的世界地图以大西洋为中心,非洲西岸和美洲东岸的海岸线走势颇为重合。魏格纳灵光闪现,接下来潜心研究,提出了“大陆漂移说”。他认为地壳的硅铝层是漂浮于硅镁层之上的,并设想全世界的大陆在古生代石炭纪以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个学说看似荒诞不经,直到上世纪60年代科学家发现了海洋板块生长与湮灭的事实,才使得大陆漂移说发展成为板块构造理论。
大陆分分合合,每次都是聚合了又要离散开,这很像古人总结出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至于分分合合的动力机制,以当下的地球物理手段,并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科学家们只好大胆猜测,普遍认可的一个解释是,地壳下的地幔有一个全球范围的大型环流,当陆地是分散着的时候,这个环流倾向于从一个半球流向另一半球,推动着陆地向一处聚拢。可当陆地聚拢在一起的时候,因为陆地板块更厚、范围更广,庞大的陆地板块就阻碍了地幔的单向流动,陆地板块周边形成了下降流,下降流又在陆地中心上升,撕开陆地使之向着分散的方向漂浮。地球内部源源不断的能量,如同无形大手,拨弄着地表的陆地如船一样漂浮。
既然陆地在移动,其上面的气候随着位置改变而变化也就顺理成章了。地球的气候带随着光照强度而变化,赤道附近是热带雨林,向两极依次是热带草原、热带沙漠、亚热带森林、温带森林、草原等等。板块移动还在板块的边缘部位俯冲或抬升,塑造出千变万化的地形地貌,也改变了局地的气候,随之影响到动植物的生长。但问题在于,板块的运动和我们指甲的生长速度相仿,动植物是完全有时间改变生活习性,适者生存的。
但以万年乃至百万年为时间尺度,我们还是会联想到米兰科维奇触发性因素的影响。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变化,却可能触发连锁反应,给地球气候带来不可逆的影响。超大陆聚合不仅仅是陆地的拼合,同时也造成全球构造活动、海平面乃至大气成分的变化,进而气候随之变化。超大陆存在的时期,海洋板块“换地板”的周期也更长了,温室气体的循环也随着变化。
2.5亿年前的二叠纪末期与三叠纪间生命大灭绝,已经有科学家将之与盘古大陆的形成建立了某种联系。如果说那一段气候变迁离我们太远,缺乏更直观的认识,我们不妨借鉴一下更为晚近的板块运动,以及近在眼前的气候现象。
2500万年前,南美洲和南极洲是连接在一起的,两大陆的分离,直接在南极周边形成了环状的海洋,南极从此被隔离出去。在西风带的作用下,南极外海绕极环流和西风环流盛行,一个世界上所有河流流量100倍的海流,外加令水手胆寒的咆哮西风带共同统御下,南极彻底被孤立。南极银光闪闪,反射走太阳光带来的能量,南极是地球的寒极,比北极温度要低上二三十摄氏度。那里是如此奇特而孤寂,是地球上最像外层空间的地方。南极终年被冰盖覆盖,即使降水比撒哈拉沙漠还少,却积累下地球三分之二的淡水资源。因为冰盖反射太阳辐射,整个地球也因此更少地接受到太阳能量。
身处陆地环抱的北冰洋则是另一种景象,非但没有累积出厚厚的冰盖,夏天冰雪融化还能通航。
南美洲和南极洲的分裂、德雷克海峡的出现,再借助大气的行星环流,就给地球环境带来了巨大且不可逆的影响。要知道,6500万年前恐龙统领下的地球,温度要比现在高上12摄氏度。如今温度低,或者就有南极被从地球整体天气系统中分离出去的影响。即使在今天,时时影响到我们的厄尔尼诺和拉尼娜形象,都和德雷克海峡南极环流是否通畅有关呢。 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