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鹅的忧郁》:动物、语言与乌克兰
作者:后商 2022年2月24日,烈火降临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安德烈·库尔科夫在公寓中被爆炸声惊醒。2月24日凌晨和早晨,一共发生了三次爆炸,此时距离基辅上次爆炸,已经过去了7年。在爆炸声响起前,大多数乌克兰人并不相信它会发生。但早在19日,库尔科夫就感到了威胁,他在一则推特上写:“基辅天气预报:+5℃,有风,可能性是30%,但感觉就像95%。”
2022年2月24日,烈火降临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安德烈·库尔科夫在公寓中被爆炸声惊醒。2月24日凌晨和早晨,一共发生了三次爆炸,此时距离基辅上次爆炸,已经过去了7年。在爆炸声响起前,大多数乌克兰人并不相信它会发生。但早在19日,库尔科夫就感到了威胁,他在一则推特上写:“基辅天气预报:+5℃,有风,可能性是30%,但感觉就像95%。”
库尔科夫是乌克兰最重要的俄语作家,从2018年开始,担任乌克兰笔会的主席。
自第一声爆炸响起,人们就动身迁徙、流亡,或者至少藏身于防空洞。库尔科夫没有第一时间离开基辅,他和家人先走到酒店,过会儿又转移到朋友家,爆炸声消失后回到自己家中。第二天,他和妻子、两个孩子,以及不多的亲友踏上了流亡之路。他不得不把所有的家当,以及600多本个人作品的再版重印收藏——他有乌克兰最多的再版重印本——都留在了家中。他养的仓鼠和猫也滞留在了炮火中的基辅,暴露在阴霾四窜的“空城”。在最初的流亡路途上,库尔科夫并没有察觉到它们的消失,等他找到了安宁的房子,并将两个孩子送出国境,已经是3月初,库尔科夫在西乌克兰想念起远在基辅的宠物,同时他在推特密切关注着乌克兰的动物新闻,有的动物和主人一起被掩埋进废墟,有的成群结队地在街头流窜,更有一小撮伫立在断裂的大楼中,而等待它们的却不一定是救援。库尔科夫请求他的亲友,带着他的仓鼠和猫穿越炮火。
3月7日,仓鼠塞米扬和猫佩潘坐在一辆破旧轿车的后座上,朝着西乌克兰方向行进。库尔科夫断断续续在推特上实时直播了这次动物逃亡大作战。
热爱动物的库尔科夫,将这份爱写进他的作品。他最重要的两部小说都与动物有关:畅销书《企鹅的忧郁》的企鹅,以及新作《灰蜜蜂》(Grey Bees/Серые пчелы)的蜜蜂。
谈及动物进入文学的必然,库尔科夫对我说:“动物是可以被预测的,而人类就不可以。动物的行为很自然,人类即使杀害其他动物,也会默认这个事实。在这个意义上,动物与人类的相同或对照在心理学方面是非常有用的。”
人的情感进入了动物的躯体,动物的本能又回应着人存在的复杂性。
 1992年,基辅国家动物园陷入了经营困境,员工工资一度用实物替代甚至停发,动物围栏被拆除,动物无人看护,有些被流放到了动物园外。糟糕的境况一直持续到1997年。
1992年,基辅国家动物园陷入了经营困境,员工工资一度用实物替代甚至停发,动物围栏被拆除,动物无人看护,有些被流放到了动物园外。糟糕的境况一直持续到1997年。
基辅国家动物园自上世纪20年代真正建成,后来变成苏联公园体系的一部分,到1983年又升格为国家动物公园。90年代的危机堪比“二战”时期,当时园内的动物几乎全部出口到了德国。乌克兰自1991年独立后就遭遇到了巨大的经济问题,制造业瘫痪、外资匮乏,这些困境持续了整个90年代,普通人生活苦不堪言。在此情况下,动物园的经营自然谈不上良好,动物的生存状况也不佳。
在《企鹅的忧郁》里,一位落魄青年维克托领养了一只叫米沙的企鹅。米沙曾经失踪过,维克托花5000格里夫纳将它找了回来,米沙还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一颗男孩的心脏救了它的性命。除此之外,我们对企鹅米沙了解不多。它爱吃鱼,无法表现出人类那样丰富的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但米沙真确地扮演着人而不是动物的角色,而且维克托作为人类也经常面无表情。维克托和他的企鹅一起在葬礼上做司仪,米沙穿上定制西装,“阴郁而俊秀”地为逝者祷告,它的酬金非常丰厚。相比之下,维克托的300格里夫纳酬金只是小数目。维克托撰写过竞选宣言,其实只是一位受雇于人的写手,但看起来却要为工厂、工作、企业家,以及人民的生活负责,除了经济,剩下的就是党派之争。和企鹅米沙在一起的这几年,维克托的生活没什么大的波澜,既无惊人之举,也无旷世之恋。他和尼娜·斯维特拉娜的情感匆匆来匆匆去,看起来也轻飘飘的,他们捉襟见肘,局促地相聚在厨房、客厅、沙滩,满面愁容,心思缭乱。
在库尔科夫的作品中,爱情就像这样,常常是直接的——两人共同生活,虽然不对外宣称是彼此的伴侣,但分工明确,情感传统且自然。不过对照外在的环境,爱情总是蕴藏着危机,两人也像是大洪水中逃亡的动物。他们相互依赖,好似血亲,但真的也没有爱。爱,有时并不十分必要——库尔科夫在《企鹅的忧郁》及其续篇《企鹅的迷途》中向读者这样传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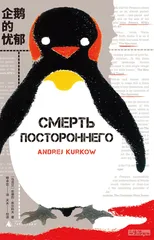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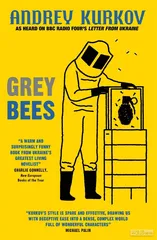 “动物很多时候能够使人更像人,因为对人类来说,爱其他动物比爱人类要来得容易。人类相信,动物很真实,如果它们依附你,就很少会背叛你。在这个意义上,动物在文学作品中永远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动物给予了人类对于人性的平衡。”库尔科夫在采访中向我解释道。
“动物很多时候能够使人更像人,因为对人类来说,爱其他动物比爱人类要来得容易。人类相信,动物很真实,如果它们依附你,就很少会背叛你。在这个意义上,动物在文学作品中永远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动物给予了人类对于人性的平衡。”库尔科夫在采访中向我解释道。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企鹅的迷途》中的一个对话:
“去动物园做什么?”
“做一只企鹅。”
胜利纪念日那天,乌克兰南极委员会将做一次南极旅行,维克托说服了委员会主席,想方设法,空运他的企鹅米沙回到南极。在整个故事的结尾,米沙看着其他企鹅扭动四肢,匍匐下水,也干脆利落地潜入海洋,没有留下一点水花。
不仅仅是巧合,库尔科夫笔下的动物都披着灰色的毛皮,企鹅、灰蜜蜂、变色龙,他养了大半生的仓鼠也是灰色的。他对灰色的喜爱,还贯彻在他自己的着装上,他总穿着灰色外套。灰色浸润开来,从宠物、衣服,扩大至人的内心、言语,再扩大至整整一个时代。企鹅成群结队地生活,很少独自生活,就像苏联解体后的乌克兰人一样。乌克兰人兀然置身于一个陌生的现场,在重新洗牌的世界格局中茫然四顾。他们已从一个如此熟悉的整体中被剥离了出去,又无法安稳地入住新的现场,迷失在陌生的、重新复苏的现代。乌克兰人身上不仅有一颗坏了的、急需更换的心脏,还惹上了后现代的忧郁症。维克托曾写作的讣闻,既是对解体前的苏联的追悼和讽刺,又是对解体后的乌克兰人的轻声安慰和祝福。亚历山大·亚可尼茨基为议会厅腾出了第三排的一张皮椅,尤利娅·帕尔霍缅科的歌声还回荡在国家剧院辉煌的纯金圆顶。而这些都在提示我们,世界唯余无穷的失落。
在静悄悄的西乌克兰,库尔科夫安好心神。他的宠物却不太妙。塞米扬瑟缩在笼子里,露出雪白的爪子,做了一次淋浴后,它灰溜溜的毛皮一霎雪白。“塞米扬现在感觉好多了。它还去散步了!佩潘正卧在暖气炉旁,享受着家庭般的温暖。”库尔科夫错估了,塞米扬没有几天就去世了。与此同时,佩潘渐渐恢复了活力。3月25日,库尔科夫写道,佩潘很开心,当你成为难民时,要明白快乐很不容易。
 俄乌冲突爆发几天后,我给库尔科夫发了一则电邮,希望和他做这一次访谈,当时库尔科夫正送两个孩子出边境,并找寻安身之所。3月7日,暂居西乌克兰后不久,他回复了这则电邮:谢谢你的来信,我可以和你进行一场对话。3月10日,他再次回邮件告知我,他会一一回应我提出的问题,但他正在移动,位置不定,不能够提前计划未来的安排。他给了我一个私人电话号码,以便保持联系。
俄乌冲突爆发几天后,我给库尔科夫发了一则电邮,希望和他做这一次访谈,当时库尔科夫正送两个孩子出边境,并找寻安身之所。3月7日,暂居西乌克兰后不久,他回复了这则电邮:谢谢你的来信,我可以和你进行一场对话。3月10日,他再次回邮件告知我,他会一一回应我提出的问题,但他正在移动,位置不定,不能够提前计划未来的安排。他给了我一个私人电话号码,以便保持联系。
库尔科夫的睡眠状态非常糟糕,通常只休息三四个小时。其间,我注意到他陆续出现在不同媒体的视频采访中,脸色一律都是苍白的。3月的外喀尔巴阡州,天气还有几缕寒意,一入夜气温就会跌到零下,公寓停了暖气和燃气,库尔科夫和他的妻子无奈地忍受着。由于物资问题,他吃了更多的面包,他最喜欢吃马卡里夫面包,不仅因为它好吃,还因为做马卡里夫面包的面包店被轰炸了。库尔科夫暂居的公寓客厅里有木质书柜,架格上所有书都是苏联时期出版的,一律的俄语书,也有些乌克兰语经典著作的俄语译本。
又过了两星期,库尔科夫终于在紧促的行程中找到了半晌的闲暇,我们约定在4月10日基辅时间上午10点见。当天,库尔科夫准时进入Zoom视频会议页,屏幕显示出了一个狭促的空间,过一会儿我才辨认出这是一间厨房。他将电脑放在操作台上,自己坐在一个低矮的板凳上,他的身后有时会飘过他妻子的影子。离开基辅后,库尔科夫一行人暂时安顿在城外90公里处,一个叫“Lazarivka”的村庄,他在此处有一座带车库和花园的小房子。可以看出,库尔科夫一直处在紧张的情绪中,睡眠不足,神情漂移。不过,他说,在访谈前一晚连续睡了8个小时,状态已经较往常好了许多。
刚开始时,库尔科夫有几分焦躁,他适应着我的中式发音,也含蓄表示了我对目前局势存在错误定位,他用严肃的口吻告诉我,这关乎乌克兰的存亡,而不只是新闻。
库尔科夫生在赫鲁晓夫当政时期的苏联,三四岁便随飞行员父亲从列宁格勒定居基辅。他的父亲在3年前以92岁高龄去世了,没有再受这次流亡之罪。父亲怀念苏联,但库尔科夫没有。库尔科夫在青少年时期就阅读了大量非常规发行出版的书籍,偏爱冒险文学,比如儒勒·凡尔纳、杰克·伦敦、欧内斯特·海明威,后来他们在库尔科夫阅读中的地位逐渐被安德烈·普拉东诺夫(Andrei Platonov)等现代俄语经典作家取代。库尔科夫从高中就开始写作,写现代诗、笑话、短篇小说。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库尔科夫在基辅国立语言大学学习,一步踏入精英阶层。他曾短暂参军,在敖德萨当狱警,分管政治文书工作,一边给其他士兵举办教育讲座,一边梦想着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
苏联解体前后几年是库尔科夫的转折时代。1988年,库尔科夫成为英国笔会的一员。库尔科夫在200名观众面前花了4个半小时朗读了一本自己写的小说,朗读完他几乎都失声了,但他从心底里认为自己已经是作家了,在场的观众也如此认为。
库尔科夫于80年代开始尝试出版作品,但直到1991年乌克兰独立前几周,他才正式出版自己的第一本书。这段经历类似于他的小说人物维克托。维克托心怀文学梦想,却始终无法完成一篇短篇故事,生计无着。在一次投稿接洽中,他阴差阳错地受雇于《首都新闻报》,以“一群老友”之名撰写讣闻。讣闻不仅写给逝者,还写给生者,他们会按时间安排人物死去,维克托生前也“被去世”了,讣闻作者也轮替给了另一个该死鬼。
库尔科夫为了把自己的文字变成油墨,伙同朋友从哈萨克斯坦购买了六吨食品包装纸,在一家油漆店印刷,再到车站报亭、大街摆摊销售,两本书每本几万册的印量不久就销售一空。为了出版《企鹅的忧郁》,库尔科夫打印了40份英文简历和作品前两章寄送给世界各地的出版商,他收到了很多出版商的拒绝信,只有一家瑞士出版社接受了。库尔科夫在家里安装了一台传真机,将原件传送给出版社,出版社收到作品后向他开出了一笔5000瑞士法郎的巨款。
库尔科夫曾模仿安德烈·普拉东诺夫的风格,写了4部短篇小说,并在1991年出版了其中两部,《不要带我去肯加拉克斯》《11件非同寻常的事》。“我仍然喜欢安德烈·普拉东诺夫,因为他改变了俄语。普拉东诺夫创造了他自己的宇宙。普拉东诺夫写的人都是很简单的人,但他尽其所能展示了人的真实。我尤其喜欢普拉东诺夫笔下这些半开化、有几分蒙昧的人,而为了书写这样的人,普拉东诺夫从一个高级的复杂的俄语,转向了一种半发达的、未完成的语言。我没有准许它们被翻译,但我非常重视普拉东诺夫带给我的天真,以及这个诚实的方法:我们必须用我们的语言忠实地描写事物,事物有多发达,语言就要有多发达。”库尔科夫对我说。
黑色幽默,是库尔科夫的主题。在他的主要作品中,库尔科夫书写了战争、墓园、失业、死亡、失恋、丑闻、腐败等事情,对性、政治、思想的探讨却好像总是戛然而止。黑色幽默对于社会来说就是集体创伤,对于个人来说就是个体反抗。“实际上,幽默会带走恐惧。当你害怕时,如果你开始发笑,恐惧就会离开,它不会离开得很远,而是变得不那么危险。这就是幽默在苏联时期如此重要的原因。苏联时期有一种讲政治笑话的氛围,人们热衷于给彼此讲笑话,而这些笑话我们知道它是反苏联的。人们认为,讲政治笑话很危险,但我却认为,假使有人嘲笑这种政治笑话,他同样也不会背叛你。笑话本就不是真的。这就形成了一个奇特的效应,那就是幽默在捍卫你的自由,同时也捍卫着你的心灵、你的头脑、你的诚实。在我的作品中,幽默能够帮助我谈论非常凄惨的事件,而不至于令读者郁闷。同时幽默也给人以希望,给人以幸福的结局。”库尔科夫对我说。
库尔科夫写了40年的日记,今年他61岁,刚超乌克兰征兵年龄。2013年,库尔科夫在奥地利出版商的提醒下将这些日记打包成了非虚构作品——《乌克兰日记》(Ukraine Diaries),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儿童文学和小说的领域,涉足非虚构,成效颇好,几乎所有关心乌克兰现状的读者都知道这本书。“如果一个人和他的国家没有发生特殊的事情,他可能就会相信,他的生活是稳定的,他的生命是永恒的。按理说,更换职业、购买房子车子、搞家庭聚会、结婚或离婚,这些时间命题大多也都是稳定的。”库尔科夫在《乌克兰日记》中写道,“我不会离开。我不逃避现实。每时每刻我都生活在现实的核心地带。我从我家的阳台就可以看到路障上的烟雾,听到手榴弹和枪械的爆炸。生活一刻也不停息,它贯穿这一切,永远前后相继。”
在西乌克兰逃难的此刻,库尔科夫搁下了正在写的小说,全身心投入另一本类似《乌克兰日记》的非虚构作品。库尔科夫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记录所见所闻上,不是官方信息和实时新闻,而是私人故事。相比于战事,他更关心他的朋友,他们的流亡、他们的洞见与情感。
他试图离开关于乌克兰的议题——他知道如何进入它的核心地带,但他没有那么做。就这一点而言,库尔科夫的观念和出生于敖德萨的诺奖作家S.A.阿列克谢耶维奇存在相似之处,后者就曾强调,历史是通过那些没有任何人记住的见证者和参与者的讲述而保存下来的。“我不是在写战争,而是在写战争中的人。我不是写战争的历史,而是写情感的历史。我是灵魂的史学家:一方面,我研究特定的人,他们生活在特定的时间里,并且参与了特定的事件;另一方面,我要观察到他们内心中那个永恒的人,听到永恒的颤音,这才是永远存在于人心中的。”S.A.阿列克谢耶维奇在《战争中没有女性》中写道。
库尔科夫或许比任何与他接洽的记者都忙碌,他生产着日记、评论、采访、活动对谈,以俄语、德语、葡萄牙语等不同语言。“我正在等待时机,回到平静的基辅,回归我的图书馆、我的书桌,重拾我写小说要用的档案,我未来的计划,以及那个几十年来以幸福为名义创造的世界。我当然无法想象,一个自我构建、自我创造的幸福将会如此轻易地被摧毁。我认为,幸福不是一种物质价值,而是一种精神、能量,当我与同样热爱和欣赏生命的人产生眼神接触,与阳光、蓝天、夏夜的星星接触,就能感觉到它。”
他传送给我动乱中最新的日记,我读完既悲叹又心酸。在写日记的间隙,库尔科夫收集仙人掌,随手拍下发在Ins,充满噪点,俗气而可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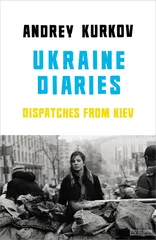 库尔科夫的推特,现在成了外界了解战乱中的乌克兰文化的一个窗口。人们通过他的动态可以了解,哪些作家和艺术家因战事去世了,哪些作家的家被导弹炸毁,哪些博物馆被破坏。科学家、翻译家奥列克桑德·基斯柳克的身亡尤其令库尔科夫心痛,基斯柳克翻译了亚里士多德、塔西佗、托马斯·阿奎那等人的经典著作。
库尔科夫的推特,现在成了外界了解战乱中的乌克兰文化的一个窗口。人们通过他的动态可以了解,哪些作家和艺术家因战事去世了,哪些作家的家被导弹炸毁,哪些博物馆被破坏。科学家、翻译家奥列克桑德·基斯柳克的身亡尤其令库尔科夫心痛,基斯柳克翻译了亚里士多德、塔西佗、托马斯·阿奎那等人的经典著作。
库尔科夫敏感于语言。他会7种语言,常说其中6种,即乌克兰语、俄语、波兰语、英语、法语、德语。在基辅国立语言大学,库尔科夫学习了4种语言,包括很少有人涉足的日语,整个基辅国立语言大学只有40名学生注册了日语课,包括库尔科夫在内的6名完成了这个课程。当库尔科夫学习日语时,他注意到他说日语时眼睛会自动缩小,几乎要眯起来。毕业后他找到了一个发挥他语言才能的工作,进入了基辅金门附近的出版社,负责将俄语翻译成乌克兰语。
80年代,乌克兰语的地位远远低于俄语,很少有人在公开场合说乌克兰语。在大街、学校,甚至出版社办公室,人们用俄语交谈,几乎没有乌克兰语的存在感。库尔科夫也是如此,他只有进入翻译工作状态时才说乌克兰语。当时乌克兰有大约200多所学校,其中90%是俄语学校。乌克兰语地位的提高肇始于乌克兰独立前后,乌克兰语成了街谈巷议、公告新闻的官方语言,精英群体被要求使用乌克兰语而不是俄语,“Kyiv”也取代了旧称“Kiev”。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在乌克兰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前两年,《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语言法》公布并推广,乌克兰语被宣布成为国家语言,一直持续至今。1992年,独立后的乌克兰恢复使用《乌克兰仍在人间》作为国歌,该曲出现于19世纪60年代。1996年伴随乌克兰新宪法的出炉,乌克兰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该文件第10条写道:“乌克兰的国家语言是乌克兰语。”
2013年,在乌克兰语学校就读的学生达到82%,这个比例高于乌克兰人所占的人口比重。在这个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大量的乌克兰人在学校说着乌克兰语,奉其为第一语言,但生活中仍然依赖俄语,心里仍然认为俄语是社交语言、日常用语。在“升级换代”期间,大多数乌克兰人同时使用乌克兰语和俄语,他们根据场合和情绪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切换,正式场合和正式词汇常常要用乌克兰语,否则可能会违反法律和禁忌。这种现象用更准确的说法是双层语言(Diglossia),但宽泛来讲双语更能说明情况的复杂程度。
加入历史情境和文化情境,乌克兰语和乌克兰文化认同的问题会变得更复杂。乌克兰历史并不是线性的,它充满戏剧化的故事、可塑的细节,以及跃动的生命。也正因如此,乌克兰历史成了欧洲历史某种意义上的核心现场。就目前而言,乌克兰尚没有一个统一的历史,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身份认同,更没有一个确定的语言史,人们甚至不知道乌克兰语的起源究竟是什么,仅依稀知道它的起源和六七世纪的斯拉夫语有关。
库尔科夫对我说:“从十六七世纪,有组织的无政府主义就是乌克兰人的底色。乌克兰人是个人主义者。如果说,俄罗斯人总有唯一一个伟大的俄罗斯形象,那么,每个乌克兰人都有他的乌克兰,他想生活在他的乌克兰。乌克兰人看中舒适,期待良好的生活状况,也在意美食。乌克兰的佳肴需很多材料和配料,做起来很复杂。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乌克兰的黑土是世界上最好的农用地之一,它可以长出除香蕉和橙子外的任何作物。”
世界文学有一个岛屿模型,即移民或流亡的艺术家相携手,共同创造一个文学共和国。由历史中少数乌克兰作家以乌克兰语创造的乌克兰文学,就是这样的一片岛屿。这些乌克兰作家脱离了既成的集团式互助赞助系统、时代性召唤,在此之外追寻着一个隐秘的信念,他们最终连接在了一起,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共同体。
库尔科夫无疑也是这个岛屿的岛民,且极具世界主义气质。库尔科夫有一个跨国家庭,他的妻子和孩子都是英国公民,同时他的文学聚焦在欧洲共享的价值,而并不仅仅是乌克兰俄语文学,类似于法语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等人。而从昆德拉、帕慕克,以及库尔科夫的角度理解何谓欧洲、何谓世界、何谓世界文学,或许较相当正统的作家更能给我们带来启发。
 1991年乌克兰独立后,库尔科夫每隔两年都有新作出版,某种意义上,他的文学生命和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在库尔科夫看来,独立后的乌克兰,其文学有7年时间的停滞期,这主要是出版发行体系、文学共识的缓慢解体和艰难重建造成的。他说到,90年代中期,卖得最好的还是大众文学,尤其是俄罗斯来的大众文学。但90年代的乌克兰文学并非如库尔科夫说的那样是一片真空,他的名作《企鹅的忧郁》就出版于90年代。更为重要的是,文学从强制性的压力中解脱出来了,原本压抑在冰层之下的厚壤开始重新生长。乌克兰的文学景观转瞬变化。审美、创造,成了新的着眼点。有的作家被精英意识所推促,拥抱现代主义精神和奇观,走向精致也走向叛逆。有些作家开始关注发生在眼前的国家灾难和民族悲剧,主动承担起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但已不同于苏联时期的说教倾向和人民理想。2014年至今,这两股力量越来越交融,读者似乎读懂了晦涩的理论和高蹈的词汇,也越来越接纳那些发自平民立场和悲怆意识的作品。
1991年乌克兰独立后,库尔科夫每隔两年都有新作出版,某种意义上,他的文学生命和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在库尔科夫看来,独立后的乌克兰,其文学有7年时间的停滞期,这主要是出版发行体系、文学共识的缓慢解体和艰难重建造成的。他说到,90年代中期,卖得最好的还是大众文学,尤其是俄罗斯来的大众文学。但90年代的乌克兰文学并非如库尔科夫说的那样是一片真空,他的名作《企鹅的忧郁》就出版于90年代。更为重要的是,文学从强制性的压力中解脱出来了,原本压抑在冰层之下的厚壤开始重新生长。乌克兰的文学景观转瞬变化。审美、创造,成了新的着眼点。有的作家被精英意识所推促,拥抱现代主义精神和奇观,走向精致也走向叛逆。有些作家开始关注发生在眼前的国家灾难和民族悲剧,主动承担起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但已不同于苏联时期的说教倾向和人民理想。2014年至今,这两股力量越来越交融,读者似乎读懂了晦涩的理论和高蹈的词汇,也越来越接纳那些发自平民立场和悲怆意识的作品。
在俄乌冲突发生的大约一个月前,根据库尔科夫近作《灰蜜蜂》改编的影片在乌克兰边境开拍。小说中虚构了一个“灰色地带”,是一个没有电的小镇,两个旧时的仇家孤零零伫立在这片废墟和焦土之上。小镇的生活充满危险,炮弹、狙击手时常来犯。主人公谢尔盖·谢尔盖伊奇是小镇的养蜂人,他的记忆斑驳褪色了,甚至连对前妻的印象都模糊了,“就好像他失去了所有感官和感觉,只有责任感幸存了下来”。谢尔盖不断做梦,然而梦里只有空白,只有蜜蜂。
中国作家写人时,笔墨常放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这是快速进入人的心灵和精神的方式。但大部分经过现代主义洗礼的作家往往并不如此,他们更擅长留白,在人与人之间安置动物、物件、碎片、历史、空间,如是人的痕迹削减了,那个超脱于人的创造者或“造物主”的痕迹却显现了出来。在谢尔盖居住的村庄,只有生活像一条河一样流动着,“除了不停地流逝,流逝又流逝,它又能做什么呢?”
(感谢郑纯名、张政硕在采写的不同阶段给予支持) 乌克兰人基辅乌克兰语库尔科夫文学历史动物乌克兰冲突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