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如何理解混沌?
作者:陈璐 2009年,物理学家、数学家弗里曼·戴森在《美国数学会会刊》中发表了一篇著名讲稿,题为《鸟与青蛙》。这本是他为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发表一百周年的讲座准备的。在这篇文章中他描述了两类数学家:俯瞰广袤数学远景的鸟和探索特定问题细节的青蛙。并沿着17世纪以来数学的发展历史,历数了在他看来属于这两类的伟大数学家。当进入到混沌理论的篇章时,他写道:“在混沌领域里,我仅知道一条有严格证明的定理,是1975年由李天岩和詹姆斯·约克(James Yorke)在他们题为《周期三意味着混沌》的短文中证明的。李-约克论文是数学文献中不朽的珍品之一。”
2009年,物理学家、数学家弗里曼·戴森在《美国数学会会刊》中发表了一篇著名讲稿,题为《鸟与青蛙》。这本是他为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发表一百周年的讲座准备的。在这篇文章中他描述了两类数学家:俯瞰广袤数学远景的鸟和探索特定问题细节的青蛙。并沿着17世纪以来数学的发展历史,历数了在他看来属于这两类的伟大数学家。当进入到混沌理论的篇章时,他写道:“在混沌领域里,我仅知道一条有严格证明的定理,是1975年由李天岩和詹姆斯·约克(James Yorke)在他们题为《周期三意味着混沌》的短文中证明的。李-约克论文是数学文献中不朽的珍品之一。”
出生于福建省的美籍数学家李天岩(1945年6月28日—2020年6月25日),是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杰出数学教授,1995年曾获得古根海姆奖。丁玖教授是他的学生,任职于南密西西比大学数学系。在本刊的采访中,丁玖向我们讲述了李-约克定理被证明的故事,以及如何从数学的角度理解混沌的概念等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据我所知,现在各学科关于“混沌”还未形成统一的定义,从数学的角度如何理解“混沌”这个概念呢?
三联生活周刊:据我所知,现在各学科关于“混沌”还未形成统一的定义,从数学的角度如何理解“混沌”这个概念呢?
丁玖:这不奇怪。许多在某个学科工作的学者都不知道这门学科的“定义”,很可能是因为它本身无法精确定义。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数学,迄今为止都没有一个关于“数学”的普遍定义。19世纪恩格斯给出了一个定义:数学是关于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学科。数量关系讲的是代数,空间形式指的是几何。当时的高等数学主要是微积分,现代数学理论还很少,近世代数也才刚刚出现不久。
从上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法国数学家团体布尔巴基学派提出数学是关于“结构”的学问。当时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数学家损失大半,剩下的也大多不再具有朝气。这些年轻的数学家觉得数学要毁在他们手上了,于是想要建立新的数学学派,便开始写书、写现代的数学教材。他们认为纯粹数学主要研究三种结构:关于连续性的拓扑结构、关于代数运算的代数结构、关于大小关系的序结构。因为很多自然现象是连续的,比如水和时间的流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研究连续函数,拓扑结构是专门研究连续性的数学概念。因为数学跟运算有关系,所以也要研究运算的代数结构。大小关系的序结构就比较好理解,比如实数1和3可以比较大小,这就叫序结构。布尔巴基学派在世界上影响很大,所以当时对数学的定义就发生了转变。
但是当代数学早已在研究更广泛的概念。上世纪下半叶美国的数学家们称雄数学界,他们为90年代写了一份关于当代数学的报告,提出“数学是关于模式的科学”。因为数学研究的是抽象的事物,不考虑具体的内容。比如1+2=3是抽象的概念,在日常生活里,早上吃了一个苹果,下午吃了两个苹果,今天一共吃了三个苹果,才有了现实意义。数学把这些共性找出来,抽象化地研究它们的关系、性质等。所以数学是模式的制造者。这是目前基本最被普遍认可的定义。但是数学研究越来越抽象,今后还有新的数学出现,数学也会随之产生更具概括性的定义。
混沌的情形也类似。它的数学概念首次由李天岩和约克在《周期三意味着混沌》(Period Three Implies Chaos)中进行了定义。实际上,那篇仅8页的短文并没有按教科书的形式给出混沌的正式定义。它仅仅对具有“周期三点”的那类连续函数,证明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结论:比全体自然数还要多的“初始点”,从它们各自的位置出发进行迭代,所产生的无穷点列,其最终走向是无法预测、乱七八糟的状态。于是他们提出了混沌的概念,第一次给出了“混沌”这个数学术语。
这篇文章引领了学术界探索混沌的热潮。在数学界,关于混沌的正式定义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在标准教科书中,比如波士顿大学数学教授罗伯特·卢克·德瓦尼(Robert Luke Devaney)的名著《混沌动力系统引论》(Introduction to Chaotic Dynamical Systems)。数学家们用三个条件定义了混沌: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拓扑传递性、周期点处处稠密。但这也不是人人接受的混沌的终极定义。
作为一种自然现象以及数学奇观,混沌可以通过不同角度来研究和刻画,如“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最终性态的不可预测性”“具有正的李雅普诺夫指数”“具有绝对连续的不变密度”等。数学界认为混沌是非线性科学中无处不在的现象,研究它的数学理论及其应用十分重要,但对混沌是否存在一种普适定义,他们基本不关心,因为这不重要。
三联生活周刊:混沌的数学名称是非线性动力学吗?两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丁玖:非线性分析创始人之一的乌拉姆说过句俏皮话:“把混沌研究称之为‘非线性分析’,就好比是把动物学说成是‘非大象一类动物的研究’”。动力系统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领域,随时间变化的任何事物都可以称为动力系统。动力系统通常分为两类:连续动力系统和离散动力系统。比如大学学习的微分方程,能够解释时间的连续变量,即是连续动力系统。离散动力系统则是在一系列不连续的时间点上考察系统的状态,通过离散时间量转化为一系列与自然数有关的函数迭代。函数迭代是什么?打个比方,计算器上有个平方键,你输入2,然后进行平方,得到4,再按平方键,得到16……以此类推,反复地把函数值放回函数里进行计算,这个过程叫作迭代。李天岩和约克的那篇文章讨论的就是关于迭代函数的问题。
混沌和离散动力系统又有什么关系?仍然回到刚才初始点为2的计算中,从2的平方到4,4的平方到16,16的平方到256……这样不断迭代下去,得到的数值会越来越大,在这个迭代点所组成的无穷数列中,可以预测到最后的结果趋向于正无穷。如果我们把这个初始点换作0.1,同样可以预测最后的结果趋向于0。但所谓的混沌是,当你取了一个初始点进行类似的迭代函数的运算后,得到的迭代点的数列,最终走向无法预测,这就是混沌。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它是离散动力系统里的一种特殊情况。
丁玖:对,不是所有的离散动力系统都有混沌。让我们来仔细看看李-约克定理。李天岩和约克的文章《周期三意味着混沌》证明了,如果一个连续函数f存在周期为3的点,那么:首先,对于任意一个自然数,存在一个点,是这个函数周期为n的周期点;其次,存在一个由不可数个点组成的集合,这些点都不是f的周期点,但从它们中的任一个点出发开始一次又一次不停歇地迭代函数f,得到的迭代点无穷点列,其最终的走向是不可预测的。
如何理解?首先,什么是函数周期点的周期?让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线性函数f(x)=-x。当x=1,第一次计算得到-1,将-1代入第二次计算又回到了1,所以1是这个函数的一个周期为2的周期点。当x=0时,它的周期是1,0因此被称为这个函数的不动点。f(x)=-x的每一个非0点都是周期为二的点。线性函数不存在周期为三的点,这很好证明,但对于包括二次多项式函数在内的很多非线性函数,都存在周期三点。
那么如果对于连续函数f,0.5是它的一个周期为三的点,可能第一次迭代到0.8,第二次迭代到0.9,第三次迭代又回到0.5。但0.65、0.55就不一定是它周期为三的点。李-约克定理说明了这么一个令人惊讶的第一个结果。对于具有周期三点的函数f,随便取一个自然数,比如10000,在这个函数的定义域里面总可以找一个点,迭代10000次后又回到初始点。但这种最终性态仍然是可以预测的,因为它反复迭代10000次后又会周而复始。所以李-约克定理的第二个结论更关键,并且与混沌有关。
大家都学过,自然数可数,实数不可数。由于周期必须为自然数,所以所有这些周期点加起来肯定与自然数一样多,是可数的。那么在这些可数的周期点范围以外,肯定能找到更多不可数、和所有无理数一样多的初始点,从这些点出发迭代同一个连续函数,无论迭代多少次都不会回到第一个点,这些迭代点组成的数列,里面的数值总是互不相同,最终的走向乱七八糟,这就是混沌。
 三联生活周刊:李天岩和约克写这篇论文,实际是在读了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茨(Edward N.Lorenz)发现所谓“蝴蝶效应”的论文《确定性非周期流》后。所以这个周期三推出混沌的证明,和洛伦茨的发现到底有什么关系?
三联生活周刊:李天岩和约克写这篇论文,实际是在读了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茨(Edward N.Lorenz)发现所谓“蝴蝶效应”的论文《确定性非周期流》后。所以这个周期三推出混沌的证明,和洛伦茨的发现到底有什么关系?
丁玖:洛伦茨分别在达特茅斯学院、哈佛大学取得了他的本科和硕士学位,两个学位都是数学学位。所以作为气象学家,他的数学功底很不错。1961年,当时他在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气象学,试图利用当时还很简易的计算机从事天气预报的数值研究。因为现实情况下天气预报的微分方程很复杂,他为了把问题简化,用了三个常微分方程,通过计算机进行数值计算,并称之为“toy weather forecast”(玩具天气预报)。
这个微分方程组构成连续动力系统,因为它得出依赖于时间的连续函数,时间总是连续变化的。所以这个微分方程的解作为时间的函数,起始于某些点的图像是一条三维空间里的燕尾蝶曲线。但这些解曲线在空间里走来走去,不知道最后走到哪里,无法预测它们的未来。
1972年,同在马里兰大学流体力学与应用数学研究所工作的气象学家艾伦·法勒(Allen Faller),将洛伦茨包括这篇《确定性非周期流》在内的四篇与天气预报模型有关的学术论文给了约克,说这些论文数学味很浓,一般的气象学家不一定读得懂,但可能对数学家的胃口。当时约克读了这些文章后,非常感兴趣,他考虑可以把这个连续动力系统转化成离散动力系统来分析。这是动力系统研究里的一条思路,最早由被誉为“混沌之祖”的法国数学家亨利·庞加莱提出。因为洛伦茨的这个微分方程组解的最终性态不可预测,约克便把这个微分方程的问题简化变成函数迭代问题,并猜想相应的函数有一个周期为三的点存在时,便会有混沌的现象出现。
约克是位非常具有原创性的数学家,他的学生评价他“不一定比他的学生知道的定理多,但是那无妨,因为他能创造定理”。尽管有了这么个猜想,但约克自己没有证明,他把这个证明交给了李天岩。从台湾清华大学数学系毕业的李天岩,微积分功底很深。李教授曾跟我讲,当初刚从台湾到马里兰大学时,约克看到他的成绩单吓了一跳,觉得他在台湾学了很多高深的数学。但李教授始终认为他是到美国后才跟约克学会了怎样做数学研究。花费两个礼拜,李天岩真的把约克的猜想证明出来了。
文章出来以后他们马上投稿给《美国数学月刊》,这是在全世界读者人数最多的数学期刊。但文章很快被退了回来,编辑说:“你们这篇文章写得太深了,我们这个杂志的主要读者是大学生。”但又补充道:“如果你们还是想投稿我们杂志的话,请改到大学生能看懂的地步。”当时他们还没意识到这篇文章真正的潜在意义,加上又很忙,文章被搁置了一年都没处理。
1974年5月底,当时最有名的科学家之一罗伯特·梅被邀请来马里兰大学数学系做了一个礼拜的报告。罗伯特·梅是位跨界的科学家,当时是普林斯顿大学动物学的教授。最后一场报告里,他用很简单的二次多项式函数Sr(x)=rx(1-x),也就是著名的“逻辑斯蒂模型”来研究种群个数随时间变化的走向。但他无法解释当r取某些3和4之间的值时,函数迭代数列出现的复杂情景。报告结束后,约克送他去机场,路上把《周期三意味着混沌》拿给他看。梅恍然大悟,并在随后的夏季赴欧访问时,到处宣传李-约克定理。而送完梅的约克回到办公室后,立刻与李天岩一起着手修改了这篇文章。约克发现了这篇文章真正的价值,它可以解释种群动力学的迭代问题,并且对气象学也有帮助,解释了洛伦茨的发现,即长期天气预报是不可能的。所以两周后,文章改好,三个月后被《美国数学月刊》接受,并于第二年12月发表。论文本身的成功加上梅的宣传,李天岩和约克很快在学术界成名。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学科都有提出混沌的现象,所以当时数学界是否存在同期类似的研究呢?如果有,整个学界为什么都开始关注到这个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学科都有提出混沌的现象,所以当时数学界是否存在同期类似的研究呢?如果有,整个学界为什么都开始关注到这个问题?
丁玖:其他比如工程学、生物学等学科确实都观察到一些奇怪的现象,但都没有给予一个“混沌”的定义。他们把这些现象作为观察结果写成论文发表,但往往无法证明,因为这些数学证明太难了。
比如现在和混沌一样有名的概念“分形”。分形的创始人本华·曼德博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英国的海岸线有多长》。他的结论是无穷长,这与人们的直观感受相违背,英国的海岸线怎么可能是无穷长呢?在多数人看来,英国是一个小国家,地理位置有限,不可能是无穷长。但他认为,由于英国的海岸线是一种分形,所以是无穷长的。但分形里很多观察,都无法从数学上进行严格证明。
事实上,一百多年前像拉普拉斯、庞加莱这些法国大数学家,他们在研究时也发现过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这个问题。对初始条件有极度的敏感性,意指即便初始条件存在一个很小的误差,最后的结果也可能产生越来越大的误差,这就是混沌,它与未来不可预测是等价的说法。拉普拉斯、庞加莱等人都发现过这个现象,但他们没有把它作为一个有重大意义的数学术语提出。
著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的演讲稿《鸟与青蛙》很有名,他在其中提到自己年轻时候的经历。20来岁他在剑桥大学念大学时,听了场女数学家玛丽·卡特赖特的报告。卡特赖特是伦敦皇家学会的第一位女性数学院士,也是著名数学家戈弗雷·哈罗德·哈代的博士生。报告中卡特赖特讲述了她在“二战”时期帮英国军方解决的一个问题,当时英国的一些军工产品出现了故障、噪音,他们不得其解,便请卡特赖特来帮他们分析,在这个过程中,她也发现了相关微分方程的解对初始条件有极度敏感性的问题。戴森在文章中责备自己当时的确没有像鸟一样的眼光,没有注意这个问题,没有对它发生兴趣,失去了很大的机会。
所以约克和李天岩的机遇很好,他们的工作是基于洛伦茨的工作,把洛伦茨的观察发现数学化,用严格的数学予以了证明。其实当时法勒给系里很多人的信箱里都放了洛伦茨的这篇论文,但其他人都没太深入考虑这个问题。约克看了后很感兴趣,又把这个文章复印了好多份给全美国到处寄,他也寄给了拿过菲尔兹奖的数学家斯蒂芬·斯梅尔。他寄给斯梅尔的复印件里写上了自己的地址、电话等信息。斯梅尔又把它重新复印,给自己所在的伯克利大学数学系印发了十来份。所以人家都以为是约克发现了洛伦茨,但其实是法勒发现了他。这是个蛮有趣的小故事。很多人做研究一个要有机遇,还有一个要有眼光。
自然科学经常是新的理论取代老的理论,但通过严格数学证明的数学理论是永远正确的,就像勾股定理一样。数学的新理论总是基于旧的理论基础一步步地发展,但旧的理论仍然正确。这也是为什么戴森在《鸟与青蛙》中表示:“在混沌领域里面,我仅知道一条有严格证明的定理,是1975年由李天岩和詹姆斯·约克在他们题为《周期三意味着混沌》的短文中证明的。”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庞加莱的三体问题,被认为是关于混沌的最初问题?
丁玖:1887年,为了庆祝自己的60岁,瑞典国王奥斯卡二世通过哥斯塔·米塔-列夫勒悬赏解决当时普遍认为重要的问题。米塔-列夫勒是当时瑞典领头的数学家,传说中因为抢了诺贝尔的女朋友,诺贝尔才不设置数学奖。这些问题中有个征求解答太阳系稳定性的问题,因为当时不知道太阳、月亮和地球这三个天体运动会不会产生不稳定性,最终会不会撞起来,想试图叫人来竞争回答这个问题,看看未来的情况。这是三体问题的一个变种。
庞加莱应征了这个问题,并拿到了奖金。但这个问题他最开始其实做错了。当他准备文章的出版时,一位年轻的数学家在负责校对的过程中发现有几个定理的证明有漏洞,便向他提了出来。庞加莱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他是创造性的数学家,想法特别多,开创了好几个学科,但他的缺点是经常证明不够完全。庞加莱仔细地思考了这个问题,试图把证明补全,这个过程里他发现有些地方搞错了,最开始他以为这个微分方程系统里不存在同宿点,但实际上有同宿点存在。这是一个关键的发现,让他理解到在某些区域里面它的解的最终性态是不可预测的,也就是这个解对初始点有极度的敏感性。
他把这个发现写下来了,但是没有用专门术语或者继续深入研究,反而因为发现了这些错误,把已经印好的初稿全部销毁。但在对这个问题解答进行修改的过程中,他创造了两门学科:一个是微分方程的定性理论,也就是动力系统;另一个他实际上也创造了拓扑学,但当时他把它称为位置分析。
三联生活周刊:实际上《周期三意味着混沌》也被认为是乌克兰数学家沙科夫斯基1964年提出的定理的特殊情况,我看到你曾谈到,沙科夫斯基为数学而数学的理念,却与混沌动力系统的发展无关。这句话怎么理解?
丁玖:李-约克定理于1975年正式发表,它有两个结论。1964年,乌克兰数学家沙可夫斯基用俄文在乌克兰的数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连续函数周期点问题的文章。但当时正值美苏冷战期间,李天岩和约克并没有看到这篇文章。所以这个故事还有段小插曲,约克出名后,有次到欧洲参加会议,一个人突然跑上来要找他谈话,这个人就是沙可夫斯基。沙可夫斯基告诉他:“你的定理是我的定理的特殊情况,并且我的结论比你的更具有一般性。”约克请他把文章寄给自己,大约两个月收到文章,一看果然不错,李-约克定理的第一个结论是沙可夫斯基定理的一个特殊情况。
沙可夫斯基定理作为一个数学定理,非常漂亮,在讨论周期点的存在性问题上更广,但它通篇没有讲到未来不可预测这种情况,和混沌无关,没有蕴含任何的混沌思想,所以在混沌学里几乎没什么地位。而李-约克定理的第二部分是从第一部分的结论进一步推导出,很自然地由有序走向混沌,开创了混沌研究的新纪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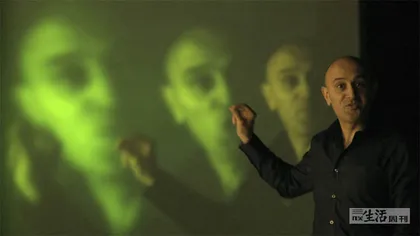 三联生活周刊:戴森那篇《鸟与青蛙》其实还写了一句,“它解释了混沌为什么在这个世界里普遍存在,但没有解释混沌为什么总是这样弱,这是留给未来的一个任务。”首先想请教一下,什么叫作“弱混沌”?关于戴森提到的这个未来的任务我们是否有了进一步的解答?
三联生活周刊:戴森那篇《鸟与青蛙》其实还写了一句,“它解释了混沌为什么在这个世界里普遍存在,但没有解释混沌为什么总是这样弱,这是留给未来的一个任务。”首先想请教一下,什么叫作“弱混沌”?关于戴森提到的这个未来的任务我们是否有了进一步的解答?
丁玖:混沌通常与“初始误差呈指数式增长”的行为相关。在现实中,指数式增长意味着极其快速的增长,在坏的情况下会导致可怕的结果,如疫情中感染人数的指数式增长。我想戴森所说的弱混沌,意思是它的不规则程度没那么强、那么大。
在力学里,一列兵士在经过一座桥时,如果步伐太一致可能会引起振幅越来越大的共振现象而导致桥倒塌。但弱混沌确保了混沌运动保持有界而不会产生猛烈变化的不稳定性,这也是为什么天体虽然存在混沌现象,因而它的轨道经常有小的摆动,但没有大到致使星体碰撞、宇宙毁灭。蝴蝶效应也是如此,蝴蝶扑闪一下翅膀会造成两个礼拜后另一个地区的暴雪,好像是部灾难片,但最后也不会让广东出现-30℃的严寒。弱混沌对于我们是好事,说明大自然还是仁慈的。
科学家们在许多物理模型中发现了弱混沌的现象,但它依然是摆在数学家面前的难题,这是戴森生前向年轻数学家提出的挑战。
三联生活周刊:最后可否介绍下你现在从事的计算遍历理论,它和李天岩、约克的研究存在哪些延续性呢?
丁玖:遍历理论通俗地说,是用概率统计的观点看混沌的动力系统。李天岩和约克均成名于动力系统领域,但他们在遍历理论和数值分析领域也有开创性贡献。李天岩一生有三大数学贡献——1975年与约克首次在数学上形成混沌概念、1976年对“乌拉姆猜想”一维情况下的证明,同年与凯洛格(R. B. Kellogg)及约克开辟了现代同伦延拓算法研究的领域。
乌拉姆猜想是遍历理论里面的一个猜想。波兰犹太裔数学家斯塔尼斯拉夫·乌拉姆是美国氢弹之父,也是冯·诺伊曼的好朋友,他1960年写了本书《数学问题集》,里面全是各种数学思想。他在书里提出了一种算法来计算用统计观点和算子方法研究混沌动力系统的“不变概率密度函数”,但他没有证明他提出的所谓“乌拉姆方法”的收敛性。
我的博士学位及后来持续30年的主要研究,是基于李天岩1976关于乌拉姆猜想工作的继续和发展,1996年我与中科院计算数学研究所的周爱辉博士(现为该所所长)曾共同证明了在高维度情况下的乌拉姆猜想。但乌拉姆猜想与周期三的问题无关。因为周期三讲的是确定性意义下关于迭代点轨道的未来不可预知性的混沌,而遍历理论研究的混沌在概率统计的意义下具有正规性态。
计算遍历理论属于遍历理论,但更偏向于研究算法,就是如何计算与混沌有关的一些统计量。一般情况下,如果对连续动力系统求解微分方程,也就是研究解的曲线,即曲线最后的走向,这可能出现混沌现象。但遍历理论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研究这种不可预测性,不管最终形态是不是可预知的,我仍然可以得到最终性态的统计规律。因为从概率统学的观点来看,尽管初始点的误差对轨道最后性态的改变很大,但是作为统计量之一的轨道点,进入某个子区域的“频度”是不改变的。也就是确定性意义下的混沌,在统计的意义下往往是正规、不具有混沌性的。这就是我所在领域的基本思想。
这是为什么数学领域非常丰富多彩的原因,因为现在数学家们都在通过不同角度来研究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 混沌微积分数学家数学迭代计算约克混沌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