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居沪漂的隔离日子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lenk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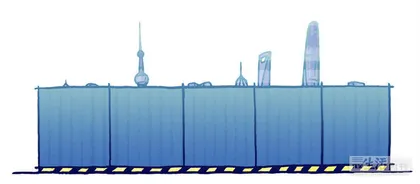 我,武汉人,“90后”,在上海读书三年,工作三年。
我,武汉人,“90后”,在上海读书三年,工作三年。
2020年,在封城前几天回到武汉,起初没预料事态发展,还庆幸自己踩点赶上了火车。
前段时间,上海疫情还没发展的时候,我曾想过,当年在武汉为什么没写写日记,记录下那段日子?回想起来,那时大部分时间都在刷抖音放松心态、和我妈因为找对象这件事斗嘴,很琐碎、单调。结果,老天给了我机会,让我在上海经历第二次,只不过这次,我没有家人陪伴,独自面对。
3月初,公司(隶属学校)安排我们进校做核酸,后来学校有人核酸异常,我们又被要求去医院做几次核酸,一开始是排队两小时,后面甚至排队四小时。我当时还只是吐槽核酸循环检测和排队的风险,没多想。转眼间整体形势不妙,我们居家办公,小区也封了。在小区排队做核酸时,有人在前面挤,和居委会的人争吵,大家都离得很近,我隐隐不安。
封控期间,照样有许多人在小区凉亭打牌、聚集聊天,甚至有人不戴口罩,小区里的菜场也无甚防护措施,没有测温仪。我又有点不安,但我从来不是那种会出头的人,相当迟钝,只是和朋友吐槽几句,也没太当回事。
武汉农村老家尚且敞亮,还可以在院子里打羽毛球、在路边散步、吃到妈妈种的蔬菜,不用自己操心生活所需。上海的独居出租屋则异常逼仄,除了下楼扔垃圾,我基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靠着勉为其难的厨艺和之前囤的一点粮食过活。
封了八天,虽然城市整体数据尚且不容乐观,但小区通知解封了,我喜极而泣,还去外面买菜。刚解封时,超市排着长龙,我下午勉强买到一些剩下的。过了两天,好像一切恢复正常了,超市人也不挤了,货架上堆满了各种商品,我买了一些,但不多。又过了一天,我们附近小区再次被封,大家嗅到信号,纷纷去超市抢购。其间,我冒着大雨去公司拿资料,看到以往人潮涌动的大街上,除了零星的外卖小哥、呜呜叫唤的救护车,几乎空荡荡的。触目所及,到处是开着小窗的蓝色围墙。
果然,第二天,我们小区又被封,因为有一例核酸阳性。陆陆续续小区封了14栋楼,楼下渐渐没有群聊的声音了。某晚下楼扔垃圾,除了穿着防护服的志愿者,路上几乎没有其他人。某栋封闭楼里传来怒吼和疯狂捶门声,好像是里面的大叔急切地让志愿者把外卖送进去。但我不想过多关注负面消息,我内心不够强大。每天和同事小p聊剧、谈吃、互相调侃,是我最大的慰藉。我本想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过下去,毕竟现在也不至于挨饿,也没遇到什么巨大的困难,除了网上买菜很难抢到、孤独、很难入眠之外,一切尚可承受。
直到某天……本栋二楼有人核酸异常,被贴封条,早上居委会让他们把垃圾放在楼道里,待会儿有专门人员帮他们扔。然而,经过多次向居委会反映后,他们答应来,又推说忙,一拖再拖,踢皮球般互推责任。楼组长怒了,说自己穿防护服帮忙扔,居委会却强调需要专门人员,最后保证明天再解决。给各种部门打电话,也没人接。毕竟是大半夜,24小时服务可能存在吗?
第二天早上,群里说那户解封了,可以自己扔垃圾。可我下楼时,那垃圾还在楼道里,没密封。可能时间还未到吧,通知和实际总是相隔甚远的。
三楼的装修师傅被困小区,每晚窝在车里休息,也不知道他怎么解决吃饭问题。楼下的阿姨骨折,医院去不了,只能在家自我痊愈。前天在居委会预订的菜,突然通知无法配送了,以后再想办法。又是一次画大饼。比起有些人的遭遇,这些或许不值一提,毕竟还安康,纵使灰头土脸、狼狈不堪地活着。
我依旧一点长进也没有,还是只能关注眼前、后知后觉,仍然陷入时代的洪流中,身不由己。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尽力维持身心健康。 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