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装没读过
作者:程旭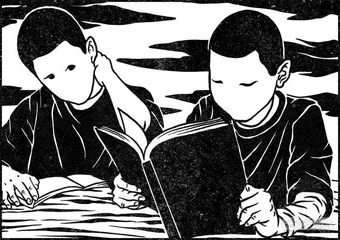 阅读鄙视链似乎一直根深蒂固地存在。某初代网红曾引发网民的围观“审丑”,大家嗤之以鼻的一点是,网红说自己从小爱读书,读的是故事和情感生活杂志。在嘲笑她的人群中,我也是笑得很响亮的那一个,好像自己从来没读过那些靠多重反转的情节和奇情耸动的标题作为卖点的刊物,而是读莎士比亚和《纽约客》长大的。其实,在我老家书柜的右下层,满层都是这类杂志,其中应该还有不少当年在火车站候车室买的法制文学。
阅读鄙视链似乎一直根深蒂固地存在。某初代网红曾引发网民的围观“审丑”,大家嗤之以鼻的一点是,网红说自己从小爱读书,读的是故事和情感生活杂志。在嘲笑她的人群中,我也是笑得很响亮的那一个,好像自己从来没读过那些靠多重反转的情节和奇情耸动的标题作为卖点的刊物,而是读莎士比亚和《纽约客》长大的。其实,在我老家书柜的右下层,满层都是这类杂志,其中应该还有不少当年在火车站候车室买的法制文学。
读莎士比亚长大的是博尔赫斯,他说一生最重要的一段时光是在父亲的大书房度过的,他在里边读但丁读《贝奥武夫》读《大英百科全书》,感觉自己好像从未从那儿离开过。号称博尔赫斯嫡系传人的塞萨尔·艾拉和前辈相比是另一个路数,他的给养是海量的好莱坞B级电影和只在超市出售的低俗小说,所以他写的故事也有一股B级味儿,比如这个:小姑娘受邀参加鬼魂们诱人的新年派对,前提是午夜12点从高楼跃下赴死。
不论是A级还是B级,没有因为接触他们变得超级,还是咱读得不够多,所谓“不怕能耐差,就怕眼睛穷”。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故事会》是“一便士惊悚小说”,狄更斯整个童年都在读这些海贼、大盗和犯罪故事,他最后未完成的小说,灵感就源于幼时读过的恐怖故事。歌德说,从流动书贩那里买来的“写在丑陋的纸上,几乎看不清”的《蛇女梅露希娜》这样的故事,对他的哲学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英国作家G.K.切斯特顿认为,这些不入流作品里“一件件繁杂琐事”包含了一切孕育“伟大文学”的主题。
柯勒律治儿时沉迷于《天方夜谭》,惹得他父亲把书付之一炬,当年我手头的金庸和同桌的岑凯伦也遭此厄运。马克斯·韦伯说“世界的祛魅”,神祇从神坛走下或跌落,如今金庸和流行歌词早已走进语文课堂,又成了“赋魅”的过程。我看过一个叫《爱情故事》的装置艺术,铺陈了一地的言情小说口袋书,旁边墙上复刻着读者写在书上的读后感、诗歌、流水账和涂鸦,艺术家试图告诉我们,这些书甜美的封面下面,还藏有巨大的表达冲动。
看电影《花束般的恋爱》才知道,还有一种“Top 1鄙视链”:自称“电影的狂热爱好者”却说喜欢的电影是《肖申克的救赎》,而对眼前坐着的押井守视而不见,这对资深的影迷来说是无法忍受的。有一回去电影院,发现一位女同事在散场的人潮中,我叫住她,问她看的什么片子,“该不会是《小时代3》吧?”我知道她平时也在朋友圈分享费里尼和小津安二郎的观影心得,所以开了这个反差玩笑。不料,她像誓言减肥的人被当场抓住吃烤五花肉,涨红了脸,眼神闪躲,不自觉地望向影厅口的海报,上面是身着华服、面容精致的少男少女。
突然意识到我犯了一个令人厌恶的错误,因为治不好自己的“装”,才去揶揄别人的“真”。所以,当我不好意思在地铁里举着悬疑小说读的时候,我应该想想萨义德的话:“你不能用禁忌来主宰真实生活,批判性的理解与解放的经验应该永远居于最高优先,无知和规避不可能是当下的适当指南。” 文学小说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