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职校的故事(上)
作者:驳静 大方家胡同在北京二环里,南北分别由金宝街和朝阳门内大街夹在腹中,不远处有著名的史家小学和北京二中,这个地儿在北京,是十足的“城里”。2005年,北京百年职校最早就办在这个胡同。办学那个小楼属于《北京日报》,报社不久前搬去新址,旧楼正打算出租,百年职校是公益办学,报社就以很低的价格将楼租给它。小楼3层,6个大房间,分别给3个班作常用教室,另外再设电脑室、图书室和会议室各一间,另有几个小房间就用作实验室,这几乎就是学校的全部。
大方家胡同在北京二环里,南北分别由金宝街和朝阳门内大街夹在腹中,不远处有著名的史家小学和北京二中,这个地儿在北京,是十足的“城里”。2005年,北京百年职校最早就办在这个胡同。办学那个小楼属于《北京日报》,报社不久前搬去新址,旧楼正打算出租,百年职校是公益办学,报社就以很低的价格将楼租给它。小楼3层,6个大房间,分别给3个班作常用教室,另外再设电脑室、图书室和会议室各一间,另有几个小房间就用作实验室,这几乎就是学校的全部。
学校创办人姚莉很喜欢这个地址,原因之一在于它的地段,她希望一直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孩子能有机会到城里上学。
百年职校1期学生王林第一次去察看这所免费学校是真是假时,撞见的还是学校装修时的大工地,连块牌子都没有。当时王林19岁,初中毕业,已经在北京的建筑工地上流转打工两年,那段时间,他正好流转到大方家胡同附近。没有逗留,他立刻就在心里给学校判了“假”,回去路上给他妈妈打电话,埋怨她听来的这个“全免费学校”根本不像个学校,而是北京常见的胡同小院儿。
王林妈妈是从电台节目《人生热线》听说的百年职校,最吸引她的是“免费”两个字。但同时,也是因为“免费”,很多人听说后都不信。第一年招生,除了在几个报纸上登广告,还有不少志愿者,去农贸市场、建筑工地和废品收购站宣传学校,散发招生通知,卖菜的、收废品的一听说“免费”,都挺狐疑。“不收学费?那孩子进去还有自由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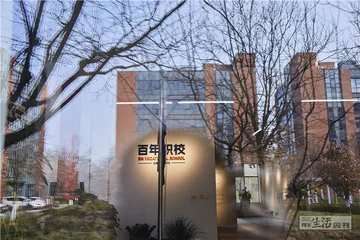 2005年算第一年,百年职校最终招生84人,这大概也是学校这几间教室能够承载的最多人数。学生们分到3个专业——电工、空调维修和管家服务,都是当时市场上的紧缺岗位。姚莉关注到这些,与她从事的行业有关。1996年,她从中国包装纸张进出口公司离职后,创办“银达物业”,算得上中国物业管理行业的先行者。从事该行业10年,她最大的感触是,物业需要专业培训,需要高级技工,她创办百年职校的初衷之一,也正是培养合格的技能型毕业生。
2005年算第一年,百年职校最终招生84人,这大概也是学校这几间教室能够承载的最多人数。学生们分到3个专业——电工、空调维修和管家服务,都是当时市场上的紧缺岗位。姚莉关注到这些,与她从事的行业有关。1996年,她从中国包装纸张进出口公司离职后,创办“银达物业”,算得上中国物业管理行业的先行者。从事该行业10年,她最大的感触是,物业需要专业培训,需要高级技工,她创办百年职校的初衷之一,也正是培养合格的技能型毕业生。
按照入学考试成绩去判断,百年职校的第一届学生中,能够达到初中毕业生水平的只有27人,那些在家乡上学的孩子成绩还好一些,跟着父母在北京到处打工、转学的学生,基础尤其差,最直观的判断依据是,这类孩子的英语成绩基本是0分。
20年前,北京的确有不少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多半可以学到初中毕业,但再往上,因为没有中考资格,他们往往面临无学可上的困境。学习基础差体现在多方面,有的数学只能得零分,有的拼音都要从头学起,有的学生跟着四处打工的父母,不断更换学校,称不上受过正规教育,连课后布置的作业要完成这样基本的意识都没有。姚莉说,最初学校里准备一顿免费的午餐,也有“留住学生”的意图在。百年职校面对的就是这样的学生群体。
姚莉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让这些农民工的孩子接受非常好的教育。所以她找来志愿授课的老师,大都是领域内的专家,来做公益讲座的,多半也是成功人士。比如,证券公司董事长、摩托罗拉总裁,还有大学教授与社会名人,他们出现在学生面前,不自觉地,总在鼓励学生去发现世界的精彩。第1期学生,着实见了一些世面。姚莉能感觉到,学生们的眼睛都亮了,很明显地变自信了,也愿意谈谈自己的理想。他们谈得最多的就是想当演员、主持人。
孩子们的主持人梦,其中一个灵感来源是赵颖。赵颖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在百年职校讲语言沟通课。他爱好中式打扮,光行头就有20多套,播音腔,声音洪亮悦耳,很有一股主持人范儿,这么一个形象往讲台上一站,对学生来说是种刺激——电台主持人站到了眼跟前儿。有一个湖南来的学生叫胡音歌,大眼睛,圆头圆脸,快人快语,第一节课下课就问赵颖“我能不能当主持人”,这位初次当老师的主持人回答说:“我争取一定把你们培养成主持人。”赵颖说,他没想到自己的自然流露,在孩子心中播下种子,真有不少人在心里做起主持人梦。
百年职校最初是两年制,到2006年,第1期学生就得去实习了,出人意料,头一个礼拜,就跑掉7个学生。其中一个实习单位是个餐厅,去了3个学生,其中一个学生还带头罢工,理由是“餐厅剥削我们”,这是他们从法律课上学到的词儿。他们刚实习,首先要传菜,这是餐饮服务行业入行必经的一条路,因为传菜过程能快速学习餐厅菜品,也最辛苦,一天下来脚就肿了。学生们在学校,感受到的是爱与关怀,谈梦想与未来,身心都没有吃苦的准备。
没跑掉的学生返校后,也抱怨太辛苦。有一个学生去的是物业公司,回来说啥也没干,“光挖沟了”。去餐厅的学生则抱怨,啥也没干,“光打苍蝇了”。还有学生回来后指点江山,说他实习那个餐厅“经营有问题”。
姚莉自己最初也曾希望毕业生能有很大出息。包括志愿来讲课的老师,都下意识地抱有这样的期待:要激发学生的远大理想。“毕业出去至少是要当领班的”,并且可以“很快晋升为主管”,姚莉还对当时国贸饭店的人力资源负责人说过这样的话:“您看我们这些学生,实习一年期满就可以从领班做起了吧?您估计他们三年内能当上主管吗?”
那是理想主义者碰到的第一个困境。这些办学者付出精力与情感,的确很像家长,恨不得把最好的东西都给孩子,同时,当然也对孩子们抱有极大的期待,几乎忘记这群孩子的学习基础与家庭基础。逃跑的孩子们让他们意识到,“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未必是真理,贫困家庭出身的孩子,未必立刻就能懂得所谓“学习机会来之不易”。
实习生逃跑事件后,学校立刻调转船头,开始在课程里增加劳动课。比如每周安排几个小时去“打扫车库”。打扫卫生这件小事,在百年职校逐渐成为一件大事。
 自打北京百年职校办出名气,找姚莉希望她把学校复制到当地的省市有不少,由于它的公益性质,各地学校大都采用合作办学模式。例如郑州,就是与河南省团校合作,校长、全职老师以及校舍都是来自该团校。
自打北京百年职校办出名气,找姚莉希望她把学校复制到当地的省市有不少,由于它的公益性质,各地学校大都采用合作办学模式。例如郑州,就是与河南省团校合作,校长、全职老师以及校舍都是来自该团校。
第一天去郑州学校,我看到教学楼走廊里几位学生在擦地,蹲在地上,用抹布一点一点擦,我的第一反应是,我在擦地的年轻人身边堂皇走过去,“这太不好意思了”。再看学生,轻松愉悦,还抬头跟我说:“老师,没关系,您往这边走就是。”仿佛对外来者的大惊小怪习以为常。宿舍上下铺,被子叠成豆腐块,在我印象里,年轻人的宿舍,只有军训期间才会短暂地保持这种面貌。打开衣柜门,一应物件也收纳得当,整齐得像是书架上的书——他们做的可不只是表面功夫。
整洁有序是具备视觉冲击力的,它能第一时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百年职校参观者对此有共同感受,这往往也是毕业生们到了用人单位后获得的第一个好评。2017年在成都百年职校入学的马巫打,毕业后去了北京的“水立方”当救生员,很快,他所在的员工宿舍就收到一条令人喜忧参半的消息:表扬该宿舍的卫生新气象——以后所有员工宿舍的内务水准向小马看齐!
成都百年职校办起来的契机是救助地震灾区的孩子,它成为第一个成功的复制品,随后郑州、武汉、丽江等地先后办起百年职校。“复制”学校,首先就要培训专职老师,而他们面临的第一个下马威就是“蹲下来擦马桶”。余忠茂,大家都叫他老余,曾到湖北省武汉、广东省梅州和贵州省雷山以及非洲的安哥拉协助办学。其中一回培训专职团队,那位校长诚恳地告诉老余说:“我这辈子就没擦过马桶。”但不做不行,因为百年职校最讲究老师“以身作则”,跪在地上擦地,只有老师熟练为之并视之为日常,学生才能从心底里接受这个俯下身子做事的观念,换言之,“不会擦马桶的不是好校长”。老余说,通常,如果学校办得不太令人满意,主要原因是教师团队难带,最大的原因是,他们是体制内员工,“又没多拿一分钱”。现在让习惯于某种模式的老师突然去做体力活,从心理层面就是巨大的挑战。
老余自己也曾是“体制内”,他2009年到北京百年职校时,刚从湖北省一个领导岗位上退休,跑到北京这样一所新学校当志愿者。起初也花了他3个月时间适应这种得坐公交车上下班、中午没有午睡的作息。但学生们都才十六七岁,方法得当,他们过去的陋习就可以得到改变。
随后,老余在学校里重点优化了“积分制”,用来整肃学生的行为规范。老余说,有不少学生刚来学校时,往地上一坐,往墙上一靠,就是不会坐在椅子上,不会冲马桶,不肯洗澡,东西乱丢。改掉这些习惯对这些孩子们很重要,因为它有助于孩子们融入城市生活。
学生们入学,前半个月是入学教育,其中重头就是清洁卫生培训。开学后,每位学生都有清洁岗位,分任务,贴岗位职责标签,每天3次(后来改为2次),每次都有专门学生检查,是扣分还是加分,每晚又有学生统计。每隔3个月,积分清零,之前要表彰一次。而这些积分,还有实际用处。百年职校免学费,学习用品、校服乃至个人电脑,学校都会想办法发给学生,唯独牙膏、洗衣粉等生活用品,只在开学初发一次。学校就成立一个小卖部,出售这些,学生可以用积分兑换。
最早,为了训练学生,学校还教过一阵“拖地舞”。那是从日本人那里学来的,拖地不是弓着背,而是挺直腰杆,有韵律有节奏地推进,到了拐角要走一个漂亮的弧线。这种形式主义的好处是,学生意识到清洁是种艺术,生活的艺术。日本人所谓的收纳力,怎么叠卷衣服、怎么做卫生、怎么收拾一个房间,呈现出来的干净与美好,最终也是提升生活品质。
北京有个创新高中叫“探月学院”,它力求培养“内心丰盈的个体,积极行动的公民”,学生的家境普遍较好。百年职校的校训则是“教育照亮人生,技能立足社会”,两所学校乍看没有共同点,甚至无论从生源还是培养目标,都是一条坐标轴的两端。探月学院训练学生的思辨能力、艺术修养,去向也多半是一流大学,而百年职校的目标,首先是学生有能力在这个社会上活下来——套用探月学院的口号,培养的是“独立有用的个体,幸福普通的市民”。有意思的是,探月学院招宿舍管理员,最后男女宿管都是百年职校毕业生。二人把在百年职校学到的扫除与收纳规范,应用到了探月的学生身上。
这两位毕业生,百年职校的校长文博都比较熟悉。他密切关注这两位学生,二人的成长轨迹促使他思考,或许到最后,教育的本质是相通的,“劳动的态度,就是人生的态度”。
去当探月学院男生宿舍管理员的同学叫朱景林,文博叫他老朱,“老朱婉拒你们的采访,理由是,他这段时间需要闭关思考”。文博说,包括婉拒记者采访,都说明,朱景林不是典型的百年职校的学生。
 所谓“典型的百年职校学生”,是王林(2005年入学,北京),或者胡波和丁聪霜(2006年入学,北京),或焦建致(2014年入学,北京)或者马巫打(2017年入学,成都),他们的共同点是,抓住一个机会勤勤恳恳,先吃饱饭过上好日子,支持家庭,做出贡献,这是一种踏实而向上的人生。而朱景林,他本来是电工班的学生,职校二年级时,因为接触烹饪选修,被它吸引,转而想当厨师,没想到还挺有天分。第二年,他在北京华尔道夫酒店的米其林餐厅应聘成功,按照这条路去走,他也是“典型学生”,在有明确发展方向的道路上获得一席之地。
所谓“典型的百年职校学生”,是王林(2005年入学,北京),或者胡波和丁聪霜(2006年入学,北京),或焦建致(2014年入学,北京)或者马巫打(2017年入学,成都),他们的共同点是,抓住一个机会勤勤恳恳,先吃饱饭过上好日子,支持家庭,做出贡献,这是一种踏实而向上的人生。而朱景林,他本来是电工班的学生,职校二年级时,因为接触烹饪选修,被它吸引,转而想当厨师,没想到还挺有天分。第二年,他在北京华尔道夫酒店的米其林餐厅应聘成功,按照这条路去走,他也是“典型学生”,在有明确发展方向的道路上获得一席之地。
可没想到,朱景林还会第二次改变主意:他打算放弃米其林餐厅的岗位,去探月学院当宿舍管理员,这个消息一传到学校负责就业的老师耳中,第一反应是明确反对。米其林餐厅厨师和宿舍管理员,显然前者更有发展空间。但是朱景林非常坚定,他说,他不会永远当一个宿管员,但他想通过这个方式了解现在中国最创新的高中是什么样子,他们在上什么样的课程。他试图寻找一些他自己心里也暂未明确的东西。
像朱景林这样的学生,实际也有不少。郑州百年职校幼儿教育专业比较出名,“典型”学生是赵艺敏,也是因为做卫生极出色,得以留在河南省数一数二的幼儿园工作。但同样是这个专业的另一位同学,实习所在的一家国际幼儿园对她评价非常高,可没多久,她自己跑去一个专业摄影机构当学徒。
尽管多数学生受益于学校非常具体且落到实处的就业指导,仍有学生,需要去寻找自己的人生道路。老师们也慢慢放手,也逐渐避免反复谈及这些毕业生里所谓的“成功典型”。
不是所有学生都是一个样式,就像百年职校并不适合所有学生。有个学生叫郑志育,父亲因工伤去世,由母亲一人带大。在学校时这孩子就特别散漫,想学好,但自制力差,没少因为违反纪律受批评,但也坚持了一年多,坚持到实习,终于跑了,连毕业证都没拿到。可就是这个孩子,过后又一边打工一边找了个职业学校上学,后来还打电话给老师,说自己在班里还当上班干部了,当的是——纪律委员,电话里,他说,“就是从百年职校学来的”。
有朱景林、郑志育这样“旁逸斜出”的毕业生,或许说明一件事:学校教不了全部,教授学生一项技能,远不如种下一颗种子。学生学到人生态度,比学到一项技能更重要。
 “假如这一年的新生里没有数学零分的孩子,倒是桩新鲜事。”这句半开玩笑的话,描述了百年职校学生另一个共同点:顽皮且学习基础差。其原因很容易总结。他们要么总跟着打工的父母辗转,有的一学年要换上两三所学校;有的来自大山深处,那儿的学校教学质量本就很差。有的初中没毕业就混迹在街上,未必认可“上学的必要性”;有的是留守儿童,学习基础相对好一些的同时,对父母有较大的怨言,这种情绪会反映到学习态度上。
“假如这一年的新生里没有数学零分的孩子,倒是桩新鲜事。”这句半开玩笑的话,描述了百年职校学生另一个共同点:顽皮且学习基础差。其原因很容易总结。他们要么总跟着打工的父母辗转,有的一学年要换上两三所学校;有的来自大山深处,那儿的学校教学质量本就很差。有的初中没毕业就混迹在街上,未必认可“上学的必要性”;有的是留守儿童,学习基础相对好一些的同时,对父母有较大的怨言,这种情绪会反映到学习态度上。
2014年入学的焦建致就是典型的代表,他既在北京上过几个农民工子弟学校,又回乡留守过,离家出走后,还在街上混过。
小焦是河北涿州人,在北京读完初一,被父母以升学为由扭送回老家后,留了几级,硬让他从小学五年级重新读起。回到涿州,小焦跟他大伯一家住。每天早上,他大娘给他5块钱,吃顿包子。中午回家,几乎顿顿是汤圆。因为大爷大娘开了家小卖部,汤圆在冰柜里囤积,卖不掉就自己吃,如果不是汤圆,就是白面条——倒不是大爷大娘虐待他,而是他们自己成天也吃这个,除非他们的儿子回家,能改善一顿。这样吃了约有半年,“日子太难熬了”。
出走前一天,也确实有导火索。那天他大伯正要揍他,“原因真想不起来了”,但“待会儿就给你捆上打你一顿”这句话记得清楚。当时小焦的舅舅正去看望,人还没走,给孩子求情说:“我还在这呢。”他大伯说:“你在咋了,他爸在我都打。”
第二天,小焦从小卖部抽屉里偷偷拿了20块钱,跑了。
先坐公交车到隔壁桃园镇,镇上有趟公交车,能直接开到北京。这趟公交车,可以刷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那张卡还是他当时被扭送回河北时带回去的,卡里存有100多块钱。到了北京房山,小焦转念一想,不能回家去,一旦回家,下场将与半年前一样,抗议,无果,然后扭送回河北,重新过上每天中午吃汤圆的日子。他就没走,找了个网吧待了下来。不是普普通通的网吧,是旁边就有肯德基的网吧,因为他身上没钱,在肯德基可以拣别人吃剩的东西,甚至晚上还能在那儿过夜,店员不会有任何意见。
一周后,撞见个熟人,那个人跟他爸妈租住在同一个院子。第二天,警察就找过来,给他带回了家。回家后,爸妈没打他也没骂他,只有妈妈指责过一句“你闯了大祸”。失踪一个礼拜后,小焦得以重新留在北京,新的初中叫京廖学校,位于房山区良乡镇。在这里,小焦遇到了他人生中至关重要的张老师。
张老师教数学,其他什么科目也都教一点,在小焦心中,张老师就是那个助他“改变命运”的人。他给班上13位同学买了车票,带大家去参观百年职校。张老师游说同学们时说,百年职校一是免费,二是它不看学习成绩,只看学习态度。他告诉同学们,大家毕业后出去,也没别的办法,顶多跟着他们的爸爸干苦力活,不如跟他去看看这所学校。
在那之前,小焦同桌,一位女同学,有一天突然告诉他说不准备念了,要回家结婚。同桌把手机里的短信展示给他看,说:“你看,我男朋友对我多好,我要回安徽跟他结婚。”小焦当时非常吃惊,他隐隐觉得这个事情“不知道是对是错,但很奇妙”。同桌很快就辍学了,事实上,即便才16岁,他也观察总结,他们这所初中的学生人数,总是越来越少。他们班上最后共13名同学,初二有20多人,一年级则是两个班,加起来有70人。而他们班去参观后,最后真正听进去张老师的话去参加入学考试的只有3人。
其中两人被录取,没录取的那位同学,语文考卷的作文部分一个字都没写。小焦分析,这或许就是“学习态度不端正”的表现。小焦从来也不是学习成绩好的学生,他在“百年”入学考试中,数学只考了16分。但他把张老师说的“学习态度好”这几个字听了进去,面试中,老老实实地按要求“拧了几个螺丝”。入学前,聪明的焦建致已经领会到,这是所需要他踏踏实实的学校。
数学16分,还不是最差的。有些学生读一个学生手册都读不下来,对英语一窍不通的更是大有人在。抽烟、奇装异服、不受管教,这样的孩子比比皆是。小焦头脑灵光,也能静下心来学。有的学生在教室里根本坐不住,甚至从来没做过作业。1期学生刘辉来最初是妈妈带着去报名,看上去“很想上学”,但开学第一天,就在姚莉眼皮底下“抓耳挠腮,不停乱动”。姚莉让他站起来读学生手册,发现他很多字根本不认识。这个孩子,入学考试,数学4分,英语0分,语文20分。
刘辉来也是典型的农民工子弟,从小跟父母在城里打工,四处辗转上学,从城里到老家,在同一个学校待不到两年,受的教育零散且随意。比如老师问他为何不交作业,他就说:“我从来没做过作业。”学校只好加大力度,专门帮刘辉来补习,班上学习成绩最好的王林,就当过刘辉来的补习老师。
王林显然是另一种情形,他或许就是姚莉办学伊始想象中那种学生,因贫辍学,一旦重新获得学习机会,就如饥似渴。按照王林的中考成绩,他能考上他家乡的重点高中,只是他妈妈罹患乳腺癌并、举债治病后,王林主动提出辍学,跟着爸爸到北京的工地上打工,最开始到北京,身上还背着课本。后来他到朝阳门内小街那一带上工,经常能看到北京二中的学生,上学下学的时候看到他们,“觉得能在北京上学真特别好”。所以王林到了百年职校,自己就会主动去学。但他的许多同学,在学习动力和学习习惯上,需要依赖外界的帮助。
 从学生人数来看,每届不到100人,百年职校可能是全国规模最小的学校。一些课程设计往往可以做到严丝合缝地适配学生需求,比如,数学课,工程维修班学起来以函数为主;而对管家服务班的学生,重点放在应用计算上。
从学生人数来看,每届不到100人,百年职校可能是全国规模最小的学校。一些课程设计往往可以做到严丝合缝地适配学生需求,比如,数学课,工程维修班学起来以函数为主;而对管家服务班的学生,重点放在应用计算上。
语文课干脆不按传统来,而是拆分为国学、语言沟通和应用文写作三门。应用文写作,就讲如何写“请假条”、数字大小写,如何写“停水通知”。同时也讲“通知”张贴在哪儿最合适。而这样教学来自一场“血的教训”。有一回有个大楼停水,就是“百年”学生写的通知,但是贴的位置不醒目,结果当晚有人在家里杀鸡,发现停水无法收拾血淋淋的现场后,怒气冲冲地跑到物业投诉。
百年职校是“全员教学”,老余也上过应用文写作课。他比较得意的一次教学是“策划书”。临近新年,老余布置做元旦晚会策划书,并宣称以小组为单位,哪个小组的作业好,就让他们主办这个晚会。几个策划书交上来,老余一看,心中有数,但还是让每个组上台演示并投票,票选胜出者与他心中的最佳是一致的。
语言沟通课培养孩子的表达能力,用意是提升学生自信心。北京的学校,一直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赵颖在讲这门课。国学课则给学生讲人生大道理——人生大道理,学生能听得进去吗?直到2期学生丁聪霜谈起,我才意识到,几乎每位毕业生都提到说“国学课收获最大”,他们会动情地说“想念刘老师”,“刘老师几年前去世了,要不你就可以采访他,并且肯定会喜欢他”。
刘老师叫刘方成,他曾将一所中学的语文高考成绩带到全区第一,后来又做成人教育,教学方法多样。原来他给姚莉物业公司的保安讲语文课,很受欢迎。他到百年职校后,除了上课,也经常参加教学会,会上听到哪位同学犯个什么错,他就从知识里搜罗一个应景的道理,用讲故事的方法输出给同学。这种方式取得的效果是,毕业生们有的离校多年,到今天张口还能背“仁、义、礼、智、信、温、良”……今天还在实践国学课学到的几项人生哲学。刘老师曾让学生们回家去给父母洗脚,就是因为察觉到很多学生与父母缺乏沟通,不理解父母的辛苦,特别是留守儿童,多少有种被遗弃的感受。
同时,一些课程也具有实验色彩。比如,学校从一开始就非常看重学生的艺术修养,不希望孩子们毕业了除了走上工作岗位,其他什么兴趣都没,比如只懂修空调,生活过得很枯燥。但艺术课同样要适配学生。中央音乐学院的一位老师答应义务授课,最早他的教学计划是“西方古典音乐欣赏”,大纲洋洋洒洒、充满激情。他后来看学生们入学时写的《我的故事》,再看他们的档案,就意识到,古典音乐恰恰不适合,不如改教民歌,同学们来自全国各地,也有少数民族,民歌最能让他们产生共鸣。
光是欣赏不够,学校很快成立合唱团,这是受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之启发。姚莉说,这是全校师生必看电影,她的本意是希望老师去了解,好老师要“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孩子,用不同的方法去激发孩子”。但她发现,很多学生也是流着泪看完电影,深感音乐的力量。她不知道的是,有些学生毕业多年,最怀念的就是合唱团。
丁聪霜就是其中之一。她是2期学生,2008年毕业,那一年正赶上金融危机,工作普遍难找。她去一个会计师事务所面试,听老板说,公司并不太需要人,学校唐老师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于是给了“百年”学生一个工作机会。那位老师叫唐欣欣,当过班主任,也负责毕业生的实习工作安排。这家事务所是百年职校的志愿合作单位,过去几年都在义务为它做审计。唐老师听我提起这事,对自己给学生的帮助不以为意,说“那或许就是老板的智慧”。不管是老板的智慧,还是学校的教育使然,丁聪霜在这家公司兢兢业业十多年,现在已经晋升为事务所合伙人。
丁聪霜在合唱团担任女高音,跟着合唱团表演过不少次,参加慈善晚会,或音乐比赛,因此去过一些高级酒店,“我们农民工的孩子,哪来这种机会”。但印象更深的是站在舞台上表演,“站在台上,看到这么多美好,看到更多的希望、更多的光,会觉得,我也是见过世面的人了,我以后要自信一点”。
她告诉我说,她到事务所那年刚满18岁,这个工作机会对她来说有难度,因为这是个跟数字打交道的公司,虽说是从前台做起,可报表上全是数据,她内心忐忑。认为自己本来数学就差,但心里反而因此有股劲,不能掉链子,不能给学校丢脸。
工作到第二年,她犯了她自认为的第一个错,与业务与关。一位级别比较高的项目经理,做的审计报告被客户退回来好几次,她在办公室里调侃了对方一句,“你行不行啊!”那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一个网络用语。丁聪霜说,她当时并没有察觉有误,因为自觉跟他已经比较熟悉。直到第二天,她听到另一位同事也在用这句话调侃对方,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逾矩了。事实上,那位经理并没有在意,但她却把这件事记到现在,认为自己应该“谨言慎行”,“说什么话,要考虑别人的感受,尤其是公共场合,是要考虑会给对方带去什么影响”。
她回想起,有一回刘老师讲什么是“好学”,讲的是《论语》里孔子对颜回的评价,讲颜回“不迁怒,不贰过”。这句“不贰过”,在丁聪霜理解中就是同样的错误不犯第二次。孔子又说“每日三省吾身”,那天之后,她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将当天发生的大小事情在脑子里过一遍。直到第五年,她犯了第二次错,仍是与同事交谈中的无心之失。这两件事她记到了现在。教育的本质是什么?丁聪霜在学校所学甚至与技能无关,她念念不忘的是艺术体验和人生哲理中的“生活教育”。(未完待续) 姚莉百年职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