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文明人的疾病
作者:维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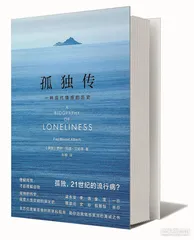 一百年前,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曾感叹:“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置身于人群之中,却又得孤独生活更可怕的事了。”如果说在他所生活的那个年代,能领会这种感受的人还未必很多,那么到如今,几乎每个现代人都会有深切的共鸣。孤独早已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流行病,《经济学人》在几年前就曾不无夸张地宣称“孤独是21世纪的麻风病”——传染性强,且极难治愈。
一百年前,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曾感叹:“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置身于人群之中,却又得孤独生活更可怕的事了。”如果说在他所生活的那个年代,能领会这种感受的人还未必很多,那么到如今,几乎每个现代人都会有深切的共鸣。孤独早已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流行病,《经济学人》在几年前就曾不无夸张地宣称“孤独是21世纪的麻风病”——传染性强,且极难治愈。
说孤独是一种“现代情感”,倒不是说古代人就不会孤独,但在漫长的历史中,这即便存在,也大抵是极少数人的体验,从未进入社会主流。心理学家弗洛姆早就曾说过,现代自我是随着个体化进程而发展出来的,然而在自我力量增长的同时,“另一方面是孤独日益加深”;相比起来,中世纪的人在现代意义上是不自由的,但他们有归属感和安全感,“既不孤单,也不孤独”。
16~17世纪时,“孤独”仅指一个人独处的状态,并不涉及丰富的内心活动。直到18世纪,西方文化中对“孤独”的理解通常只留意到其身体性(人们会形容这样一个落落寡合的人“冷”),却不像现在这样注重其内在的心理和情绪。1719年问世的《鲁滨逊漂流记》中,主人公虽然孤身一人流落荒岛,然而小说中却没有一处提到他感到“孤独”。不仅如此,当时人们对孤独也没什么好感,狄德罗就曾说过:“为人邪恶才会离群索居。”
在早期的历史上,孤独感其实是最敏感的那些文艺心灵才能最深切感受到的,那几乎是一种天赋,因为他们的卓尔不群天然使他们无法与人打成一片。这既赋予了他们远离人群喧嚣的自由感,能从外部冷静地观察人世间,但也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英国女诗人拉德克利夫·霍尔半自传性的小说《孤寂深渊》中,就突出了女性在遭受外部世界孤立时压倒性的孤独感,这本身就塑造了她独特的自我意识。直到近一两百年来,孤独才从一种精英的情感经验,逐渐变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孤独也被民主化了。
古代社会之所以极少有人孤独,原因很简单:在一个无力应对外部风险的时代,独自生活的个体很难生存。西欧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出现了一种史无前例的全新理念,那就是个人主义,把人首先看作是一个独特的个体,而非面目模糊的群体中卑微的一分子。根据托克维尔的洞见,只有当家庭传统逐渐对个体失去约束力或意义时,个人主义才能得以兴盛起来。在近现代史上,这种“个体的解放”长久以来都被认为是一件好事,因为你自此摆脱了出身所限定的命运,通往无限可能,也正是由此出发,自由、宽容和个人权利等承诺才得以从这个内核推演出来。
从这一意义上说,“孤独”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社会形态发生结构性改变之后浮现出来的复杂情结,只有把它放在社会背景下,才能真正理解它意味着什么。实际上,不同时代、不同文化对“孤独”的界定和感知都会有所不同。在中国,“孤独”原初的含义是相对于亲属网络而言的:“孤”是幼而无父,“独”是老而无子,所着重的是其在社会上的孤立无援,无可依恃,直到相当晚近才与独立、不从众乃至异化等更抽象的含义产生关联。“孤独”之所以难以精确定义,正是因为其内涵随着社会的变迁在不断发生流变,而这本身就是我们理解社会和时代特质的一个极好切入点。
由一个英国人来写这部《孤独传》,可能也最适合不过——因为普遍公认英国是第一个现代社会,按照艾伦·麦克法兰的看法,个人主义甚至是英国人的一项现代发明,本书也强调“孤独之所以在英国出现,就是因为更关注个人”。然而,随着现代社会为个人生存提供了更好的条件,每个人都减少了对他人和集体的依赖,在突出自我独特性的同时,又使人陷入更普遍的孤独,而在“上帝死了”的年代里,人们也只能独自面对所有的风险。这种“脱离部落状态”的原子化过程,最终给社会成员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紧张感。
据2008年英国的一份调查报告,全国上下都普遍感到“不断加深的孤独”,而这种孤独感的增长正始于个体解放之风盛行的20世纪60年代。新文化脱胎于战后的富裕社会,推崇“即刻得到满足”的“占有性个人主义”,离婚率开始攀升,而原有的邻里纽带也随着眼花缭乱的人口流动而逐步被削弱了。
在一两百年前,“孤独”所面对的社会背景仍是对个体的束缚,因而它仍然与一系列正面意味相连(特别是摆脱群体压力、自愿从纷繁的生活中抽身而退,并保留自我认同),到了今天,它却俨然成了一种危险的生活方式:孤独与安慰性进食、肥胖、缺乏体能锻炼这“三位一体”密切相关,意味着社会变得越发冷漠,向城市化、匿名化社区转变,弱化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和公共参与,最终可能危及公共生活。
这是一种文明人的疾病,与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也只有到了后工业时代,人们才开始因为难以逃避的无归属感而重新认识孤独本身。这并不仅仅是社会的情感结构发生了变化,或是人们的身体和心理健康遭到了威胁,还意味着公共生活的萎缩,因为人们退回到自己的城堡里,宁愿沉浸在更加私密化的乐趣之中,仿佛人已经不再是一种社会化的动物了。
问题并不只是孤独,也取决于现代人整体的情感结构。与孤独相应的是,人们如今可能比任何时代的前人都更注重“爱”——每个人都想寻找到那个“灵魂伴侣”,相信有了这“重要的另一半”,才能使我们获得完整。然而,与此同时,这种现代爱情观本身又往往是高度私密化的,对自我意识的坚持也使人更不愿妥协,其结果反倒可能加深了人的孤独感。
在西方社会的语境中,孤独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医学化和政治化的——通俗地说就是,社会上关注的是孤独引发的身心疾病和对社会政治生活的低参与度。在社交媒体的时代,“社区”往往只意味着虚拟的网络社区,但这却反过来强化了人们的孤独感。这提醒我们,不管技术如何发达,它都不能替代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互动与联结。
反过来说,孤独既是个体解放的代价,却也正因为与外部联系的弱化,使人们摆脱了外力的左右,促进了内在心灵的丰富化。真正的问题或许并不在于孤独本身,而在于每个人能否有自由的选择:虽然不同的选择都伴随着代价,但良好生活应当是允许人们在权衡利弊之后做出自愿选择。因为说到底,人们并不是不想要他人的温暖,只是不想因此丧失了自我。 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