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人的播客生活
作者:乌里扬诺娃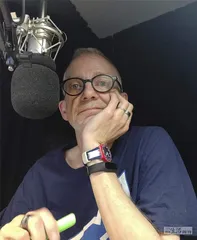 俄语世界中的播客最早被上溯到1989年发行的一盘磁带,是一本独立杂志的伴生物。
俄语世界中的播客最早被上溯到1989年发行的一盘磁带,是一本独立杂志的伴生物。
1989年,两位来自俄罗斯南部城市顿河畔罗斯托夫的记者创立了一本介绍地下文化的独立杂志《乌拉砰砰!》(Ura Boom Boom!),并随之推出配套音频节目《独立广播幻觉》。节目的名字颇具自嘲精神。在严格的媒体审查环境下,顿河畔罗斯托夫第一家真正的独立广播电台直到1992年才成立。
节目共录制四期,收录了不少当地地下乐队的现场演出录音,还与国外音乐人进行对谈,讨论诸如俄罗斯音乐家移民之类的话题。如此“离经叛道”的内容无法进入公共广播,便被录制在磁带上全国发行。在没有互联网、文化生活匮乏、思想暗流涌动的时代,这些可以反复收听的声音精准击中地下文化爱好者,在小圈子内被奉若珍宝,像极了播客的史前形态。
2005年,受到美国掀起的播客风潮启发,俄罗斯知名电台主播瓦西里·斯特雷尔尼科夫(Vasily Strelnikov)在自己的卧室里成立了俄罗斯第一个网络电台,取名“海盗广播”。紧接着他又创立了俄罗斯第一家播客平台Rpod.ru。俄罗斯播客的历史由这里正式开启。
在这股自我表达的新浪潮下,一批有着独特行业背景和生活经历的俄罗斯人,找到了比文字传播效率更高的发声渠道。
旅居上海的俄罗斯人阿里克第一次坐在《老外播客》(Laowaicast)的话筒前,是2009年的冬天。邀请他的是三位居住在上海的同乡——谢尔盖、“马玉玺”和伊万诺夫。
几位主创人员都是上海的俄罗斯俱乐部成员,早已积累下深厚友谊和合作经验。早在2002年,谢尔盖和阿里克就参与了网络论坛“东半球”(Polusharie.com)的创建,供俄罗斯人分享在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生活体会。
到《老外播客》创立的2009年,“东半球”的访问量已超过850万人次,发帖数超过1.5万篇。论坛的联合创始人在一次会议发言中说,生活在异国他乡的俄罗斯人缺乏便捷的信息交流渠道,“互联网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信息出口,既可以关注俄罗斯和世界新闻,也可以利用网络提供的机会,尝试建立自己的日常生活”。从论坛到播客,中国话题在俄罗斯网民中已经积累了相当的关注度,《老外播客》的出现恰逢其时。
做一档聊中国的播客,这个想法由谢尔盖首先提出。他与马玉玺一拍即合,很快建立了《老外播客》网站。第三期节目,他们请来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律系、从1990年起就在中国生活的老“中国通”伊万诺夫加入节目。伊万诺夫沉稳的声线和有趣的谈话方式很快让谢尔盖和马玉玺折服,成为了节目的第三位主持。而从第五期加入节目的阿里克坚持到了今天,从早期的嘉宾,变成《老外播客》目前唯一的主持人。
2009年,无论在中国还是俄罗斯,受限于网络环境和硬件条件,播客都还是一种只在小众范围内传播的媒介形式。但得益于自由简单的传播方式,一些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外国人,纷纷选择播客作为发表观点、分享资讯的方式。
他们之间常常惺惺相惜,比如一家加拿大中文学习播客Chinesepod.com就伸出援手,主动与《老外播客》分享专业录音室,让此前只能在团队成员家中“打游击”录制的《老外播客》显著提高了节目音质。
在尚不发达的网络传播环境下,技术出身、熟悉网页制作的内行人马玉玺,是让《老外播客》迅速发展壮大的重要人物。阿里克对他赞不绝口,“《老外播客》的成功关键之一,就是马玉玺在各个播客平台上的积极推广,尤其是带着我们的节目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
2009年到2012年,《老外播客》在各类大赛上屡次斩获奖项,包括在“全球播客大奖赛”(Podcast Awards)上获得多项提名。为了给节目拉票,马玉玺经常在俄语论坛上一页页发帖,介绍《老外播客》的节目详情。
有趣的是,早期的播客奖项经常只是博客大赛中的一个类目,比如《老外播客》入围最终轮的2010年“世界最佳博客大赛”(The Best Blogs 2010)和2011年“俄语互联网博客大赛”。当时播客还未被看作一种成熟独立的媒介形式,只是文字博客的变体。直到2012年,《老外播客》才终于获得了一个专属于播客的俄罗斯本土奖项——PodFM.ru网站举办的“777播客大赛”最佳播客奖。
作为Rpod的竞争对手,PodFM的出现标志着俄罗斯播客开始早期商业化尝试。2007年,马克西姆·斯皮尔多诺夫(Maxim Spiltonov)看中播客的商业前景,决定建立一个营利性质的播客平台。斯皮尔多诺夫是个典型的互联网创业者,尝试过网站、电子杂志、在线百科等项目,而播客是他嗅到的下一个风口。
PodFM的运作方式对用户来说更为友好。斯皮尔多诺夫复制了Rpod网站的所有功能,加入话题合集和热门推荐栏目,最大的创新是添加了“PodFM独家”标签,试图将热门播客独揽门下。他们为头部主播提供服务,换来对方在节目中对平台的宣传。
遗憾的是,俄罗斯播客行业并没迎来斯皮尔多诺夫想象中的春天。在收听环境尚不成熟的情况下,PodFM过于急切的商业化尝试适得其反。2011年,试图尽快盈利的PodFM与俄罗斯电信运营商MTS达成了一项资费协议,下载1M节目居然要50卢布,这意味着一期节目要付费将近1500卢布(按照当时汇率大约315元人民币)。此举受到媒体攻讦。
两家播客平台在平行的道路上渐行渐远。2014年,斯特雷尔尼科夫开始寻找愿意收购Rpod的买家,但显然无人看好这家俄罗斯播客元老级平台的商业潜力。斯特雷尔尼科夫最终宣布Rpod网站将在2015年初停止运营,没有说明原因,只留下一句愤愤不平的“播客已死”。“我们从不迎合听众”
与Rpod的倒下形成鲜明对照,《老外播客》穿越了播客行业的风风雨雨运营至今。俄罗斯播客界经历的大起大落,对于这档根植于中国的节目来说似乎不相干。
尽管2014年下半年由于主创成员的生活变动,节目更新频率有所下降,但在Rpod关站的次年1月,《老外播客》又恢复了每周一次的更新频率。
当被问及《老外播客》成功的关键是什么时,阿里克的第一反应是“我们从不去考虑迎合听众,在个人兴趣和观众喜好之间,总是选择个人兴趣”。他一再强调,“我们不会为了播放量去研究数据,从来没有过”。
《老外播客》关于中国的视角深入而恳切,到了令中国人都咋舌的程度。
主创们的音乐品位独到又狠辣。节目坚持使用山人乐队的歌曲当片头曲,一开始是《三十年》,中间曾短暂变更为《酒歌》,后来又回到《三十年》。一打开节目音频,就能听到西南民族乐器伴奏下的云南话念白:“小瞿生活过呢个好?猪么猪没有养,人么人病重。”紧接着就是主持人的俄语开场白。两条音轨在耳机里碰撞交接,立刻竖起“老外看中国”的鲜活印象。
每期节目结尾,他们都会播放一首贴合主题的中国歌曲,所有节目插曲在俄罗斯社交网站VK上集结成一个播放列表,名字是俄语拼写的“好听”,共有75首歌。怀旧的有邓丽君、宋祖英、刘德华,通俗的有周杰伦、蔡健雅,洗脑的有《卡路里》《小苹果》,更多的是来自山人乐队、五条人、玩声乐团、海龟先生、逃跑计划等小众乐队的个性之作。其中一些音乐人的名字,大多数中国人可能闻所未闻。
除了从在华外国人角度分享中国生活经验,比如怎么在中国当翻译、怎么来中国留学、如何使用移动支付等,他们也和中国百姓一样关注民生问题。“上海菜市场惊现夜光猪肉”“戴什么口罩能防雾霾”“环保烟花为何难卖”等等,都能成为他们的话题。间或插播一些无厘头的社会热点新闻,比如“90后徒手攀爬上海中心”“中学生头悬梁备战高考”。阿里克作为一名中国古典文化爱好者,还会带来中文古诗俄译这样的高深文化议题。
在早期节目中,《老外播客》坚持使用颇有时代特色的中国新词,“比特币”“给力”“超生”“皮包公司”等等不一而足。最令人称奇的是,早在2014年,他们在节目中就谈到了“996”,起因是马玉玺成为了阿里巴巴公司的员工。这期节目里,几位主播分享了自己的人生转折,末尾灵性地配了一首周先生乐队的《真实谎言》:“水玩出位,船被风吹,诱惑本来无罪。”
整个播客产业对于阿里克来说却极其陌生,他对别人的节目如何风生水起不感兴趣。阿里克有些不好意思地承认,自己从来没有听过其他俄语或中文播客,“生活里还有太多其他事情,我有孩子、有工作、有自己的博客,连电影都不看,实在没时间听播客。相比信息量稀疏、不适合快进的音频节目,我更喜欢阅读”。
2014年,《老外播客》的主要成员开始各奔东西,伊万诺夫被派到欧洲工作,谢尔盖云游四方,马玉玺则投身中国互联网大厂。阿里克也曾短暂地离开过中国,后来又回到了这片他深爱的土地,独自支撑起《老外播客》的制作工作。
对于朋友们的离开,阿里克抱着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一开始我和谢尔盖、马玉玺也通过网络通话,各自录下自己的音轨,然后汇总制作。但他们渐渐觉得失去了那种朋友们坐在一起聊天的氛围,不在中国生活,谈论这些话题可能也不那么有趣了。”
如今阿里克独自担当主持人,寻找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的嘉宾对他来说不是难事,这反而是结识新朋友的有趣途径。近期的嘉宾里有在深圳AI行业工作的程序员,有研究中国文言文的学者,也有谈中国手机游戏的从业者。他笑着说,当然也欢迎老朋友们回来,在《老外播客》重聚。

 2015年Rpod.ru关站后,俄语播客曾偃旗息鼓了一段时间。带来新生机的,是一家新闻门户网站的无心之举。
2015年Rpod.ru关站后,俄语播客曾偃旗息鼓了一段时间。带来新生机的,是一家新闻门户网站的无心之举。
2017年,美杜莎通讯社(Meduza.ru)几位看好音频节目的新闻编辑自发在下班后留下来录制播客。录制环境相当简陋,就在公司茶水间,旁边贴了张A4纸,手写着“安静,我们在录播客!”
起初他们只是将晚间新闻录成音频版,得到大量正面回应后,又加入了评论与对谈。播放量很快突破百万,《美杜莎内幕》成为播客复兴时代大多数俄罗斯人听的第一档播客节目。
这样的成功在项目负责人看来始料未及:“俄罗斯几乎不存在播客市场,一切都是从零开始。”在美杜莎通讯社的示范下,主流媒体纷纷跳进播客蓝海。今天,俄新社、《生意人报》、《俄罗斯商务咨询》等传统媒体都已经成立了自己的播客频道。美杜莎通讯社成立了自己的播客制作室,打造出一批经常占据排行榜前列的节目。
俄罗斯头部互联网公司Yandex旗下的音乐平台开始专门扶植独立播客,女性群体、两性关系成为新崛起的热门话题。在单身母亲众多的俄罗斯,专门讲现代女性育儿的《新母亲》获得了Yandex的青睐。该平台还收录了诸如《俄罗斯性爱故事》这样大胆的两性主题独家播客,大胆谈论如何变得性感、性爱中的满足感、怎样改善性爱体验,收听量很快突破200万。
疫情给播客行业添了一把火。在俄新社今年年初的调查中,近65%的俄罗斯人表示他们会定期收听至少一个播客,超过30%的人每周会听几次,10%的人每天都离不开播客。与此同时,近一半的受访者承认,2020年他们收听播客的频率比以前高得多,27%的人每天听30到60分钟的播客,20%的人收听时长超过一个小时。
在俄罗斯,播客的启动资金并不昂贵,麦克风大约合700~1400元人民币,音频可以发布在平台或者自己的服务器上,此项花费每年约800~5000元人民币。莫斯科的平均薪资大约在6000元人民币左右,这对于在大城市生活的人来说是一笔不难承担的投入。头部播客的收入说得上可观,俄罗斯最长寿的播客节目之一Radio T的播放量达到每期10万次,每月收入1000~3000美元,播客终于快成了一门有赚头的生意。
新播客随之不断涌现,据播客研究网站Podcasts.ru统计,2020年俄罗斯平均每天出现12档新的播客节目,目前Yandex Music上共有1.3万余档播客节目。新内容多了,听众的注意力也随之被分散。
说起听众的反馈,阿里克有些怅惘。近年来,评论数量显著下降。他们播放量最高的“在中国做翻译”一期发布于2019年,收到22条留言,许多都像小作文一样一写十几行。而近一年的节目,评论数大多只有两三条,最多不超过10条,都是寥寥数语。
阿里克认为,评论数下降的一个原因是受疫情影响,俄罗斯人很难来到中国,没有实地生活体验,也就少了感受。另一方面,“人们变懒了,可能是因为现在大多数人在手机上听播客,如果要给单期节目留言,就必须打开我们的网站,而愿意花几秒钟时间打开网站的人,越来越少了”。
《老外播客》从未考虑过商业化的问题。谈到广告,阿里克用了“牛仔布”这个词。在俄语里,“牛仔布”是软广告的别称。据说这个表达起源于苏联时期,当时的“黑布贩”跟着美国潮流追捧牛仔布,而电视上身着牛仔裤的年轻人就成了最早的软广告。阿里克向我强调,即使“看似没有打广告,其实有推荐商品”的软广告,他们也绝对没有做过。一切只从内容出发,无关商业利益。
而在今天的俄罗斯,播客的商业前景已经被主流品牌承认,“牛仔布”一样的软宣传层出不穷。阿尔法银行推出了理财节目《钱来了》,儿童食品厂商“水果阿姨”成了育儿播客《从头而育》的赞助商,均不失为比较成功和得体的参与方式。 播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