卵巢癌:从传统模式到维持治疗
作者:王珊 肖院是在化疗第六次之后才知道了自己的病情实情。那天,她跟家人一起走进医院。这家医院位于上海,是国内排名前列的妇产科医院。肖院这次看诊只有一个诉求:按照医生的治疗方案,肖院手术后需要完成8次化疗,但化疗太痛苦了,她想停下后面的化疗。“每次化疗,我都吐得很厉害,闻到油烟味就想吐,喝水会吐,甚至后来形成了条件反射,走进化疗的楼都会吐。”
肖院是在化疗第六次之后才知道了自己的病情实情。那天,她跟家人一起走进医院。这家医院位于上海,是国内排名前列的妇产科医院。肖院这次看诊只有一个诉求:按照医生的治疗方案,肖院手术后需要完成8次化疗,但化疗太痛苦了,她想停下后面的化疗。“每次化疗,我都吐得很厉害,闻到油烟味就想吐,喝水会吐,甚至后来形成了条件反射,走进化疗的楼都会吐。”
除此之外,每次化疗之后,肖院的白细胞数量都降得很低。白细胞对于维持人体的免疫功能非常重要,一般来说,患者化疗后白细胞正常范围为4000~10000/毫升,肖院最低的时候只有600/毫升。这意味着,如果她不能及时打上升白针,时刻都面临着感染的风险,也没有能力进行下一次化疗。每个化疗疗程,肖院都会将打升白针的时间和白细胞值记录下来,试图琢磨出自己白细胞上升下降的规律。从生病开始,肖院的工作就停了下来,她几乎将自己封闭起来,不想跟外人联系,怕别人问起自己的情况,家人也不让她上网查与病情相关的内容。“我所有的时间都围绕着呕吐和白细胞指数打转。”肖院觉得自己的人生停滞了。
肖院的主治医生是个50多岁的女性,长得很和气,一再劝肖院再坚持一下。肖院很坚决,“我不要再化疗了”。医生也急了,提高了音量,说:“你要是Ⅱc期或者是Ⅲa期,我也就让你停了。”话刚说完,坐在肖院旁边的家人突然在桌子底下踹了下医生。整个诊室瞬间沉默了下来,就连所有人的表情都凝固住了。肖院有些恍然,她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她没有再说什么,安静地走出了诊室。
肖院是在2017年4月因为腹痛去医院做检查时被确诊为卵巢癌的。超声的结果显示她的腹部有一个巨大的囊肿,医生高度怀疑是卵巢恶性肿瘤。这个消息,家人再三考量后选择不告诉她——她才33岁,在一家外企做管理工作,事业有声有色,才刚结婚一个月,还没有孩子。他们怕她承受不了这突然袭来的打击。手术前,肖院只知道,考虑到她还未生育,医生会先用腹腔镜进行探查,取病理,如果是恶性肿瘤会立即转为开腹手术。肖院对自己的病情很乐观,手术前,她在线问诊了许多医生,因为她腹中囊肿大小已经有13厘米,却没有腹水,不少医生认为她可能是良性的巧克力囊肿。
腹腔镜探查的结果显示,肖院体内的病灶不仅累及双侧卵巢,还存在明显的淋巴结转移,是一个典型的晚期病理,手术即刻转为开腹手术。手术时间持续了6小时,除了子宫、卵巢之外,还切除了大网膜、阑尾、左侧的宫颈韧带、直肠表面的病灶等。肖院醒来时,摸着身上近30厘米长的疤,除了痛哭之外,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那一瞬间,她觉得自己没有未来了。她看着家人手中的病历,上面写着卵巢透明细胞癌Ⅰa期。家人安慰她,卵巢癌很难被早期发现,70%的患者发现时都是晚期,“早期的生存率有90%,你算是幸运的”。
第七次化疗之前的这次门诊,让肖院意识到父母给她看的病历是假的,“他们将病历拍照,PS之后,再打印出来,还自己去刻了医院的章盖上”。她也才明白为什么每次去门诊见医生,父母都让她待在外面等会儿,他们先进去,然后再把她叫进去。“他们给我的说辞是担心我脾气大跟医生吵起来,所以先去跟医生打个招呼,其实他们是怕医生病人多,一时间忘记就露馅了。”就连进了诊室,都是肖院的家人坐在靠近医生的桌子前,肖院则挨在家人旁边坐着,“紧挨着医生的座位能看到医生电脑上的病历”。父母小心翼翼的呵护让肖院觉得,活着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责任,她选择继续剩下的两次化疗。
2017年9月底,第八次化疗之后,肖院做了增强CT。CT显示她的腹腔右侧升结肠上段旁有个约1.1厘米的结节,除此之外,其他一切正常。肖院的主治医生认为这个结节大概率不是恶性。肖院觉得自己恢复了健康,她让护士取下了支在胳膊上的PICC管,这是一种静脉置管,可以解决化疗时多次扎针引发的静脉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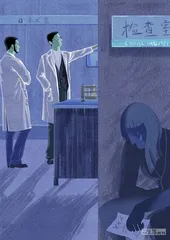 肖院没有想到的是,化疗刚刚结束两个月,她去做基因检测,检查的报告显示,她的血液里发现了与原发肿瘤组织一致的基因突变信息,这意味着,肿瘤可能卷土重来了。肖院立即赶到医院做了PET-CT,检查结果显示,肖院升结肠旁的1.1厘米结节已经长到了3厘米,且其最大代谢值已经到了13.6,非常活跃。医生告诉肖院,肿瘤复发了。
肖院没有想到的是,化疗刚刚结束两个月,她去做基因检测,检查的报告显示,她的血液里发现了与原发肿瘤组织一致的基因突变信息,这意味着,肿瘤可能卷土重来了。肖院立即赶到医院做了PET-CT,检查结果显示,肖院升结肠旁的1.1厘米结节已经长到了3厘米,且其最大代谢值已经到了13.6,非常活跃。医生告诉肖院,肿瘤复发了。
因为这个增长的结节,肖院开始频繁地去看医生,北京、上海、香港,她和家人都去了,或者打印出病历让朋友带着去见医生。对于如何处理结节,医生们给出了各种各样的判断:有的医生认为应该继续化疗,毕竟肖院在治疗的过程中病程还在发展,贸然手术,很可能缩短生存期;有的则坚持手术,认为是孤立病灶,切干净可能对患者更好。这让肖院和家人难以抉择,她觉得自己拿到了许多把通往生存的钥匙,但每一把都不是确定的。
另一个让人丧气的事实是,肖院的肿瘤在化疗结束两个月左右复发,说明她是一个“铂耐药”患者,即她对化疗的药物不敏感。在妇科肿瘤中,卵巢癌的发病率虽然低于宫颈癌和子宫内膜癌,死亡率却是最高的。对于一个卵巢癌患者来讲,只有极少数患者在初次治疗后能够临床治愈,70%的患者在初次治疗后都会复发;而大多数复发性卵巢癌会再次复发,或多次复发,复发周期不断缩短,患者最终会在一次次化疗中耐药,最后无计可施。相比这些患者,肖院更不幸一些,因为耐药,她一开始就失去了与疾病相争的武器。
事实上,一直到2014年,包括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妇科主任刘继红在内的妇科肿瘤医生一直被卵巢癌的治疗所困扰。2018年,《柳叶刀》发表了一篇关于全球18种主要癌症生存趋势的监测报告。监测数据显示,2004~2014年的十年间,中国卵巢癌患者的总体5年生存率从2004年的42.4%降到41.8%。在调查涉及的18种主要癌症里,中国仅有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胰腺癌两种癌症与卵巢癌的情况类似。换句话说,在2014年以前,与其他癌症领域新药迭出相比,卵巢癌的发病机制和诊疗进展在这几十年间基本上是“原地踏步”。
与之相对的数据是,近30年来,中国的卵巢癌发病率一路飙升,2014年,中国卵巢癌的发病率,甚至超过了全球平均发病率,每年新发卵巢癌患者约5.21万例,死亡约2.25万例。“卵巢癌发病隐匿,且缺乏有效筛查手段,70%的患者就诊时已处于晚期。”刘继红今年59岁,已经在肿瘤医院工作了37年。她告诉本刊,很多来到她诊室的病人都觉得不解,说自己并没有什么症状,怎么就是癌症了呢?
“肿瘤细胞的数量要达到106才能形成一个肉眼可见的肿块,卵巢位于女性身体盆腔深处,并且体积很小,小的肿块很难发现。很多患者是因为腹胀去医院看消化内科才发现问题的,实际上这时候她很可能已经出现腹水或者肿瘤已经在腹中扩散,是晚期患者的症状。”刘继红说,尤其是高级别浆液性卵巢癌,发生突然,进展却很快。她曾遇到过一个案例,患者在三个月前因为身体不舒服到医院做B超,检查显示一点问题也没有,三个月后患者再来医院就被诊断为晚期卵巢癌。患者认为医生之前是漏诊,医生只好将三个月前的片子调出来。
2014年,卵巢癌的治疗方式依然局限于“手术+化疗”的传统治疗模式。刘继红经常被患者问到如下问题:“医生,我手术做完了,化疗也打完了,接下去应该怎么办?我要不要吃点什么药?”
“你要按时随诊。”刘继红会多次叮嘱患者。刘继红很难去告诉患者,大部分人要面对的现实其实是等待复发,她只能悄悄地告诉家属,复发的可能性很大。“那时,我们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只能给一些更晚期的患者,比如说癌症Ⅳ期的患者用上抑制肿瘤血管生长的药物贝伐单抗,可贝伐单抗的副作用也大。”
刘继红说,从2000年以后,医生们就在期待新的药物出现。刘继红记得当时有国外的药企在中国组织专家调研,组织有关卵巢癌药物的讨论,想看看做一款新药是否有使用前景,医生们都在表达一个新药物出现的急迫性和重要性。当时,为了尽量延长患者复发前的周期和总体生存期,医生们只能在原有的治疗方式上下功夫——晚期卵巢癌转移灶可覆盖全盆腔,甚至延续到上腹部,该情况下手术切除达到R0(切除后显微镜下无残留)很难。那么对于晚期卵巢癌患者,是先进行新辅助化疗还是直接进行手术?直到现在,越来越多的医生认为,对于Ⅲc期或IV期的晚期卵巢癌患者,无论是直接手术还是间歇性手术,达到R0才能使患者有更好的预后。
 倘若问妇科肿瘤医生,近30年来卵巢癌治疗领域最大的突破是什么,他们的回答一定是PARP抑制剂的出现。
倘若问妇科肿瘤医生,近30年来卵巢癌治疗领域最大的突破是什么,他们的回答一定是PARP抑制剂的出现。
2014年12月,PARP抑制剂奥拉帕利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以口服胶囊剂上市,临床用于铂敏感复发性BRCA突变卵巢癌成人患者的维持治疗。BRCA是一种抑癌基因,在调节细胞复制、DNA损伤修复、细胞正常生长方面有重要作用;如果BRCA基因突变,人体就丧失了抑制肿瘤发生的功能。流行病学显示,无BRCA基因突变的女性一生中患卵巢癌的概率为1%~2%,而有BRCA1基因突变的女性一生中的患癌风险可高达54%,有BRCA2基因突变的女性一生中的患癌风险也高达23%。像奥拉帕利这样的药物被统称为PARP抑制剂,对有BRCA基因突变的卵巢癌患者非常有效。
2017年3月12~15日,美国妇科肿瘤学会(SGO)年会公布了大型临床Ⅲ期SOLO2研究的数据。结果又证实,不仅针对BRCA基因突变患者,在铂类敏感的复发卵巢癌患者中,PARP抑制剂奥拉帕利单药维持治疗较安慰剂组显著改善患者无进展生存期(PFS)。在临床实践中,刘继红发现,对于前期使用PARP抑制剂作为初治维持治疗的卵巢癌晚期患者来讲,“比如一个Ⅲ期的卵巢癌患者,原本化疗结束后可能一到两年就复发了,但用PARP抑制剂维持治疗,可能3~4年都没有复发,或者就不复发了,即使复发了,在接受继续治疗后有很好的愈后效果。”
从全球PARP抑制剂的销售数据能够看出全世界对奥拉帕利这个药物的渴望。2015年奥拉帕利上市第一年的全球销售额达0.94亿美元,2016年增长为2.18亿美元,增长率高达131.91%。2017年全球PARP抑制剂的销售额为4.62亿美元,其中,仅奥拉帕利便贡献2.97亿美元。
2018年奥拉帕利在中国获批用于复发患者维持治疗。在此基础上,2019年国家药监局批准奥拉帕利用于BRCA突变的晚期卵巢癌患者的一线治疗。奥拉帕利在中国大陆上市之前,刘继红经常会推荐有经济条件的患者去香港或者澳门买药。“在奥拉帕利进入医保之前,患者用药的经济压力很大。”刘继红说,对于一些患者,当时最好的办法是推荐他们进入药物临床试验组。一位患者家属告诉本刊,奥拉帕利刚上市时,国内价格是一盒2.5万元,一个月要吃两盒,费用就是5万元。后来,奥拉帕利有慈善赠药活动,买2盒送2盒,能帮助病人减少一半的费用。但是病人吃一年奥拉帕利依然要承担30万元,“因为吃不起正版药,许多人就只能通过其他途径购买原研药”。
那时,原华西医科大学校长、中华医学会妇科肿瘤学分会主任委员曹泽毅经常会遇到患者因为吃不起药而无法达到就医效果的事情,他总是会给药企打电话,拜托对方给患者最大的优惠。“对一名医生来说,最无力的时刻,是看着患者得不到好的治疗。”曹泽毅说。有一年,他跟随中华医学会到甘肃下面的贫困区搞巡回医疗,有一位父亲带着自己20多岁的女儿找到他,对方说家里穷,女儿得了卵巢癌没钱治病,他问曹泽毅能否免除手术费用,曹泽毅向当地医院申请得到了批准。可对方又问他,手术之后是否就治好了?曹泽毅说还要化疗,还有后续的治疗。对方算了下费用,很快就说不治了。
从2018年开始,呼吁奥拉帕利进入医保成了医生和患者的共同目标。2019年11月28日,奥拉帕利被列入国家医保目录。根据协议,奥拉帕利医保后的价格是5700元/盒,每盒规格是150毫克×56片,一个月的费用是1.14万元,各地可以根据当地的医保报销比例进行报销。2020年,奥拉帕利医保适应症扩展至BRCA突变晚期卵巢癌的一线维持治疗。
肖院的初治手术是在2017年4月,当时距离奥拉帕利在中国上市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在做完手术后,她的医生也建议她去做BRCA基因检测。肖院的手术医生觉得,如果肖院有BRCA基因的改变,就可以进行相应的药物治疗。因为家里有亲戚曾经得过肠癌,肖院的父母在考虑后为她选择了全套基因检测,然而并没有发现她有BRCA基因的突变。肖院又是一个铂耐药患者,当时尚无临床试验证明PARP抑制剂对铂耐药患者有很好的作用。肖院去找医生,对方是全国最顶尖的专家,告诉她“没办法了”。肖院哭着从诊室里跑出来,沿着马路一路走一路哭,连车也不看,“我当时想着车撞死自己就好了”。去见医生之前,肖院曾上网搜了有关铂耐药患者的相关信息,她看到了许多终末期患者的照片,看着她们被肿瘤榨干的身体和被腹水撑得巨大的肚子,她恐惧自己也会是这样的结局。幸运的PD-1
如果让肖院列举5年治疗下来的幸运节点,其中一个一定是手术治疗后全基因检测项目的购买。
在肖院购买的项目检测里有肿瘤突变负荷(TMB)一项,这是衡量每百万碱基中被检测出的体细胞基因编码错误、碱基替换、基因插入或缺失错误的总数。这一项的检测结果显示,肖院的卵巢透明细胞癌属于dMMR/MSI-H(微卫星高度不稳定),而且TMB分别为20个突变/Mb和28.9个突变/Mb。“那时基因检测刚刚兴起,人们对全基因检测的概念就更加陌生了。”肖院说报告出来后,她曾拿给医生看,但当时医生们对TMB都不了解,所以这份报告就被家人收了起来。
再次想起这份报告是在被医生告知“没有办法”之后。为了找到生存机会,肖院开始学习有关卵巢癌的知识,她查阅各种相关文献,也加入了不少患者/家属群。其中一个群的群主邓永已经自学卵巢癌知识8年,他的母亲2010年被诊断为卵巢癌,他经常去查看最前沿的医学进展。邓永告诉肖院,根据她的基因检测报告,也许PD-1抑制剂会对她有效果。
PD-1是人类正常细胞表面的一种蛋白,其功能是和免疫细胞表面的PD-L1结合、阻止免疫细胞活化杀伤正常细胞,是人类组织自我保护的手段之一。PD-1抑制剂的作用就是通过打断PD-1/PD-L1信号通路,恢复细胞的抗肿瘤活性,进一步杀伤肿瘤细胞。从2014年9月以来,PD-1抑制剂相继被美国FDA正式批准用于恶性黑色素瘤、非小细胞肺癌、肝癌、胃癌、肾癌、膀胱癌、头颈部肿瘤、霍奇金淋巴瘤、宫颈癌、Merkel细胞癌,以及所有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SI-H)的实体瘤。肖院正属于微卫星高度不稳定的患者。
燃起希望的肖院拿着基因检测报告去找一位卵巢癌领域的权威医生询问,对方将她的报告放在一边,告诉她“PD-1在卵巢癌里不适用”。现在回想起来,肖院觉得也能理解医生当时的判断。一直到2018年,关于卵巢癌使用PD-1抑制剂的临床数据都很少,仅有的几个也是不好的结果。比如说2015年,一项20例铂类耐药卵巢癌患者的研究中,PD-1抑制剂欧狄沃等在治疗卵巢癌时的治疗反应率为15%,治疗结果与PD-L1阳性或阴性没有关联。2018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会上发表的Dana-Farber癌症研究所KEYNOTE-100试验,PD-1抑制剂Keytuda在治疗铂敏感复发性卵巢癌患者上客观反应率为8%。一个可以比对的数据是,在传统的化疗药物治疗上,铂敏感复发性卵巢癌客观缓解率约为30%~79%;治疗铂耐药复发性卵巢癌客观缓解率为20%左右。PD-1单药治疗并未表现出优于传统化疗的优势。
美国安德森癌症中心一位教授的在线诊疗给了肖院尝试的决心。对方认为,从临床研究来看,PD-1虽然在试验人群中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效果,但确实显示出对个别患者有效,肖院的基因突变类型也是适用的。“当时医生都已经给我开了手术单,在等床位了,但家人坐在一起商议之后,还是决定使用PD-1。”肖院说,家人立刻做了分工,去香港买药。肖院所用的药物全部是家人去香港背回来的。PD-1须恒温保存,不能剧烈晃动,否则可能导致药品变质,家人就买了个药品保温箱,将药物紧紧抱在怀里。“我们买的Keytruda,当时3.18万港元一支,一支只有100毫升,像抱了黄金一样。”肖院说过安检时,家人担心安检机器会影响药品的效用,每次都是拿出医生的处方证明跟工作人员商量,能不能不过安检。
肖院则留在上海负责寻找可以给患者使用PD-1的医生——2018年下半年,PD-1抑制剂Opdivo和Keytuda才在中国上市。因为PD-1抑制剂有很强的副作用,可能会引发免疫性肺炎、免疫性心肌炎、肾炎等,在上市之前,国内很少有医生敢给患者用药。在患者群里,肖院得到了一个医生目录,上面是病友和家属总结的可以给患者使用PD-1的医生名单,肖院记得在上海的医生有两位。她去找了其中一位,是肠胃科的医生。“我不敢打了,前段时间有个患者用PD-1副作用很大,医院处分了我。”对方又给肖院推荐了一个人。
2018年1月2日,肖院终于用上了PD-1,40多个小时后,她开始低烧。她很忐忑,不知道是药物在起作用还是副作用或者是疾病本身的进展。直到复查的前一天,她还梦见一股像死神般的巫邪力量来到床边,自己被那强大的力量罩住,动弹不得,呼吸急促,脸涨得难受。好在,复查的CT显示,她的升结肠位置的病灶减小到1.6厘米。一瞬间,肖院觉得自己像溺水的人终于抓住湍流中的浮木。在持续用药1年零4个月之后,医生认为肖院的病症已经完全缓解。规范治疗
一直到现在,肖院都认为患者群的帮助在自己治疗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比如说,关于PD-1的停药问题,因为是新药,现在还没有明确的规范。在肿瘤完全缓解后,肖院曾去询问医生什么时候可以停药,她问了国内两家权威医院的妇瘤科医生,一个说可以即刻停药,一个则说要终身用药。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让肖院有些不知所措,她最后只好参照病友的经验,在完全缓解后又用了一段时间药,然后停用。“其实有时候患者和家属在某些方面的知识会比医生多一些,或者是医生出于谨慎考虑很少会让患者做冒险性尝试,但对患者和家属来说,每一次尝试都是一个得以生存的机会。”肖院告诉本刊。
正是维持生命的想法驱动着许多患者去主动学习卵巢癌的相关知识。肖院所在的群,其中一个是由邓永建立的。邓永告诉本刊,母亲确诊卵巢癌后,他也曾恐惧、迷茫、崩溃,觉得一切都暗淡无光。他起初去学相关的知识只是希望能够理解一些专业的词语,能跟医生交流,帮助母亲的治疗。但随着与医生、患者、患者家属交流的增多,他发现,对于卵巢癌患者家属来讲,学习能够帮助患者规避很多治疗的误区。
对于初治的卵巢癌患者,“紫杉醇+卡铂”的方案是卵巢癌初治的一线方案,但现在很多患者都得不到规范的治疗。邓永曾经遇到一名患者,在手术化疗时医生不仅没有给她使用一线方案,而且在使用铂类药物时,剂量也不够,也没有完成指南规定的6个疗程,患者很快复发,接受了第二次手术,可手术并没有实现R0。“复发性卵巢癌要谨慎手术,如果不能实现R0,不仅无法延长生命,还会缩短生存期。”邓永说。“国内的肿瘤专科医生制度不健全,许多治疗妇科肿瘤的医生并不是专科医生,而是来自于妇产科,他们接受的培训不够,经常会开出五花八门的化疗用药。”一位医生告诉本刊,有的患者在第一次化疗疗程里,就使用了多种不同的铂类药物。
曹泽毅从2000年初就开始呼吁国内妇科肿瘤医生制度的建设,建立一支高素质、高质量、高水平的妇科肿瘤医生队伍。“妇科肿瘤不仅跟妇产科有关,还涉及很多其他学科,如普通外科、泌尿科、病理科等。妇科肿瘤医生必须掌握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操作,这样才能在诊疗过程中,抓住最佳时机为患者争取时间。”曹泽毅告诉本刊,欧美各国早就建立了相应的培训制度,“国外有一套专门培训妇科肿瘤医生的制度,一般妇产科大夫要成为妇科肿瘤专科医生,要再接受两三年的培训,他们不仅有妇产科的基础,还要学习普通外科的知识、病理学、化疗药物的应用、解剖学、流行病学,制度同时规定要操作多少台手术,经过学会考试合格后才行。”曹泽毅说,在国外只有经过妇科肿瘤培训的医生才能做妇科肿瘤的手术,否则就是违法的。
曹泽毅去年遇到一个案例,有一个自称女儿是卵巢癌晚期的患者家属向他求救,希望他能够救救她的女儿。曹泽毅见到患者时,对方躺在病床上,面无血色,四肢骨瘦如柴,腹部顶着一个巨大的肿瘤,整个人就快被肿瘤“吸干了”。曹泽毅给对方做了检查,他当时就判断这个巨大肿瘤或许并非恶性晚期,后续的检查证明了他的判断。可惜的是,这个患者已经被当作卵巢癌治疗了一段时间,尤其是腹部的肿瘤,在多家医疗机构进行过多次穿刺引流,导致多器官粘连,严重增加了手术难度。“卵巢囊肿不能盲目穿刺,这是写在指南里的,即使穿刺,也不能碰到肿瘤,否则如果囊肿是恶性的,造成的后果就是肿瘤的扩散。”
如果去看女性盆腔的解剖图,会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妇科肿瘤的复杂性。盆腔里面很拥挤,神经像一棵大树分出的纵横交错的枝杈,有的支配膀胱,有的支配子宫。盆腔里有数个潜在间隙和结缔组织层,它们使得泌尿、生殖、胃肠道等系统互相独立发挥作用。子宫在盆腔的中部,两个卵巢和输卵管位于子宫的两侧,除此之外,还有输尿管、膀胱、直肠,彼此之间的距离非常近。以宫颈癌为例,如果宫颈位置发生癌变,向下很容易侵犯阴道,向上又很容易侵犯子宫、输卵管,最后沿着淋巴转移到人体的各个器官。
北京协和医院妇科肿瘤中心副主任医师谭先杰告诉本刊,2007年左右,为了提升患者的生存质量,科室里的医生在做妇科肿瘤手术时开始注重保留患者的相应的神经,仅这一个变化,科室就组织各种解剖知识的培训,大医生带头在手术台上做,小医生就在旁边看。谭先杰那时已经是主治医生,他是在学习了四五年后才开始做保留神经的手术的。谭先杰告诉本刊,他记得当时科室的主任郎景和经常念叨一句话:“只有心中有神经,眼里才有神经,手下才有神经;心里没有神经的话,脑袋里面就没有神经,你怎么可能去保护它呢?”“对于医学来讲,外人看来一个小小手术细节的变化,其实是医生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磨练和积累以及理念的变化才实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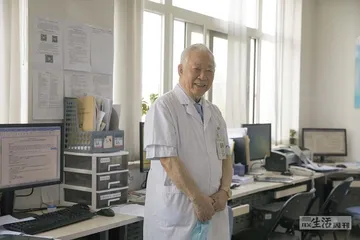 自1956年从医以来,原华西医科大学校长、中华医学会妇科肿瘤学分会主任委员曹泽毅觉得,面对妇科肿瘤,医生手中的武器增加了。
自1956年从医以来,原华西医科大学校长、中华医学会妇科肿瘤学分会主任委员曹泽毅觉得,面对妇科肿瘤,医生手中的武器增加了。
曹泽毅提到他在上世纪90年代治疗过的一名患者,对方是一个13岁的女孩,被诊断为内胚窦瘤,卵巢癌的一种。曹泽毅给她做了手术,切掉了肿瘤,但很快肿瘤重新长了出来,曹泽毅又给她做了手术,后来肿瘤又复发了,转移到淋巴、肺、肝。曹泽毅查阅了很多文献和国外的一些资料,那时对于这种肿瘤,除了手术以外,没有其他好的治疗方法。在这个女孩去世几年后,一种新的化疗方法出现了,可以配合手术很好地解决内胚窦瘤复发的问题。后来,在自己有关妇科肿瘤的著作上,曹泽毅特意对这个肿瘤的治疗方法做了标记,他希望其他的患者能够受益于医学的进步。
而另一方面的现实是妇科肿瘤患者的增多。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及卵巢癌,一起被称为妇科三大恶性肿瘤。研究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15年,我国宫颈癌的发病率每年都在以10%的幅度增加。全国肿瘤登记中心相关统计显示,我国卵巢癌的发病率也在不断增长。北京协和医院妇科肿瘤中心有90多张床位,面对需要住院手术的病情较轻的良性肿瘤患者,主任医师向阳也只能告诉患者,“如果是外地的,建议回去手术,如果是北京的,也建议去其他医院,不然手术排期要等上三个月”。
每次看完门诊,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谭先杰都会将需要手术的患者按照病情的严重程度排序,向医院提交手术申请。面对向他请求早点入院的患者,他经常会打一个比方:“我就像个飞行员,你来找我看病,就像买某个航空公司的票,登上了飞往协和医院的飞机。作为飞行员,我特别想跟你一起飞,可我在机场排队的时候,不是说我想飞就能飞,我必须要遵守医院的流程,飞机晚点的话,我也得根据要求排队。作为医生,我们不能保证治好每一个病人,但我会保证好好地治疗每一个病人。”
即使已经到了90岁,曹泽毅还在学习关于妇科肿瘤的知识。几年前,他在美国时看到一本杂志,上面收集整理了内科、外科、妇科、肿瘤科等最新的发现和报告,他觉得非常好。因为订阅有地区限制,他就通过熟人帮他订阅了杂志。“医学是在不断发展进步的,医生也要不断学习,保持一直学习的态度才能接近更前沿的知识,给患者更好的诊疗。”在曹泽毅的眼中,妇科肿瘤的治疗方式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尤其是卵巢癌,从过去“手术+化疗”的传统模式进入到“减瘤术+含铂化疗+PARP抑制剂维持治疗”的模式。
已经90岁的曹泽毅身体看起来很硬朗,他现在依然会出门诊、做手术。每天只要在医院,他都要去病房看病人。“对于病人来讲,每天看到医生她们会觉得安心一些。”在曹泽毅的病人里,有许多是晚期患者。每当病人问到自己的生存期,曹泽毅很少说“可能只有几个月了”“你现在治疗已经晚了”这样的话,他会认真地看着患者说:“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像你这种情况70%~80%治疗起来都很困难,但在我的经验里,有20%~30%的人接受治疗后是可以活下去的,你为什么不争取到20%~30%里头去?我给你一个适当的治疗,你跟我好好配合,比如说给你必要的治疗你都接受,我要求你好好休息,好好吃有营养的东西。我们有一个很阳光、自信的心态,这样的话,你就可能进到那20%的人群里去。”
从医60年,曹泽毅见过各种各样的患者,也在这个过程中,他愈发觉得医生能力的有限性和医学的不确定性——同样是两个癌症病人,几乎同时接受检查和治疗,但两个病人对治疗的反应不一样,治疗的结果也不一样。“有的人身体还可以,可思想压力很大,生活习惯也不好,免疫力不断下降;另一位可能刚检查出来的情况不太好,但他心态好、习惯好,配合医生的治疗,所以生命维持时间长,甚至可以好转。”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曹泽毅慢慢感受到自我角色的转变。“年轻的医生容易把患者当成治疗对象,一切是我做主,病人是听我摆布的。但随着经验的积累,他会发现单纯的治疗并不一定起到好的结果。积累越多,就会对疾病越敬畏。”曹泽毅说,他后来明白,对于一个患者来讲,自我免疫功能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存活下去的最强大武器,吃药、做手术、放化疗,都是从旁边来给患者的免疫功能一点帮助,最后还得靠免疫功能来恢复自己。“作为一个医生你必须了解这一点,你只是对病有帮助的,你不是万能的。我希望我的患者始终能有希望,他们是我治疗时的伙伴,然后我尽力帮助他们。我有几个Ⅳ期癌症的患者,患病四五年,现在状态都还不错。”
在采访中,曹泽毅几次提到了加拿大医生爱德华·特鲁多的一句话:有时是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在安慰。在不断发展的医学知识面前,这可能是一名医生承担最多的角色。
(肖院为化名,感谢曹泽毅教授以及《时间的礼物》作者邓永对本文的帮助) 放化疗癌症复发pd-1妇科肿瘤刘继红癌症肿瘤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化疗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