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是我们自身内部的电影院
作者:帼杰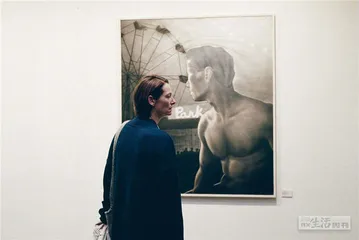 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是泰国第一位获得金棕榈的电影导演,也是亚洲最重要的独立导演之一。在《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捧回金棕榈大奖后,时隔11年,阿彼察邦带新作《记忆》重回主竞赛单元,最终获得评审团奖。
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是泰国第一位获得金棕榈的电影导演,也是亚洲最重要的独立导演之一。在《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捧回金棕榈大奖后,时隔11年,阿彼察邦带新作《记忆》重回主竞赛单元,最终获得评审团奖。
《记忆》是阿彼察邦的第一部外语对白影片,也是第一次在本土之外拍摄。同时因为贾樟柯担任联合监制,以及奥斯卡金像奖得主、“古一法师”蒂尔达·斯文顿的加入,本片在华语影迷中也颇受关注。
从《热带疾病》到《幻梦墓园》,阿彼察邦的电影永远是关于梦境和记忆的。这一次,“记忆”甚至直白地成为影片片名。杰西卡(蒂尔达·斯文顿饰)是一位移居哥伦比亚的花农,她在波哥大探望生病住院的姐姐,可她自己却被脑海里一种巨大的“砰”声困扰至失眠。这个声音显然只有她自己听得到,于是她游走于哥伦比亚的城市和丛林,试图理解这神秘噪声从何而来。游走中,个体记忆与这片土地的记忆、与自然甚至地球的记忆慢慢交融,最终顺着记忆,杰西卡看到了那出人意料的起源。
阿彼察邦第一次与国际班底合作,幸运的是这并没有影响他独特的电影魅力,那些摒弃传统叙事、在现实与超现实之间游走的镜头画面,依然充满让人沉思的灵性。长镜头,而且是长而静止的镜头,阿彼察邦可以让蒂尔达·斯文顿在单人床上完完整整小憩一觉,银幕前的观众如果愿意,也可以跟着打个盹,醒来会些微恍惚:镜头移动过了吗?我是否错过了什么?
这种恍恍惚惚类似催眠的体验,是阿彼察邦电影最“难熬”也最“迷人”之处。催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唤醒”,阿彼察邦用温柔又冷静的现实主义电影语言模糊了时间与空间、历史与当下的界限,让人相信生者与死者、清醒与梦境、人类与他者可以共存,给观众创造似梦非梦的体验,然后唤醒他们心底的思考,去审视内里,追问来时与去处。
本刊特约撰稿人在影片世界首映后面对面采访了阿彼察邦导演,和他一起回溯了这次创作的“前世今生”。
 三联生活周刊:这是你第一次离开泰国在国外拍摄,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
三联生活周刊:这是你第一次离开泰国在国外拍摄,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
阿彼察邦:我觉得是因为我感受到了身体的沉重,我变老了。我在泰国的家里太舒服了,同时我也不能做很多事情,来反映这个被军队占领的国家的现实。2017年我有机会去哥伦比亚,在各地旅行,那里的人们很愿意讲述他们的故事。我想我找到了我们的位置,是的,哥伦比亚是一个与回忆产生共鸣的地方,同时这里还存在着一些我们不了解的东西。我们不再年轻了,需要找到一个地方来激活我们的存在感。
重要的是,我认为哥伦比亚人正视他们的记忆。我在那里看了展览,有很多这个国家关于对抗、死亡和暴力的历史,而且这些统计数据在泰国是没有的。我真的很欣赏这些,也想了解这种紧张、焦虑。当然,这部电影并不完全是关于这一点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电影里的语言从泰语变成了西班牙语,这会影响到你的创作吗?
阿彼察邦:我在语言方面有很大的问题,因此我很沮丧。比如选角阶段,我说某个演员对我来说真的很自然,我喜欢这个,但当地选角导演说:“不,那真的是肥皂剧式的台词。”又比如我和我的日本朋友说我喜欢小津安二郎电影的节奏和语言,但我的日本朋友说:“不,小津的电影真的很生硬。”这些语言上的不自然我不能领会,这是一种我无法理解的东西,所以我放弃了。我只会专注于电影中的节奏和沉默以及停顿。哥伦比亚的西班牙语语速非常快,我会说,慢一点,慢到一般的学生水平。
三联生活周刊:能不能谈谈电影中对声音的设计,它们让人印象非常深刻。
阿彼察邦:这部电影是关于记忆的,我们谈论记忆时,谈论的常常是影像,有时会忽略声音。对我来说,从我的电影制作生涯开始,我就一直很重视声音。对于这部电影来说,是一次声音素材库的极致积累。在影片中,录音师和杰西卡试图去好莱坞的声音素材库找到一个声音,但其实我们也有自己的声音素材库,并把这些年来自己收集的声音素材放到了影片不同的部分中。这是我们之间的密码,也是人性的声音。如果你仔细听,影片最后有一个声音,那是我们人类录制的第一个声音,来自法国香颂(chanson),是有记录以来的最古老的声音。它是关于这种集体记忆和个人记忆的结合。
三联生活周刊:杰西卡脑海中的爆炸声又是怎么来的?
阿彼察邦:哦,这个是真的。这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人们称为“爆炸头综合征”(患者常常在午夜时听到爆炸般的巨响,但对于其他人却并未听到如此强度的声音)。我和我的声音设计师一起尝试建立这个场景,我试着向他解释,但解释它是非常令人沮丧的过程,因为它不是真正的声音,就像杰西卡在影片中努力挣扎着尝试表达清楚——这里的声音应该听起来像金属和回声。对我来说,电影本身就是表现出这种沮丧,并试图传达一些无法用语言说出的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音效之外,电影里还有两首音乐,它们太美了。你选择它们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是谁创作了这些音乐,或者为什么选择它们?
阿彼察邦:这两首音乐是波哥大音乐人制作的。第一处的钢琴曲是我和音乐人一起工作的结果,我只是跟他描述我要的感受。第二个很有趣,是我在取景的时候,在大学里散步,走到影片场景的那个房间,一些人正在排练,我就拍了30秒的视频。然后,当我们设计拍摄时,就说也许可以把我当时的体验放进去。我们找不到这个音乐家,所以我们只能有个参考,但是波哥大音乐人在此基础上的重新创作效果并不好,最后我们只保留了这个音乐的精神内核,它其实是一首不同的新的音乐了。这两首音乐创作了几个月的时间,我真的很注重声音的细节,而我们的音乐人真的很有耐心。
三联生活周刊:在当代电影中,99%的电影都要剪辑。对你来说,你在拍摄中怎么判断这个镜头可以结束了,又怎样处理你的长镜头和剪辑的平衡?
阿彼察邦:这真是个有趣的问题,我也真的无法回答,因为对我来说,这就是电影制作的美妙之处。电影不像戏剧,我拍了很多很多镜头,然后像听一个人的心跳一样听这些镜头的节奏。我和我的剪辑师花了很长时间听这个,并试图找到一种生命规律。但是很难说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剪辑,是电影自己告诉我们(该这样剪辑),然后声音设计师把声音放进去,它就成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做了很多工作来支持和培养你自己国家的新电影人,并在给年轻人的忠告里强调冥想的重要性。所以冥想是你创作工作流程的一部分吗?它给你带来了什么?
阿彼察邦:对我来说,冥想就像锻炼一样让我平静下来,尤其是在我有太多想法的时候。我失眠是因为我的大脑太疯狂了,冥想对我有很大帮助。所以我总是告诉年轻的电影制作人大口呼吸、脚踏实地和活在当下。我也尝试将这个想法引入电影中,让观众能够欣赏屏幕上的幻觉。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你会失眠,那么在你真正睡着的时候会做很多梦吗?因为你的电影总是与梦境有关。
阿彼察邦:是的,很多。我记下了这些梦,有时还录了下来,我认为分享梦的体验,其实就像一个电影院,梦是我们自身内部的电影院,这种感觉太神奇了。当我们做梦时,对内容的真实性没有质疑,但当我们醒来时,当我们想到它时,就觉得很奇怪。这就像电影一样。所以人类和电影之间的关系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充满激情的话题。
三联生活周刊:影片里我们不仅感受到个体的记忆,还有自然的记忆,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阿彼察邦:不仅是自然,还有我们在不同国家(的记忆),如果我们倾听,就会明白记忆不仅仅是属于一个人的,人类是有全球记忆的。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一点,就会理解宇宙的脆弱性,这样我们就会互相照顾。我们会更好地爱护环境。而灾难,我们不需要灾难来提醒自己,我们必须在灾难之前先保护好地球。
三联生活周刊:贾樟柯导演是这部影片的联合监制,能不能谈一谈和他合作的经历?
阿彼察邦:和他的合作对我来说是一种幸运,因为我们很早以前就知道彼此,都很尊重彼此的工作。他实际上从五六年前就想给我们提供帮助,然后就顺理成章加入现在这个项目。他并不是一个强加想法给别人的人,像这部电影里的其他制片人一样。即使是后期制作剪辑,我们也有完全的创作自由。我真的很荣幸能与这个团队一起工作。
三联生活周刊:你影片里有个镜头让人很容易想到贾樟柯的电影。
阿彼察邦:啊我知道你想要说什么,但请不要跟大家剧透,这是一个美丽的秘密。 记忆音乐电影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