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剑》:觉醒的寓言
作者:张杭 《大剑》是我看的次数最多,也无数次安利给朋友的作品,终于有机会写一写。需要说明的是,《大剑》漫画也曾动画化,但只出了一季26集,止于漫画全篇大概五分之一、第一个高潮“北之战”结束处,又加了一个动画版自行设计的结尾草草收场,断了后路。虽然动漫爱好者中总有漫画党和动画党之争,但对于《大剑》,我只推荐漫画。觉醒,一个存在主义的主题
《大剑》是我看的次数最多,也无数次安利给朋友的作品,终于有机会写一写。需要说明的是,《大剑》漫画也曾动画化,但只出了一季26集,止于漫画全篇大概五分之一、第一个高潮“北之战”结束处,又加了一个动画版自行设计的结尾草草收场,断了后路。虽然动漫爱好者中总有漫画党和动画党之争,但对于《大剑》,我只推荐漫画。觉醒,一个存在主义的主题
有一种看法,认为八木教广创作于2000年后的《大剑》,与三浦健太郎自90年代作画的《剑风传奇》有某种渊源:《大剑》的故事发生在一片虚构的大陆,而剧情中暗示这个大陆只是一个岛屿,星球上还有更大的大陆,就是《剑风传奇》的故事发生地。无论这一点能否证实,两部漫画都有不少相似的元素,中世纪的环境氛围、魔物的存在、《剑风传奇》的主人公格斯使用的巨剑与《大剑》中的武器“大剑”、不断出现的砍杀动作及身体切割造成的残忍风格。而从上述诸多设定来看,近年风靡的《进击的巨人》也可加入这一类序列。
要描述它们的差异,则需要提到动漫史上的分水岭之作《EVA新世纪福音战士》。我无法确切追溯脉络,但有两点我认为是《EVA》带来的广泛影响:一是对精神分析的引用,并专注于青春期成长的心理空间;另一则是在机战类动漫中,将人形作战机体设定为生物体,而对作战机体的操作不需要什么技术,需要的是操作者与生物体建立精神联结。尽管《圣斗士星矢》以来的日本战斗动漫中,精神力量一直是制胜因素,但到了《EVA》,物质性的武功被全然取消了,战斗即是精神战斗。这或许是日本动漫彻底摆脱曾经的美国雇主影响的结果,不免让人想到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基督教的修行不涉及身体,而身体修炼却是东方宗教的普遍逻辑。
而《大剑》的架构充斥精神分析的资源,并且布满了成长的精神过程的对应性。在一个孤立大陆上,有妖魔,有被平民唤为“银眼魔女”的大剑,有被称为“组织”的机构。组织把孤儿们培养成大剑,也靠大剑斩杀妖魔收取各城镇的佣金,成为大陆的实际控制者。这一关于身体规训与反抗的寓言,靠无数精妙的细节撑起:大剑从小被组织在身体里植入妖魔的血肉,有超出常人的力量,使用一柄长剑。但她们必须保持平和的心智,预防觉醒。觉醒就是超过某种身体的极限,兴奋、疲劳、痛苦,都会至此。引起觉醒的物质基础是她们体内的妖,越过界限,会感到彻底的“解放”,也就站到了妖的一边。这是一个悖论,大剑靠妖的力量战斗,但又必须学会控制。
大剑的觉醒,像极了性的机制。另一个引人联想的征象是,大剑只有初代是男性,此后皆是女性,因为男性大剑一旦动用妖力,马上觉醒,就像男性的性冲动一经发起不可逆转。大剑对觉醒的恐惧与压抑,也很像人在青春发育时那种斗争似的场面,在这一点上与《EVA》有着相似的主题。但更进一步的是,不像《EVA》那样,搬用精神分析的描绘仅限于私人关系,如父子、初恋,与其宏大世界观割裂为两部分;《大剑》将社会因素整体构建在一套能指设定中,就好像与自我矛盾进行斗争的少年,又必须面对他同时感受到的社会虚伪及强制力。不可觉醒与不可杀人等条款构成组织对大剑的戒律体系,没有一条在现实中是绝对的,尤以觉醒为难以避免。但组织以行动将戒律绝对化,濒临觉醒或违反戒律者,被组织派来的其他大剑所剪除。由此,理念与现实(身体)的矛盾,不但没有被意识为荒诞,反而内化成为大剑们的恐惧。这是组织的生命政治。
《大剑》发明了属于自身想象世界的专有名词“觉醒”,作为词语本义的“觉醒”也成为该部作品的关键词。在《大剑》中,由次主角米莉亚承担的这条线索,就像《进击的巨人》中调查军团的认知进路,再现柏拉图的洞穴比喻。当米莉亚和伙伴们发现,妖魔也是被组织改造的人,一系列诸如斩杀妖魔与“不可杀人”的矛盾,就骤然显现为荒诞。觉醒,即发现荒诞,是存在主义典型的戏剧动作。而米莉亚们在新获得的认知视角下,越界成为妖的觉醒者,他们不再是地狱恶魔般的存在,他们甚至是忠实于自身欲念的“理想的人”。但米莉亚们选择保守人的形态(就像培尔·金特的选择那样),没有一刻脱离与自身的斗争。从而对于“如何活”这一加缪式问题,做出了回答。不断累加的女性团结?
《大剑》的绘画,至少创造了某种极致景观。这一情形并不来自人物造型的特异,相反,大剑的人物造型十分克制,对于身体比例只是适度“理想化”,其景观在于以质素的风格创造女性群像。
大剑们身着的甲胄,或许可以从圣斗士的圣衣那里找到出处,但不像圣衣各具形态。大剑们的甲胄完全一样,从身形区分角色是困难的,只靠脸形、五官、发型等标识个性差异。整齐划一的武器“大剑”,加重了这一奇观效果,成为抹除个性的象征。此一形象设定,确切传达了身体规训的批判性主题,但同时也散发着规训式审美的诱惑。
表面整饬的形式美感并非诱惑的关键所在,而是某种制式形态对个体丰富性的压制与摧毁,预兆性地带来悲剧审美。那么这一审美体验的获取者是谁?《大剑》看似是一部女性向漫画,是这样吗?它的拥趸中女性较多还是男性较多?或可以更直白地设问,是谁热衷看女性的战斗?
大剑与圣斗士形象上的联系或许不是完全偶然。我仍记得一个童年经验带来的提示。圣斗士角色大都是男性,但在我六七岁间,《圣斗士》引进中国播出前,我曾在一则电视预告中,见到众多秀美身体穿着金属光泽的铠甲,我的第一印象是,“他们”是女性。这则预告给我带来的兴奋,一直伴随其后数年的追番经历。后来我多次从那些现代身体约束性服饰上想到圣衣,诸如丝袜、靴子、高跟凉鞋、西装,它们的目的不是完全遮住身体,而是使人取得身体被改变为物的倏忽印象,又能很快从中辨认出人。这些服饰的功能是将人推向社交性,因为社交既包含认同,也包含对他者的象征性占有、操控与毁坏。而动漫可以最大限度地承载这样一种社交想象,从几何中创造人的能指,并轻易地加以操演或摧毁。反复出现的各色战斗机具与铠甲,几乎就是一种典型符号。
在那个创造经典性的动漫时代,某些男性视角不应被忽视。《EVA》第一集中那个标志性镜头,主人公真嗣看到用医疗床推出、裹覆绷带的绫波零,被激起同情和勇气。绫波零的短发造型显得中性,作为人造人的绫波零保持被动的、缺乏感情的姿势与反应,映衬了男性少年纯真欲望受阻的境况。绫波零的形象被反复借鉴,10年后的《交响诗篇》中,女主角优莱卡来自珊瑚的非人类身世和短发造型仍然沿袭绫波零,在不断讲述的少年成长经验中,女性的物化形象变得难以改变。
端详《大剑》主角克蕾雅的形象,似乎还能看到一袭绫波零的影子。漫画中克蕾雅自相纠结的两条线索贯穿了全篇叙事:寻找与之分别的男主拉基,向杀死迪妮莎的觉醒者普莉西亚复仇。克蕾雅对拉基的执着,可看作男性欲望的反向映射。克蕾雅真的把对拉基的感情视作两性之爱吗?她可能只是把拉基看作幼年的自己,而将自身投射为她曾追随的最强的大剑迪妮莎。迪妮莎的肉体已埋入克蕾雅的身体,被纳入自我者才是完美伴侣。漫画中出场时间不长的迪妮莎,兼具美与力量,完美而自足,是女性集体中神一样的存在。众多角色分享从迪妮莎分化的精神实体性,如帮助或影响过克蕾雅的伊蕾娜、珍、奥菲莉亚、拉花娜,米莉亚团队的同伴和倒戈的新一代战士们。不断累加的女性团结,使男性视角中可毁坏的女性画像最终消融,生长出有生命力的主体,构成对某种预设的反转。
仅从性别视角和审美选择来看,漫画作为通俗作品与社会结构有着暧昧关系,一定时代的风潮会被顺应,也会被悄然僭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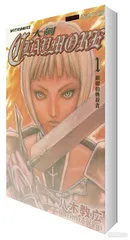 作者:[日]八木教广
作者:[日]八木教广
出版社: 文化传信有限公司
出版年:2001 大剑剑风传奇迪妮莎漫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