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的代价:“二次疫情”中的印度
作者:刘怡 时隔将近7个月,阿尼尔·赫巴尔(Anil Hebbar)终于从医生口中得知,在2020年10月的那次阿斯利康疫苗接种试验中,他本人被注射的是真正的腺病毒载体疫苗而不是安慰剂:“疫苗没能让我避免感染新型变异毒株。今年2月,我还是在方舱病房里待了两个星期。但当时的感染症状是可控的,我想这和疫苗的作用有关。像我这样一个56岁的糖尿病患者,能病愈出院完全是由于疫苗的功效。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更多人。”
时隔将近7个月,阿尼尔·赫巴尔(Anil Hebbar)终于从医生口中得知,在2020年10月的那次阿斯利康疫苗接种试验中,他本人被注射的是真正的腺病毒载体疫苗而不是安慰剂:“疫苗没能让我避免感染新型变异毒株。今年2月,我还是在方舱病房里待了两个星期。但当时的感染症状是可控的,我想这和疫苗的作用有关。像我这样一个56岁的糖尿病患者,能病愈出院完全是由于疫苗的功效。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更多人。”
魁梧、健谈、留着醒目的八字胡:当赫巴尔作为嘉宾接受自媒体视频节目《新印度连接点》(New India Junction)的采访时,特地换上了一身新西服,显得神采奕奕。“但我内心的真实感受要悲伤得多。有一段时间我甚至不敢点开朋友们的Facebook页面,生怕传来的就是噩耗。”他在邮件访谈中告诉本刊。
新冠肺炎“大流行”开始前,赫巴尔在孟买经营着一家小小的医疗器材公司。2020年夏天,在得知著名的贫民窟社区达拉维(Dharavi)由于防疫封锁正在陷入食品危机时,他加入了一个由本地中小企业家组织的志愿者团队,每天开车为贫民窟住户运送粮食和燃气罐。“但我觉得这还不够。作为曾经的医学院学生,我还可以为抗疫贡献更多。”赫巴尔告诉本刊。去年10月,当一位多年好友不幸感染新冠肺炎去世后,他走进了孟买帕雷尔街区的爱德华国王纪念医院,志愿参加牛津阿斯利康疫苗在印度的第一批临床接种试验。在访谈邮件中,赫巴尔表示:“在印度,医疗工作者需要对抗的不仅是病毒,还有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宗教观念造成的偏见。我的妻子是一位虔诚的印度教徒,她对一切牛血清(疫苗生产的关键辅料)制品都持抵制态度。参加试验之后的好几个月里,我一直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她。当她最终得知真相后,整整一天没有和我说一句话。”
 赫巴尔最终痊愈出院。但在拥有将近2000万人口(含卫星城)的孟买,像他这样的幸运儿只是极少数。事实上,当赫巴尔在4月第一周离开位于孟买金融城的方舱医院返回家中时,他意识到第二波疫情暴发已经开始了:“平时熙熙攘攘的街道上空无一人,只有救护车的警笛声在城市上空回荡。我所居住的高层社区里,九栋大楼被政府封闭了五栋。”根据印度医学研究委员会(ICMR)和各邦政府公布的数据,从2021年4月初开始,全印度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再度进入了暴发式增长状态,持续时长超过一个月,单日新增病例数由2月初的大约9000人一路飙升至40万人以上(5月第一周数据)。4月12日,印度正式超过巴西,成为全球确诊病例第二多的国家,仅次于美国。截止到6月第一周,ICMR公布的全印度累计确诊病例数已经接近2920万例,其中35.9万人病殁。而在4月28日之后的短短26天里,就有超过10万名患者去世,可谓触目惊心。
赫巴尔最终痊愈出院。但在拥有将近2000万人口(含卫星城)的孟买,像他这样的幸运儿只是极少数。事实上,当赫巴尔在4月第一周离开位于孟买金融城的方舱医院返回家中时,他意识到第二波疫情暴发已经开始了:“平时熙熙攘攘的街道上空无一人,只有救护车的警笛声在城市上空回荡。我所居住的高层社区里,九栋大楼被政府封闭了五栋。”根据印度医学研究委员会(ICMR)和各邦政府公布的数据,从2021年4月初开始,全印度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再度进入了暴发式增长状态,持续时长超过一个月,单日新增病例数由2月初的大约9000人一路飙升至40万人以上(5月第一周数据)。4月12日,印度正式超过巴西,成为全球确诊病例第二多的国家,仅次于美国。截止到6月第一周,ICMR公布的全印度累计确诊病例数已经接近2920万例,其中35.9万人病殁。而在4月28日之后的短短26天里,就有超过10万名患者去世,可谓触目惊心。
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东部,普利策奖得主杰弗里·格特尔曼(Jeffrey Gettleman)拍摄到了工作人员站在临时征用的板球场中,利用简陋的柴堆不分昼夜火化病患遗体的情景。病亡者数量的急剧增加(最多时日均接近4000人)使得原有的火化设备变得不敷使用,公园、球场甚至河畔都变成了集中焚尸点。经济条件稍微宽裕的中产阶级不惜花费每天100美元的高价租用救护车,载着病情严重的家人在孟买、德里、加尔各答等大城市周围的公路上穿梭,寻找每一家可能提供输氧服务或者空余床位的诊所,却每每一无所获。格特尔曼的一位颇有能量的朋友动用了全部社会关系试图找到一张空床位,最终却眼睁睁看着一名相识多年的晚辈倒在了家中。“到处都是一片混乱,再多的人脉也帮不到他,”这位大人物啜泣了起来,“这是一场灾难,是谋杀。”
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总理以及执政的印度人民党(BJP)再度成为众矢之的。今年2月,正是莫迪及其首席代言人、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Amit Shah)率先呼吁恢复街头政治集会,以为即将到来的西孟加拉邦议会选举造势。沙阿还鼓励民众踊跃参加12年一度的印度教大壶节(Kumbh Mela)庆典,这一举动最终导致了900万人次的集结和数万人确诊感染。人们现在正用选票宣泄自己的不满:5月2日,人民党在西孟加拉邦选举中以巨大劣势不敌全印草根大会党(AITC),在泰米尔纳德和喀拉拉邦也未能赢得执政权。尽管莫迪作为政府领导人的地位在短期内依旧足够稳固,但这位曾经的“印度推销员”的光环已经全然消散。
而被印度这波“二次疫情”影响的,还不止于这个国家的13.9亿人民。邻国尼泊尔和孟加拉国在今年4月先后确认发现了来自印度的变异毒株病例,并引发了新的医疗“挤兑”现象。印度在全球医药产业链尤其是疫苗生产环节上的重要地位,则意味着全世界范围内的疫苗接种将不得不大大延后,从而使更多易感染人群暴露在危险的境地中。这场“大流行”暴发已经1年又6个月,世界距离回归“正常”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仅仅5个月之前,“大流行”在印度死灰复燃看上去还是小概率事件。诚然,没有人会把疫情缓和的结果归功于人民党政府——自从2020年1月30日喀拉拉邦发现第一个本土确诊病例以来,莫迪内阁只是机械地公布了一连串的“封城令”和社交隔离规则,却没有在强化医疗系统方面投入多少资源,对卫生条件落后的农村地区更是采取了近乎放任的态度。据ICMR援引抗体抽样调查结果估算,在“大流行”开始的前半年,孟买达拉维贫民窟(居民数量超过100万人)中的住户已经有57%感染新冠肺炎,持续将近一整年的农民抗议示威更是使社交隔离令变得名存实亡。2020年9月中旬,印度单日新增确诊病例突破10万人,达到了第一个顶峰。
仅仅5个月之前,“大流行”在印度死灰复燃看上去还是小概率事件。诚然,没有人会把疫情缓和的结果归功于人民党政府——自从2020年1月30日喀拉拉邦发现第一个本土确诊病例以来,莫迪内阁只是机械地公布了一连串的“封城令”和社交隔离规则,却没有在强化医疗系统方面投入多少资源,对卫生条件落后的农村地区更是采取了近乎放任的态度。据ICMR援引抗体抽样调查结果估算,在“大流行”开始的前半年,孟买达拉维贫民窟(居民数量超过100万人)中的住户已经有57%感染新冠肺炎,持续将近一整年的农民抗议示威更是使社交隔离令变得名存实亡。2020年9月中旬,印度单日新增确诊病例突破10万人,达到了第一个顶峰。
然而转折随即开始出现。在“封城令”迫使大量低收入的流动人口回归农村之后,疫情初期的医疗“挤兑”现象得到了缓解。数量有限的方舱医院和ICU病房开始集中力量救治症状严重的大城市确诊病患,农村人口的救助则被交给了各邦地方政府加以应对。从2020年10月起,印度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开始呈现直线下降趋势,至2021年2月初已降至9000例左右,不及巅峰期的1/10。按照新增患者数量占总人口的比例计算,印度的疫情控制水平已经和经济、医疗条件远为优越的韩国相当。以至于印度储备银行(央行)在2021年1月发表了一份洋洋得意的报告,宣称“我们像贝克汉姆(英国足球明星)踢出弧线球那样扭转了新增病例曲线”,“国家即将由不满之冬走向辉煌之夏”。在农民愤怒的谴责声中神隐近一年之久的莫迪也重新露面,在今年1月通过视频连线方式举行的达沃斯论坛上,他骄傲地宣称,印度“通过有效遏制病毒,使人类躲过了一场大灾难”。
一派云开日出的气氛中,讨论“印度何以抗疫成功”一时间成为诸多流行病学家和外国观察家热衷的课题。有人口学者宣称,印度相对年轻的总体人口结构(年龄中位数仅为27岁)和老龄化趋势明显的西欧相比是一种优势,因为这意味着重症感染者出现的比例更低,年轻病患也更有希望免于因呼吸系统衰竭而死亡。一个政府专家组在2020年10月通过计算机模拟得出的结论则显示,到2021年2月,整个印度将因为感染人数饱和而实现群体免疫。更激进的观点是所谓“卫生假说”(Hygiene Hypothesis),它宣称:在那些居住环境拥挤、医疗和卫生条件较差的国家,人们在面对新疾病时天然就具有更强的抵抗力。印度提供的即是明证。
无论如何,紧绷的情绪开始逐渐远离印度社会。随着“封城令”渐次解除,人群重新涌向了集贸市场、餐厅和写字楼,富裕家庭则开始规划在南部海滨的旅行。当格特尔曼在2月初穿过印度中部的农村地区时,他发现连巡逻的警察也不再戴口罩了——长达一年的“防疫疲劳”和乐观主义蔓延使得民众确信危险已经远离。政客的鼓励更是进一步催化了大规模聚集事件的出现:2021年4月到5月间,印度有5个邦将要举行议会选举,而人民党期望在拥有9000万人口的西孟加拉邦有所斩获。毫无例外,那些在街头聆听候选人发言的民众没有一个遵循了社交隔离令。而在4月8日举行的赫尔德瓦尔(Haridwar)“大壶节”庆典上,数以百万计的印度教信徒跳进恒河、沐浴祝圣。没有人告诉他们,就在庆典开始前四天,负责仪式的祭司已经被确诊感染新冠。
61岁的苏米娅·斯瓦米纳坦(Soumya Swaminathan)是极少数没有被乐观情绪冲昏头脑的印度医疗专家之一。她出生在金奈一个享有盛誉的知识分子家庭,从全印度医学科学研究所获得儿科医学博士学位,深知这个庞大国家医疗体系的真实内情。由于统计系统的不可靠,即使在承平时期,印度政府每年公布的死亡数字可能要比实际情况低1/5。而在新增病例的增长趋势放缓之后,由ICMR主导的核酸筛查以及疫苗接种步骤也一下子变慢了——2021年1月16日,莫迪政府宣布启动全民疫苗接种计划,第一批优先面向医护人员、军警以及基层公务员,目标是在前三个月内完成1.17亿剂次的接种。但由于印度药企同时还承担了出口海外的疫苗的生产任务,疫苗施打实际上仅仅集中于少数城市。而整个印度的核酸检测普及率还不到美国的一半。
斯瓦米纳坦开始发出警告。3月13日,她在一次采访中告诉印度媒体:“我们还没有到可以自满的时候,疫情随时可能再度‘起飞’。”ICMR提供的数据显示,从2月中旬开始,全印度单日新增病例数重新恢复了缓慢上升的势头,至3月中旬已经突破2万例大关。这其中,尤其值得担忧的是2020年10月在马哈拉施特拉邦首度发现的谱系B.1.617变种病毒,即WHO命名的“德尔塔”和“卡帕”变异毒株。与原型病毒相比,它们的传染性进一步增加了60%,并且可以借助“免疫逃逸”现象抵冲疫苗的效力。而印度防疫部门对此完全束手无策。
不幸的是,斯瓦米纳坦的身份不是印度总理,而是WHO首席科学家。她在日内瓦发出的警告,只有很少一部分传到了同胞们的耳朵里。而在新德里,莫迪已经打定主意:无论2021年发生多么剧烈的疫情反弹,他都不会重启一年前被证明确有实效的“封城”举措。总理的动机通过阿米特·沙阿转告给了媒体:“没有理由要求印度最贫困的那些公民放弃工作、隔离在家。他们的积蓄已经所剩无几,很快就要开始饿肚子了。”事实是,在度过了一个真实GDP增长率仅为-7.3%的惨淡年头之后,人民党政府不愿再牺牲经济来保障疫情防控了。
 新德里和孟买的居民们开始感到“事情好像有点不对劲”,大约始于3月的最后一周。起先是剧烈咳嗽和发热的患者数量重新开始激增,接着是医院一家接一家地在“挤兑”中濒临瘫痪。格特尔曼从新德里一家检测机构了解到,4月前两周,接受核酸检测的市民中呈阳性的比例从3%一路上升到了36%,而更多贫民窟和农村居民还没有条件接受筛查。患者家属开始给他们能想到的一切“大人物”打电话,从亲戚、同学到所在选区的国会议员,希望能搞到空床位、氧气瓶、退烧药乃至一切可以带来生存希望的东西,但应者寥寥。进入4月最后一周,印度主要城市的医疗系统已经在事实上宣告崩溃。4月30日,全国新增病例数达到了破纪录的40万。
新德里和孟买的居民们开始感到“事情好像有点不对劲”,大约始于3月的最后一周。起先是剧烈咳嗽和发热的患者数量重新开始激增,接着是医院一家接一家地在“挤兑”中濒临瘫痪。格特尔曼从新德里一家检测机构了解到,4月前两周,接受核酸检测的市民中呈阳性的比例从3%一路上升到了36%,而更多贫民窟和农村居民还没有条件接受筛查。患者家属开始给他们能想到的一切“大人物”打电话,从亲戚、同学到所在选区的国会议员,希望能搞到空床位、氧气瓶、退烧药乃至一切可以带来生存希望的东西,但应者寥寥。进入4月最后一周,印度主要城市的医疗系统已经在事实上宣告崩溃。4月30日,全国新增病例数达到了破纪录的40万。
“听上去很荒唐:全世界重要的疫苗、医疗器械和医疗级氧气生产国,竟会在整整几个星期里陷入严重短缺状态。”华盛顿大学客座教授、全球卫生智库“疾病动力学、经济与政策中心”(CDDEP)创始人拉马南·拉克斯米纳拉扬(RamananLaxminarayan)几乎出离了愤怒,“更荒唐的是,这个国家的政府似乎没能从第一波疫情中学到任何东西。”第二波疫情开始暴发时,拉克斯米纳拉扬正在新德里的家中,他说服了自己的研究伙伴放下办公室里的工作,投入到寻找氧气瓶和供氧设施的志愿服务中。“印度理论上的单日氧气产能是8500吨到9000吨。去年第一波疫情中,全国医用氧气的需求峰值是单日3000吨;即使把这个数字翻一番,供给也是充足的,”拉克斯米纳拉扬在邮件中告诉本刊,“问题在于,满载着氧气的低温罐车被堵塞在了路况糟糕透顶的中部公路上,而政府在中北部地区扩建氧气工厂的承诺根本没有兑现。那些患者是在绝望的等待中死去的。”
拉克斯米纳拉扬的分析,得到了Inox集团执行董事悉达斯·杰恩(Siddharth Jain)的赞同。作为印度最大的医用氧气供应商,Inox旗下的550辆大型罐车和600名司机从2020年春天开始就马不停蹄地向800家医院运送氧气,但在二次疫情期间依然陷入了供不应求的境地。杰恩告诉英国BBC记者:“卫生部在去年9月发放了新建162家制氧工厂的许可证,但到2021年4月为止,只有33家真正完工了。我们的罐车从东部的老工厂满载着氧气出发,最长需要行驶1500公里才能抵达目的地。一旦途中遭遇事故或者拥堵,交付就会延误。铁道部紧急调用了一批货运列车来参与氧气运输,但可笑的是,他们却没有准备好专门的容器。最后反而是Inox通过美国的合作方搜罗到一批20吨大型气罐,这才解决了问题。而气罐从美国运来又需要耗费时间。”
在德里,格特尔曼看到电视上出现了一个怪异的画面:印度空军的C-17“环球霸王”大型运输机从新加坡樟宜机场起飞,满载着从当地购买的空氧气罐返回祖国。他觉得这着实太荒诞了,“政府实际上是在花高价空运空气”。这些不远万里运回的氧气罐需要首先运抵东部的工厂,进行大约12个小时的气密性检测和灌装,随后才能载着宝贵的氧气,借助铁路或者公路输送到目的地。每一次重新灌装,又要经历一遍类似的流程。从美国和欧洲采购的呼吸机直到4月下旬才开始成批运抵一线医院,此时二次疫情已经开始整整一个月了。
 类似的混乱,也出现在了至关重要的疫苗问题上。总部设在浦那的印度血清研究所(SII)是全球最大的疫苗制造商,年产能可以达到15亿剂。早在2020年6月,该公司就和英国阿斯利康制药签署了合作协议,计划生产至少10亿剂牛津阿斯利康疫苗,以满足包括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需求。阿尼尔·赫巴尔参加的就是这种疫苗在印度的第一批接种试验。莫迪政府随后还宣布加入由WHO发起的COVAX计划,承诺将向全球92个中低收入国家提供2.4亿剂阿斯利康疫苗。到了2021年1月,另一家本土药企巴拉特生物科技(Bharat Biotech)和ICMR联合开发的灭活疫苗Covaxin也获得了紧急使用授权,成为印度在产的第二种新冠疫苗。
类似的混乱,也出现在了至关重要的疫苗问题上。总部设在浦那的印度血清研究所(SII)是全球最大的疫苗制造商,年产能可以达到15亿剂。早在2020年6月,该公司就和英国阿斯利康制药签署了合作协议,计划生产至少10亿剂牛津阿斯利康疫苗,以满足包括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需求。阿尼尔·赫巴尔参加的就是这种疫苗在印度的第一批接种试验。莫迪政府随后还宣布加入由WHO发起的COVAX计划,承诺将向全球92个中低收入国家提供2.4亿剂阿斯利康疫苗。到了2021年1月,另一家本土药企巴拉特生物科技(Bharat Biotech)和ICMR联合开发的灭活疫苗Covaxin也获得了紧急使用授权,成为印度在产的第二种新冠疫苗。
然而一旦进入接种流程,熟悉的“印度效率”立即不期而至。阿斯利康疫苗在临床试验中的数据可靠性风波导致印度卫生官员出现了犹豫心理,他们迟迟不愿批准正式启动全民接种,B.1.617变种病毒的发现同样牵制住了ICMR的精力。于是,在SII已经开始向南非、缅甸、加纳等国交付阿斯利康疫苗的同时,印度本国的实际接种启动时间却从莫迪宣布的1月中旬延宕到了2月底,并且继续伴随着混乱——一位班加罗尔商人告诉美国彭博社记者,他本人并不属于第一批接种对象,但只花了很少一点精力就找到了愿意提供注射的诊所,而许多被迫暴露在危险环境中的基层医护人员和新闻记者却得不到类似的待遇。尽管到了3月下旬,莫迪政府决定暂时延缓向外国客户(包括COVAX计划)交付疫苗的进度,以优先保证本土的供应量,但直到第二波疫情全面暴发为止,整个印度仅有10%的国民注射了第一剂疫苗,完成全部两针接种者更是只有区区1.6%。
 即使是最铁杆的莫迪支持者,在触目惊心的疫情面前也无法再为政府的失职做辩白。全国第二大英文报纸《印度教徒报》(The Hindu)在4月下旬发表了一份言辞激烈的社论,谴责政府“完全放弃了对底层贫民应尽的责任”。民族主义媒体“共和电视台”的创始人阿纳布·戈斯瓦米(Arnab Goswami)一向是总理的粉丝,这一次也罕见地表达了不满:“你们总在说自己为印度人民做了这个、做了那个,可氧气在哪里?都是胡扯!”
即使是最铁杆的莫迪支持者,在触目惊心的疫情面前也无法再为政府的失职做辩白。全国第二大英文报纸《印度教徒报》(The Hindu)在4月下旬发表了一份言辞激烈的社论,谴责政府“完全放弃了对底层贫民应尽的责任”。民族主义媒体“共和电视台”的创始人阿纳布·戈斯瓦米(Arnab Goswami)一向是总理的粉丝,这一次也罕见地表达了不满:“你们总在说自己为印度人民做了这个、做了那个,可氧气在哪里?都是胡扯!”
莫迪从未回应这类问责。事实上,人民党政府采取了和面对农民抗议时类似的策略,一方面拒绝正面答复,另一方面频繁切断网络通信,试图阻止信息扩散。北方邦高级部长约吉·阿迪亚纳斯(Yogi Adityanath)公开宣称,假如有人不满医院缺少氧气,那么他应该捐出自己的财产而不是叫板政府。偏偏疫苗生产商在这个节骨眼上也跑出来诉苦——4月中旬,SII和巴拉特先后要求政府提高疫苗采购价,理由是“全球医疗供应链价格普遍上涨,企业无法再以约定的低价提供产品”。这差点导致愤怒的浦那民众围困SII总部办公大楼。
在拉克斯米纳拉扬看来,尽管目前问世的几种疫苗在应对变异病毒时的效果还有待商榷,但全民接种始终是避免疫情出现波动式反复的最佳方案。不过,被寄予厚望的印度医疗产业在疫苗生产方面的表现并不及预期——SII制定的阿斯利康疫苗产能目标为每月1亿剂,但由于印度无法自产一次性生物反应袋和过滤器,需要从美国进口,实际产能仅能达到每月7000万剂,甚至不足以满足本国的接种需求。为了填补供应缺口,印度卫生部已经批准引进俄罗斯的“卫星Ⅴ”和美国诺瓦瓦克斯医药的Covovax两种新疫苗,计划在国内投入批量生产,另外还允许少量进口莫德纳、辉瑞两种品牌疫苗的成品注射液。不过,拉克斯米纳拉扬担心那又会导致新问题:“为了在最短时间内实现群体免疫,理论上印度每天需要完成1200万剂疫苗的注射。但我十分肯定,即使疫苗供应量能达到这个水平,我们也没有足够的注射器和针头去完成计划。这些都会是疑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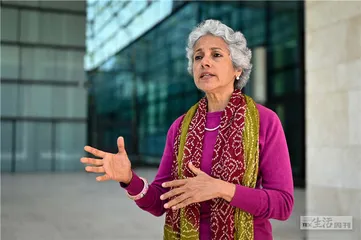 除去疫苗供应以外,印度二次疫情的实际影响,早已远远超出了一个国家。从4月中旬开始,拥有近3000万人口的尼泊尔同样遭遇了第二次疫情暴发,单日新增病例数至5月中旬已经突破9000例。检测结果证实,传染源大部分来自从印度返回的跨国劳工,其中夹杂有大量变异病毒感染者。而在印度已经上演的医疗“挤兑”、疫苗短缺等现象,同样在基础设施更为落后的尼泊尔重演了。另一个被印度疫情殃及的南亚国家是岛国斯里兰卡,高度依赖旅游业收入的该国在今年4月短暂取消了针对印度游客的入境限制,并鼓励国民进行短途旅行,结果却是新增病例创造历史新高。而在印度于5月1日起启动针对本国国民的第二轮疫苗接种行动,同时暂缓向国外交付疫苗成品的背景下,被列入COVAX计划受助国的斯里兰卡只能转向俄罗斯采购更多疫苗。
除去疫苗供应以外,印度二次疫情的实际影响,早已远远超出了一个国家。从4月中旬开始,拥有近3000万人口的尼泊尔同样遭遇了第二次疫情暴发,单日新增病例数至5月中旬已经突破9000例。检测结果证实,传染源大部分来自从印度返回的跨国劳工,其中夹杂有大量变异病毒感染者。而在印度已经上演的医疗“挤兑”、疫苗短缺等现象,同样在基础设施更为落后的尼泊尔重演了。另一个被印度疫情殃及的南亚国家是岛国斯里兰卡,高度依赖旅游业收入的该国在今年4月短暂取消了针对印度游客的入境限制,并鼓励国民进行短途旅行,结果却是新增病例创造历史新高。而在印度于5月1日起启动针对本国国民的第二轮疫苗接种行动,同时暂缓向国外交付疫苗成品的背景下,被列入COVAX计划受助国的斯里兰卡只能转向俄罗斯采购更多疫苗。
2021年6月第一周,印度单日新增病例数从40万回落至10万以下,标志着第二波疫情暴发的最艰难阶段已经过去。然而,将近36万病逝者的生命已经永远从南亚次大陆上消失了。他们中有医护人员、记者、警察、社工,以及许许多多先是失去了工作,继而在氧气和疫苗短缺中离开的普通人。这当中,尤其令人不忍的是大批感染了变异病毒的青少年。赫巴尔回忆起,4月下旬的一个晚上,他曾经开车在孟买全城疾走,希望为一个奄奄一息的5岁男孩找到一个可用的氧气瓶。3个小时后,氧气瓶终于送到,但男孩只多活了12分钟。
 医疗疫苗事件国际社会疫情问题疫苗印度
医疗疫苗事件国际社会疫情问题疫苗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