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之外:女导演访谈专辑
作者:宋诗婷 3月20日那天,《你好,李焕英》的票房达到53.03亿元,这一票房成绩让贾玲超越了《神奇女侠》的导演派蒂·杰金斯,一跃成为全球票房最高的女导演。
3月20日那天,《你好,李焕英》的票房达到53.03亿元,这一票房成绩让贾玲超越了《神奇女侠》的导演派蒂·杰金斯,一跃成为全球票房最高的女导演。
紧接着,另一位女导演殷若昕执导的《我的姐姐》上映,目前票房已逼近8亿元,电影中那个“姐姐该不该养弟弟”的话题也在互联网上掀起一波又一波讨论。
再过几天,奥斯卡颁奖典礼即将揭晓,已经手握金球奖最佳导演奖杯的赵婷依然是大热门,很可能凭《无依之地》拿下不止一座小金人。
再往前回顾,2020年9月,香港导演许鞍华拿到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奖”奖杯,成为获得该奖项的全球第一位女性导演。
把这些成绩加在一起,华人“女性导演”取得的成就和关注度,从没像这一年来得如此猛烈和集中过。
这当然得益于大环境。贾玲的成功几乎集中了最近几年国内所有高票房导演的几大特征。在贾玲横空出世之前,排在华语电影票房前两位的《战狼2》《哪吒之魔童降世》的导演都不是科班出身;徐峥凭《泰囧》成功转型导演后,赵薇、陈思诚、黄渤、吴京……一大波演员开始转型导演,都取得了不错的市场反馈,如今,贾玲也成为其中一员;喜剧向来是观众喜欢的类型,这也是贾玲擅长的。
这两年,《三十而已》《乘风破浪的姐姐》《脱口秀大会》等影视剧、综艺先在小荧幕上火了一把,输出的女性价值和态度尚值得讨论,但女性议题和让女性站出来发声变得更让人期待。
《你好,李焕英》《我的姐姐》正好出现在这个时间点上。两部电影都讲亲情,一部为纪念母亲而创作,另一部探讨的是重男轻女、女性自由与责任的话题。
赵婷和她的成功则建立在华裔电影人多年来探索个人表达与好莱坞主流文化如何平衡的基础上。《无依之地》是赵婷与奥斯卡奖得主、女演员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密切合作的产物,一个倔强而孤独的女人,选择离开城市、居所,开着车上路,成为新时代的游牧人。这故事里有美国社会的阶层、种族、养老和医疗体系探讨,也有一个女人内心的挣扎。
“Me too运动”之后,好莱坞自我修正的方式是支持女性电影人和女性电影,最近几年,大银幕上多了很多“女超级英雄”,站在超级英雄背后的,也开始有派蒂·杰金斯一样的女性导演。赵婷也已经与迪士尼合作,执导后面的漫威“超级英雄”系列电影。

 女性导演所带来的女性视角也被大众所讨论。不久前,赵薇发起的“听见她说”系列女性独白剧上线,这系列短剧贡献了包括原生家庭、家庭暴力、重男轻女、大龄剩女在内的八个女性议题,七位参与的导演中有五位是女性导演。
女性导演所带来的女性视角也被大众所讨论。不久前,赵薇发起的“听见她说”系列女性独白剧上线,这系列短剧贡献了包括原生家庭、家庭暴力、重男轻女、大龄剩女在内的八个女性议题,七位参与的导演中有五位是女性导演。
《你好,李焕英》里有个不起眼的小情节,后来却被视作“女性导演和编剧才有的对同性的善意”。电影开头,贾晓玲以为当年妈妈的同事抢了妈妈能成为厂长家儿媳妇的机会,按多数电影的套路,这位叫王琴的阿姨必然处心积虑,是个反派角色。但在电影结尾,观众才知道,王琴没做任何小动作,她去深圳打拼,和厂长儿子自由恋爱,也是个独立、坚强的女人。
《我的姐姐》探讨的问题就更直接,一个从小在重男轻女环境下长大的女孩,父母去世前没怎么好好待她。在这样的环境下,她要不要像姑妈一样,为弟弟和家庭牺牲自己的人生?张子枫饰演的安然用了很多激烈的方式反抗,虽然最终走向了和解的结局,但那些质疑和反抗也是很少有华语电影去触及的。
由此看来,《你好,李焕英》和《我的姐姐》在商业上的成功是有价值的,至少贡献了“李焕英”和“安然”两个成功的女性形象,并用票房成绩证明了女性导演和女性题材的价值。
 尽管当下这股女性题材和女性导演热度不知能持续多久,但走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如果追溯中国女性导演的历史,1925年完成自导自演的作品《孤雏悲声》的谢采贞大概可以算作“中国第一位女性导演”。和当下的很多转行而来的导演一样,谢采贞也是演员出身。那是个追捧女明星的时代,“五四运动”带来的女性意识和自由精神大多体现在当红的女演员身上,在阮玲玉、胡蝶被追捧的大上海电影圈,谢采贞并不显眼。
尽管当下这股女性题材和女性导演热度不知能持续多久,但走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如果追溯中国女性导演的历史,1925年完成自导自演的作品《孤雏悲声》的谢采贞大概可以算作“中国第一位女性导演”。和当下的很多转行而来的导演一样,谢采贞也是演员出身。那是个追捧女明星的时代,“五四运动”带来的女性意识和自由精神大多体现在当红的女演员身上,在阮玲玉、胡蝶被追捧的大上海电影圈,谢采贞并不显眼。
有资料记载,当年,这部电影首映式选在了维多利亚剧院,当天的反响还不错,《申报》还针对电影和谢采贞做了很多报道。但后来不知怎的,电影界有关谢采贞的消息就再难找到了,除了零散的报道和资料,《孤雏悲声》也没有留下任何影像资料。
抗战时期,华语电影圈倒是有一位出名的女性导演,出生、成长在美国的伍锦霞。虽然是华裔身份,也一度被称为“好莱坞唯一的华裔女导演”,但她一生拍摄的11部电影都在讲中国人的故事,都用粤语和普通话拍摄。接受采访时,她也说,自己是为中国人拍电影的。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能拍电影,还要得益于伍锦霞出生在一个富商家庭。为了满足女儿的梦想,父亲投资为伍锦霞办了个电影制作公司。1935年,伍锦霞21岁,到处筹钱拍出了自己的处女作《心恨》。电影到香港放映,她就顺便在香港继续拍电影。
在抗战年代,电影用来同情受难者,控诉战争和歌颂英雄,具有明显的功能性。但那时,伍锦霞的电影已经具有明显的女性意识。《民族女英雄》讲国防故事,但也在鼓励女性参与战争,保家卫国。除了呼吁女性为国家出力,伍锦霞还拍摄了一系列“爱情喜剧”,用幽默的方式呈现爱情、婚姻关系里的伦理和道德。
如今回头看,伍锦霞可能是在张暖忻之前,华语电影史上第一个拍出真正的“女性主义电影”的导演。她在另一部电影《女人世界》里为观众呈现了一个女性群像。教师、记者、律师、舞女……她将镜头对准了各个阶层、各个职业和不同境况中的女人们。整部电影动用了三十六位女演员,那是当时在香港拍摄的唯一一部全部由女演员演出的电影。
1949年之后,中国文学、艺术进入了“十七年”时期——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之前的十七年时间。那是一个对女性电影工作者很友好的年代。“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让女性电影人的工作更具合法性,国家培养和电影制片厂制也让女性导演有了相对安稳的工作环境。
“第四代”导演都是在“文革”之前在专业院校学习导演,当时,文学和电影的叙事传统还没有断。即便今天回头看,“第四代”的讲故事能力依然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但就像那个时期一切艺术都为宣传服务一样,电影创作也有它明确的任务和使命。董克娜和王苹的作品最有代表性。无论是《昆仑山上一棵草》《柳堡的故事》,还是《霓虹灯下的哨兵》都体现了当时的集体主义精神。她们的电影主角常常是女性,电影自然在讴歌女性,但更多的是以女性为描述对象,讴歌一种无私奉献、爱国爱集体的时代精神。
改革开放之后,在上世纪80年代,年龄稍轻的“第四代”女导演张暖忻、黄蜀芹等人贡献了一批有个性的大银幕女性形象,以及有批判和反思精神的女性题材电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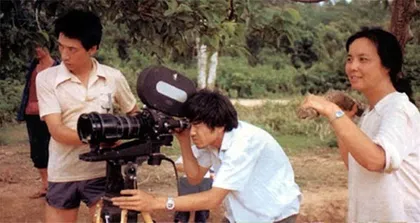 张暖忻的《沙鸥》和《青春祭》都是以人物成长和命运为主线的电影。《沙鸥》是当年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推出的一系列体育题材电影中的一部,讲的是女排球运动员经历伤痛、失败和时代变迁后,仍然坚持排球事业的故事。张暖忻在电影里融入了更多时代背景和人物的挣扎。
张暖忻的《沙鸥》和《青春祭》都是以人物成长和命运为主线的电影。《沙鸥》是当年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推出的一系列体育题材电影中的一部,讲的是女排球运动员经历伤痛、失败和时代变迁后,仍然坚持排球事业的故事。张暖忻在电影里融入了更多时代背景和人物的挣扎。
《青春祭》的切入口更小,讲的就是一个下放到傣寨的知青,在当地融入生活,从傣族姑娘们身上学会了美,自我的女性意识一点点觉醒的故事。电影的结尾很有隐喻性,刚刚找到了自我,感受到了野生力量的女孩意识到自己不属于那里,不得不回到城市,而她在寨子里结识的伙伴在一次泥石流中丧生。
黄蜀芹1987年导演的《人·鬼·情》是一部标准的女性主义电影,这被所有女性主义电影和女性主义研究者所认同。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看来,《人·鬼·情》甚至是迄今为止,中国女性电影脉络上最重要的一部电影。
 电影改编自戏曲演员裴艳玲的真实经历,讲一个艺术上不断成功的女演员如何不断在情感、婚姻、舆论中陷入泥沼,最后不得不选择隐藏在钟馗这个男性面具下,试图摆脱自己女性困境的故事。黄蜀芹用了相当多的象征和隐喻手法来展现女人内心的痛苦和挣扎,这在之前女导演拍摄的现实主义电影里是少见的。
电影改编自戏曲演员裴艳玲的真实经历,讲一个艺术上不断成功的女演员如何不断在情感、婚姻、舆论中陷入泥沼,最后不得不选择隐藏在钟馗这个男性面具下,试图摆脱自己女性困境的故事。黄蜀芹用了相当多的象征和隐喻手法来展现女人内心的痛苦和挣扎,这在之前女导演拍摄的现实主义电影里是少见的。
1978年,高考恢复。北京电影学院迎来了“文革”之后的第一届学生。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包括这些今天的“大导演”在内,那一年,电影学院录取了28个学生,李少红、胡玫、彭小莲和刘苗苗也在其中,都有至今会被提起的作品。他们都被归入“第五代”。
李少红、彭小莲们是中国女导演中为数不多的先后经历过大制片厂制和商业浪潮的一代。当年,中国电影还是“计划经济”时代,导演和演员都是领了任务干活。毕业后,电影学院“78级”的导演们被分配到了全国各地的电影制片厂。李少红留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刘苗苗去了潇湘电影制片厂,彭小莲被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
七八十年代的大学还是精英教育,尤其是艺术类院校,招来的学生也大多出自干部家庭或知识分子家庭。本来就心高气傲,都想拍出好东西。在加上,80年代整体的开放思潮和反思情绪,每个人都想铆足了劲,想形成自己的风格,完成自我表达。
但那时候,导演想拍什么,不是自己说了算,尤其是刚参加工作的新导演。在这几位女同学里,最顺利的要数胡玫。当时,男同学们的脚步更快,陈凯歌已经导演了《黄土地》,张艺谋也拍完了《一个和八个》。八一电影制片厂也想赶上去,就让年轻导演胡玫带人成立了一个青年摄制组,搞探索和创作。1985年,胡玫拿出了自己的探索成果《女儿楼》。那之后的三两年,刘苗苗的处女作《远洋轶事》、彭小莲的《我和我的同学们》,以及李少红那部最卖座的《银蛇谋杀案》先后创作完成。
“第五代”成长起来的那些年,正是欧洲女权主义运动、理论和文化快速发展的几年。欧洲涌现了一批女性导演,“女性电影”就此诞生。欧美概念中的“女性电影”和我们常常提到的概念完全不同,“女性电影”的全称是“女性主义电影”,是女性主义运动的产物之一。而当时的女性主义理论是“女性电影”最重要的文化依据。甚至可以说,那个年代的欧洲“女性电影”都是为展现和服务于女性主义运动和理论而拍摄的。所以,当年那些最早投入电影创作的女导演们都有明确的女性意识,她们拍摄了大量的实验片,试图推翻男性统治的话语体系,创造全新的语言和表达方式。
在国内,状况完全不同。在后来的“第五代”导演采访中,几位女导演都或多或少地谈及自己创作起步阶段的女性身份和女性意识。当年,李少红不想接下《银蛇谋杀案》这个项目,不是因为它不够女性,而是它不够创新和实验。那部电影是部犯罪片,放在今天看就是个标准的商业片。胡玫的《女儿楼》倒是一部女性题材作品,讲述一个在野战医院工作的护士乔小雨的初恋故事。后来,影评界很多人把这部电影评价为“中国文革后第一部女性题材”。但在当时,胡玫也没有明确的性别意识,那只是她出于自身经验和顺应创作规律的自然选择。
很多年后,李少红拍出了至今被视作女性题材电视剧标杆的《大明宫词》,那之后,她才开始对女性导演、女性表达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被大制片厂制统治的那些年反而是中国女性导演创作环境很好的一段日子,因为没有市场竞争和票房压力,大家能安心创作,各地方的制片厂都有女性导演。后来,市场浪潮袭来,很多女导演无法适应弱肉强食的市场环境,渐渐淡出了大众视野。
类似的状况也在香港发生。“台湾电影新浪潮”“香港电影新浪潮”和“第五代”是相互影响、先后出现的电影艺术革命。1979年,当李少红那批女性导演还在学校念书时,许鞍华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处女作《疯劫》。和李少红的《银蛇谋杀案》类似,也是一部类型化的电影,没有明显的女性态度,同样在票房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许鞍华也出自TVB电视台,没有票房压力的创作环境曾给了她很大的创作自由,在电视台那两三年,为她积累了后续拍电影所需的技术和人脉。
真正开始就自觉将镜头对准女性身体和精神困境,还要从李玉、尹丽川、郭小橹、徐静蕾等一批“70后”导演算起。我也愿意把宁瀛列入这个行列,尽管她是“50后”导演,是电影学院“78级”一代,但她从90年代的《找乐》到后来让很多男人觉得受到冒犯的《无穷动》,都将目光投向了城市,讲都市生活中的困境,赤裸裸地展现女人的欲望。
李玉的《苹果》《今年夏天》等电影都把城市作为空间背景,消费主义的大环境下,边缘人和弱势群体不得不为生存挣扎,为身份而隐藏、委屈自己。在《苹果》里,被强奸的苹果反而成为代孕的工具,这也是当时大银幕上少有的把女性被强奸、性侵拿到台面上讲述的电影。
徐静蕾早期的电影偏文艺,在我看来,她早期的三部作品其实是在讲述一个女人成长和走入社会后与男人的三种关系:亲人、爱人和朋友或同事。《我的爸爸》讲父女关系;《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改编自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同名小说,讲一个女人对男人的爱情;《当梦想照进现实》则是一个女演员和一个女导演对现实生活的控诉,是逃脱现实生活的同盟。包括后来商业性更强的《杜拉拉升职记》在内,徐静蕾代表了一类都市女性,她们已经摆脱了物质生活的困扰,“我是谁”的问题不再被压抑于日常生活,而是变成了一个更虚无缥缈的哲学命题。
最近几年,女性导演的电影风格和主题也越来越宽泛。赵薇、薛晓路、苏伦等导演在商业片领域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文晏的《嘉年华》直面性侵问题,新导演滕丛丛、杨明明等人带着更明确的女性意识拍摄自己的电影,像很多欧洲“女性电影”评价体系内的电影一样,直面女性的生理和精神世界。
 在做这个选题之前,我曾有点拧巴。一度怀疑在导演这个职业前强调“女性”,在这个年代是否有价值。甚至,是否是一种变相的歧视。
在做这个选题之前,我曾有点拧巴。一度怀疑在导演这个职业前强调“女性”,在这个年代是否有价值。甚至,是否是一种变相的歧视。
后来,我想起了之前在某个影展采访时的经历。我在那儿认识了一位“90后”女摄影师。之前,她在纽约学电影、拍纪录片。回国后,接到了一个去横店给美国导演做助理和翻译的活儿。“一到那儿就惊了。”有一次,她坐在摄影组的苹果箱上休息,却被摄影师呵斥,“女人不能坐苹果箱,不吉利。”如果她不是导演助理,很可能当天会被抬出去。
“大家一起拍戏,男人可以说累,我不能,说了就显得娇气、体力不行。”尽管她这么忍耐、克制,在影展期间,我还是听到有人发她的牢骚:“一女孩,个儿不高,还说自己喜欢拍手持镜头。”
后来,我与“山一国际女性电影展”的创始人杨婧、策展人李沫筱聊起了女性电影人的困境。“山一”是目前国内唯一有资质的女性影展,从2017年创办至今。这五年,她们接触和了解了很多女性电影人。有些时候,性别差异会突然显现。“有制片人说,在有些社交、酒会场合,男人们喝酒聊天,顺便把合作谈了,作为现场唯一一个女性,有时候确实会被边缘化。”杨婧说。一些现实的问题也不得不考虑,比如,找投资时的弱势,拍摄时的体力问题,甚至郊外拍摄去个卫生间,女性工作人员和演员都更麻烦一点。
今年,“山一”做了一个统计,从影展创立的2017年算起,到2021年上半年,所有进了国内院线的电影都算在内,女导演作品所占的比例也只有10%。若是把时间线向前推得更远,这个比例还会更低。
“有明确女性立场、自我认知和身份寻找的电影本来就少,这几年才陆续多了一点,但大多是不太可能卖钱的。”《春潮》的制片人李亚平以一个商业片制片人的角度评估。
女导演杨荔钠的《春潮》是去年面试的一部女性题材电影。当年,这项目是一个朋友推荐给李亚平的。“我和杨荔钠都是‘70后’,她比我年长几岁。她出名早,我还没开始做电影就听过她的名字,看过她的纪录片。”李亚平说,2016年她作为制片人,和导演一起参加了金马创投,“当时只有一个大纲,但女性、母女三代人的关系是定下了。”
在金马奖那两三天,李亚平和杨荔钠和很多创投评委、投资人交流过。“导演很坚持,一遍遍讲她要拍中国女性的画像,觉得女性的声音应该被听到。”李亚平说,当时,“女性”这个话题还不像今天这么火,“大家一听是女性个体经验、家庭故事,就觉得没什么卖点。”那几天,李亚平留了很多投资人和片方的联络方式,后来没一个人跟进过。
当年的金马创投,还有另一部女性题材电影——杨明明导演的《柔情史》,也是女性导演,也是讲母女之间互相拒绝、伤害与是否和解的故事。2018年,《柔情史》又入围了柏林电影节的全景单元,第二年在院线上映,全部票房却只有32.1万元。因为疫情关系,《春潮》没能进入院线,直接在视频网站上架了,没经过院线检验,大银幕上的商业价值就成了未知数。
在金马奖现场,有一个场面让李亚平印象深刻。她陪杨荔钠去酒会,在酒会上,金马创投的各个奖项会逐一揭晓。“就跟公司年会抽奖一样。”李亚平说,整个公布过程她一直站在导演身边,“她整个人非常紧张,一直在发抖。”那一刻,李亚平知道了这部电影对杨荔钠到底有多重要,“当天,直到酒会结束,杨荔钠也没听到自己的名字。”
《春潮》之后,李亚平还想继续做女性题材。她手头有个讲上海中老年相亲的剧本,改编自前两年一篇流传度很广的特稿。陈冲看上了这个故事,愿意出演。“即便这样,剧本递到视频网站找合作,还是第一轮就给毙掉了。”李亚平觉得,在当前的环境下,女性题材没想象中那么受追捧,涉及到思考社会身份、自我认知,剖析痛苦和欲望的故事,怎么拍都有点严肃和偏小众。“观众需要什么样的女性故事,电影该如何表达,还需要摸索。”
在李亚平看来,在今天,强调女性大银幕形象和女性导演的话语权是一件很有必要的事。“你看中国票房排在前100位的电影,有多少能让人记得住的女性形象?有多少出自女性导演之手?”简单的统计,现实状况就很明朗了,“很长一段时间里,你找不到多少印象深刻的女性形象,不管卖不卖座,除了个别小妞电影、爱情片、喜剧,女性作为主角的电影都很少。”李亚平觉得,商业片兴起以来的中国院线电影和当年的好莱坞主流电影一样,“男性视角就是客观视角。”
在电视剧领域,早几年有海清、孙俪,“流量”兴起的这些年有赵丽颖、杨幂等女演员,因为有过商业上取得成功的代表作,因此被市场信任,也能拿到很高的片酬。这与电视剧领域的受众偏好有关,女性观众为主,大女主、家长里短的戏就更多,女演员的机会也更多一些。
电影领域则是另一番景象。“演员是靠塑造成功的形象、取得商业价值而被认可的,但在电影领域,女演员没这个机会。”李亚平说,这几年,马丽和周冬雨算是为数不多真正“熬出头”的女演员。前者是喜剧出身,后者接连拍了《七月与安生》、《后来的我们》和《少年的你》,三部电影口碑好,又卖座,女性形象鲜明。
这或许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女性导演的声音。当下,我们正在走一条曾经好莱坞走过的路。上世纪90年代之前,好莱坞电影的女性形象和女性意识也乏善可陈,1991年,雷德利·斯科特导演的《末路狂花》取得巨大的商业成功。1993年,女导演简·坎皮恩执导的《钢琴课》横空出世,拿到那年的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这两部电影让市场看到了女性电影的机会,那之后,进入主流的女性导演越来越多,女性声音才能更好地被听到,男性导演也开始更多地涉猎女性题材。尽管,今天好莱坞大银幕上的女性形象虽还远算不上丰富,但较之从前,已经有了很大起色。
和杨婧见面那天,她刚从一个影视公司谈合作回来。“他们今年有个KPI,要拍两部女性题材的电影。”杨婧觉得,这有点难,“他们公司一百多人,七十多个女生,其中连个中层领导都没有。”杨婧的建议是,与女导演合作,或者至少启用一个女性制片人,再不济,主创团队里要有一定比例的女性,“否则,创作大概率只能停留在臆想的女性题材阶段。”
至少在眼前这个阶段,女性导演要获得业内认可会更难一些。这几年做影展,杨婧和李沫筱发现,尽管很多导演的前几部作品都与自己的人生经验有关,但男女还是有别。“男性世界的冲突和挣扎更多是向外的,很多男导演呈现出来的故事有更多戏剧性,看起来可能更商业。女性导演表达更自我、更细腻,电影显得更文学化。”以不同风格开启的职业生涯,对大家处女作之后的发展影响很大。“女性导演驾驭更大的、更商业项目的能力很多时候会受到质疑。”杨婧觉得,这可能是女性导演作品周期更长,更难开拓市场的其中一个原因。
 2016年,《好莱坞报道》曾发布过一个调查:“过去十年,80%的女性导演只拍了一部电影。”在华语电影圈,这状况也相似。
2016年,《好莱坞报道》曾发布过一个调查:“过去十年,80%的女性导演只拍了一部电影。”在华语电影圈,这状况也相似。
但事情在慢慢变好。刚做“山一”时,杨婧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给人解释“女性电影”和“女性影展”。谈及“女性影展”定位,最常要区分的概念是——女性导演拍摄的电影、有女性意识的电影和更狭义的兴起于欧美的女性主义电影。为了空间更大,也更符合国内大环境,“山一”走的是包容性更强的路线,女性导演和有女性意识的电影都包括在内。“前两年要从头讲起,这两年有了明显变化,品牌和合作方会主动问是两三种定义中的哪一种。至少,这个话题从填空题到了做选择题。”杨婧还发现,最近两年,国内的各大电影节、影展都有了女性电影、女性电影人的相关板块,“几乎成了标配”。
最近,李亚平作为评委参与了今年的“青葱计划”,这个青年电影扶植计划曾帮白雪(《过春天》)、梁鸣(《日光之下》)等年轻导演完成了他们的处女作。“在今年入围的十位导演里,男女导演差不多一半一半。”李亚平发现,“85后”和“90后”的女导演越来越多,即便是男性导演也有了更好的女性意识,很多人在创作女性角色时,已经跳出了以往固有的标签框架。
从这些不得不面对的困境和变化的形势来看,在当下这个阶段,走近并探讨女性导演是有必要的,至少能让人看到,她们是如何一路走来的。未来将走向哪里,虽不可预料,但值得期待。 女性导演青春祭沙鸥中国电影银蛇谋杀案电影剧情片春潮电影节女性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