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官开着除草机来了
作者:刘铮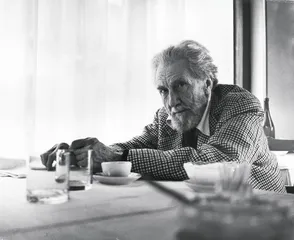 英国著名诗人埃兹拉·庞德(1967年)
英国著名诗人埃兹拉·庞德(1967年)
《阅读ABC》(The ABC of Reading),也许译作《文学入门》会更准确些。埃兹拉·庞德当年是把它设计为一本教材的,当然,事实上,它根本无法发挥教材的功用,因为流通广的教材总不免要俯就,而庞德这本书的问题就在于他的标准定得太高,除了他本人,恐怕再难找到能讲授这本教材的教师。
T.S.艾略特在为自己编选的《庞德文论选》作序时,曾指出庞德的“教师脾性”。我想,如果再准确一点,也许应该说是“教官脾性”。这位教官的严厉、专断,是今天那些掌握着给授课教师打分大权的学生们不能接受的,而这恰恰也是今天教育(尤其是人文教育)失败的一大原因:竟有人以为,知识和技能在严酷的训练之外还有别的获得途径。
庞德明白无误地说:“真正的教育最终必定限于坚持要知道的人们,其余的仅仅是放羊而已。”(《阅读ABC》中译本第70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这样的说法,或许会得到相当广泛的赞同,然而当你充分认识到“坚持要知道”所需付出的努力,你恐怕就不会那么确定自己是否属于其中的一员了。庞德说:“我的出版商请求我将英语文学尽可能地置于显著地位。这没有用,或几乎没有用。我的意思是,如果我要对学生公平的话就不行。你不能靠读英语来学习写作。”(56页)那么,换到中国学生身上,他的要求就无异于你不能靠读中文来学习写作,你要能读英文、法文、意大利文、拉丁文、古希腊文⋯⋯庞德在《严肃的艺术家》(收入艾略特编《庞德文论选》)一文中也讲过:“我们只有,比方说,在六七种伟大的文学中,摸索出作者表达的程度,然后才能初步判断,某一作品是否有了伟大的艺术的丰富性。”这种限定、这一“最低标准”,对庞德来说,当然是不成问题的:他在英文、法文、意大利文、拉丁文、古希腊文之外,至少还涉猎过中文和日文。可是,对其他读者呢?就难说了。庞德设下的语言门槛,还不单纯是个语种数量的问题,隐含着的还有语言领会深度的问题。庞德在书中谈道:“任何懒到驾驭不了理解乔叟所需的那相对不大的词汇量的人都活该永远被关在阅读好书的大门之外。”(88页)不幸的是,我猜,99.99%非母语的英文学习者都不曾掌握“那相对不大的词汇量”。文学作品的翻译,使我们这一代读者心中形成了一种幻象,好像我们当真读过《伊利亚特》、《罗兰之歌》或《源氏物语》似的。其实,我们读的那些东西,仅相当于杜甫的七律被转成白话文,我们读到的只是那个大概的意思,我们捉住的只是原著的影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当然不配说自己已经“摸索出作者表达的程度”,自然也就没有下“初步判断”的可能了。
在通览欧洲文学全局之后,庞德开出了他的“钦定书单”。“大约在这一点上,心脏虚弱的读者通常会在路上坐下来,脱下鞋子,哭诉‘他是一个糟糕的语言学习者’或是他根本不可能学会所有的语言。”庞德这么做是故意的,因为他认定“必须要把想成为专家的读者和那些不想的区分开来。”(28页)庞德的书单,在某种程度上,的确骇人听闻。当然,其中不乏我们都能接受的名字:荷马、萨福、卡图卢斯、奥维德、乔叟、约翰·堂恩、菲尔丁、劳伦斯·斯特恩、司汤达、福楼拜⋯⋯可是他不怎么认可维吉尔,他觉得16世纪初苏格兰翻译家加文·道格拉斯翻译的维吉尔甚至比维吉尔本人更好,书中作为范例选出的所有诗作中,加文·道格拉斯的占比最大;他不太情愿推荐但丁和莎士比亚,他把弥尔顿骂了个狗血淋头;诗人布莱克呢?我不记得在这本书里见到过他的名字;16世纪的英国诗人里,庞德推崇的还有哪几位?有阿瑟·戈尔丁、马克·亚历山大·博伊德⋯⋯可是,见鬼,他们是谁?
文艺批评家的任何标举都有一种反拨的意味。庞德自然也不例外。但他标举奎多·卡瓦尔康蒂、加文·道格拉斯,而不是但丁、莎士比亚,倒不能完全看作出于单纯的逆反心理,或许他更尊重的是发明权。庞德订立了一项文学等级制度:排在第一级的,是发明者;第二级是大师;接下来,是“稀释者”——“追随前两种作者,而无法做得一样好的人”;第四级是“没有卓越品质的好作家”;第五级是“Belles-lettres(借自法语,约略相当于民国时期所谓的“美文”——引者按)作家”——“并不真正发明任何东西,但专攻写作的某个特别部分的人”;排在最后的是“风尚的发起者”,简单地说,就是十几二十年后就被忘记的那类作者。因为庞德看得深远、看得深透,所以他也许不那么看重一种技巧、一种风格成熟乃至烂熟的形态(维吉尔、但丁、莎士比亚⋯⋯),而更关注萌藤与绽露(荷马、卡瓦尔康蒂、乔叟⋯⋯)。已经有轮子了,我们就不必费心再发明它了。1492年哥伦布来到新大陆之前,那里一直没有车,假如真有哪个印第安人灵机一动想出了轮子的构造,我们也只能同情地望着他了。文学上的创造也未必不是如此。只不过普通人通常只记得那些将轮子改进到最合宜的状态的人,而庞德则喜欢褒奖那些筚路蓝缕的草创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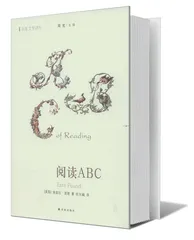 《阅读ABC》
《阅读ABC》
对于文学技巧、品位、风尚的演进,庞德有一段很好的说明:“一个大师发明一个小机件或一个程序来执行一种特殊功能或一组有限的功能。学生们应用这一小机件。他们大多没有大师用得熟练。下一个天才可能改进它,或者他可能将它抛弃而换用某件更适合他自己的目的的东西。随后便来了糨糊脑袋的学究或理论家,宣称那小机件是一项法律、一项规则。随后便成立了一个官僚机构,图钉脑袋的书记员攻击每一个新的天才和每一种形式的发明创造,因为不遵守法律,因为感觉到了那书记员感觉不到的某些东西。”(264〜265页)对于缺乏历史感的孤陋者而言,可能任何符合历史真实的判断听上去都像是奇谈怪论。庞德对那些不怎么长进的后来者,对等级制度中处于第四级、第五级的作者,时常加以调侃,比如他给(他心目中的)学生布置了这样的任务:“试找出拜伦或坡的一首没有七处严重缺陷的诗作。”(65页)这确为一种严酷,也确为一种真相,或许,真相总是严酷的。在文学世界里,最最严酷的真相不就是绝大多数的作品都是垃圾吗?
毫不留情,是一个够格的批评家对文学垃圾所能持有的唯一态度。庞德提到了对于此类作品的“非个人的愤慨”(20页)。等级,冷酷而真确。在毛姆的小说被当成世界名著的时代里,贯彻这种等级制就显得尤为必要了。懒惰和骄傲,是当代读者的两大罪过。懒惰,使他们无心关注真正伟大的东西,就像庞德说的:“通俗写作的秘密是在特定的一页里放进的绝不要多过普通读者能够轻轻舔食掉的分量,不施任何压力于他惯常松懈的注意力之上。”(56页)而骄傲,则使他们逃避教官的话语——他们受不了那股子说教劲儿,哪怕说教的内容全是对的。
对庞德的文学观念,有相当不同的评价。艾略特说庞德的文学评论“非常重要——或许是最不容我们失去的那类”(《庞德文论选》序言),而韦勒克则在《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五卷中对之不停地加以讥诮。你选择相信艾略特还是韦勒克呢?你选择相信大师、天才还是糨糊脑袋的学究或图钉脑袋的书记员呢?
〔刘铮,笔名乔纳森,毕业于清华大学,著有《始有集》、《日本读书论》(编著)〕 读书文学阅读ABC文艺批评批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