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景泰蓝
作者:李晶晶 ( 清乾隆铜胎掐丝珐琅多穆壶 )
( 清乾隆铜胎掐丝珐琅多穆壶 )
西班牙的胡安·乔斯(Juan Jose Amezaga)家族收藏着一批精美的珐琅器,有些甚至是孤品,极为难得。巴黎佳士得曾为这个家族旧藏的珐琅器做过多场专拍。业界将2007年6月13日巴黎佳士得推出的“Juan Jose Amezaga家族首场拍卖”,看成是中国铜胎珐琅器拍卖的分界点。不仅是因为此场专拍数件拍品的成交价创造了新的拍卖纪录,更重要的是此场拍卖是全球范围内真正意义上的珐琅器专拍——43件拍品全部由中国珐琅器组成。
“认识哈里·加纳爵士(Sir Harry Garner),对我的收藏起到了很大的帮助。”胡安说,“古董店、博物馆、拍卖行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一开始,我收藏的种类很多,但随着对珐琅器的了解逐步加深,我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这类艺术品的收集中去了。”胡安所说的哈里·加纳爵士是英国著名的古陶瓷收藏家,20世纪50年代他就出版了代表作——《东方的青花瓷器》。跟随着哈里·加纳爵士,胡安的收藏日渐壮大。这些藏品大部分为明清时期的,是胡安在80年代初期购买自英国的Spink&Son和伦敦佳士得等拍卖公司。这些珐琅器几乎都是在清末民初的时候流散到欧洲的。
不管什么文化、什么物品,进了中国,一定会给它起个入乡随俗的名字。掐丝珐琅也不例外,它的中国名字叫景泰蓝。景泰蓝并不是在景泰一朝出现的,早在元代就已经进入中国,只是到了景泰年间,由于皇帝的喜爱,于是它声名鹊起。其实“景泰蓝”这个名字,并不是在景泰年间开始叫的,甚至整个明朝都不这么叫。在雍正六年(1728)的《造办处活计档》中有这么一条记载:“五月初五日……其仿景泰蓝珐琅花瓶不好。钦此。”这是关于景泰蓝最早的文字记录。在晚清陈浏的《陶雅》中,写道:“范铜为质,嵌以铜丝,花纹空洞,杂添彩釉,昔谓之景泰蓝,今谓之珐琅。”虽然陈浏说反了,应该过去称珐琅,现在称景泰蓝。不过从这段记载中可以清楚地知道,至少在清后期,景泰蓝的名字已被广泛使用。从16世纪开始,一直到乾隆中期,对景泰蓝的创新改造一直不断。乾隆以后,景泰蓝的工艺可以说是越来越成熟,做得也最精细。
晚清到民国时期形成较大规模的收藏热潮,大量西方人来中国搜集文物。对于景泰蓝,西方人的认识颇高,认为这是代表中国宫廷文化或者说贵族文化的典型器物,所以大量景泰蓝都流往欧洲。受此影响,当时古玩店里不摆几件景泰蓝,显得档次低。换句话说,有品位的买家一看你店里连景泰蓝都没有,转身就出来了。
西方之所以认为景泰蓝重要,是因为他们在进入紫禁城的时候看到,凡是重要的大殿里摆放的全都是景泰蓝,有成堆的鼎式大香炉、大仙鹤、太平有象等等,还都是大件的景泰蓝。而当时清宫确实有严格规定,对景泰蓝非常重视,比如乾隆四十四年(1779)除夕,宫里吃年夜饭的时候,只有皇上的御宴桌上几乎都是景泰蓝的餐具,底下陪宴桌全部都是瓷器和银器餐具。同时在中国古代的工艺中,绝大部分都是官民共享,唯独这景泰蓝在清末“同光中兴”之前完全是宫廷独享,没有走入民间。由此可见,景泰蓝在当时宫廷中的崇高地位。
 ( 清乾隆铜胎掐丝珐琅胡人像一对 )
( 清乾隆铜胎掐丝珐琅胡人像一对 )
在胡安的收藏中,一对胡人像和鸟笼为不可多得的精品。以铜胎珐琅所制作的人物立件数量极少,目前所知国内的博物馆藏品里都没有类似的实物,故宫藏有的珐琅器物里,仅发现以人物像作为装饰部件的。珐琅鸟笼摆件是独一无二的,国内外博物馆都没有类似实物。一对“大清乾隆年制”款铜胎掐丝珐琅鸭尊摆件也非常少见,原来应该是宫廷的陈设物。虽然故宫藏品中与此完全一样的没有,但是其他动物造型的实物有,比如明代晚期的鸭子、狮子、大象摆件。乾隆时期的珐琅器器型丰富多彩,玩赏品的种类很多,大英博物馆藏有一件以珐琅掐丝工艺制作的狗窝,应该是当时乾隆帝的玩物。
掐丝珐琅是一个外来物种,是元朝时从阿拉伯地区传入中国的。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论》在“大食窑”条目下有记载:“以铜作身,用药烧成五色花者,与佛郎嵌相似,尝见香炉、花瓶、盒儿、盏子之类,但可妇人闺阁之中用,非士大夫文玩清玩也,又谓之‘鬼国窑’。”

大食是中国过去对阿拉伯地区的一个统称,“鬼国窑”则是一种蔑称。中国人的面目都比较平和,轮廓没有阿拉伯人突出。元代景泰蓝传入中国有两个阶段:第一是实物阶段,通过贸易,把景泰蓝实物直接传入中国;第二是技术进入中国。
中国人聪明,对于外来物品,只要是喜欢,一定会琢磨出它的技术,自己烧制。元代是一个典型的游牧民族统治期,与农耕民族重视手工业生产,以满足自给自足所不同的是,游牧民族更多是把产品作为商品去交换,或者换来钱去购买其他需要的生活物品,因此对于贸易以及手工业人员尤为重视。早在蒙古伐金时,就有许多汉族工匠去到和林(在今蒙古国),他们精湛的工艺令当时在和林的欧洲人为之倾倒。尚刚在《元代工艺美术史》中写道:“元代的工艺美术品并不是粗糙草率的,而是颇为精美的,其水平是很高的。蒙古贵族对于手工艺品有一种天然的喜爱,因此,他们征战所到之处,都要掠走大批工匠,聚敛众多的工艺美术品。在元代,政府集中使用着大批来自欧亚的优秀工匠,垄断着精良的生产原料,在各地设置许多官府作坊,进行着大规模的生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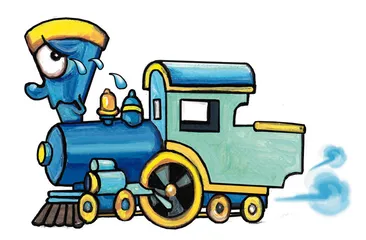 ( 哈里·加纳爵士 )
( 哈里·加纳爵士 )
元朝定都北京后,对社会等级划分得很明确,不过,由于政府对手工业兴趣浓厚,需要很多工匠为其服务,因此对于手工业者的态度还算不错,对他们高看一等。郑思肖的《铁函心史》以及谢枋的《叠山集》,分别指出了当时元人对职业的分等——“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各有所统。”
景泰蓝虽然是一个外来艺术,但经过元、明、清三朝皇家的推崇,再加上工匠的不懈努力,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史上的一朵奇葩。但由于中国文人不推崇这种繁缛华丽的艺术,导致后人不大重视,对它的研究也非常浅薄。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反而对景泰蓝的认识偏低。曹昭就说它俗,“非士大夫文房清玩也”。过去文人的这个态度,导致其大量流往欧洲。
 ( 清乾隆御制铜胎掐丝珐琅鸭尊摆件 )
( 清乾隆御制铜胎掐丝珐琅鸭尊摆件 )
曾有拍卖公司的专家说,与明清官窑瓷器市场所不同的是,珐琅器的买家都是国际性的。如果是官窑瓷器,可能亚洲市场会更好一些。“Juan Jose Amezaga家族首场拍卖”中的清乾隆御制铜胎掐丝珐琅胡人像,以652.8万欧元被Eskenazi收入囊中,这一价格成为迄今所知中国铜胎珐琅器拍卖的最高价格。
 ( 清乾隆御制铜胎掐丝珐琅鸟笼摆件 )
( 清乾隆御制铜胎掐丝珐琅鸟笼摆件 )
(文 / 李晶晶) 景泰蓝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