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流行可卡因
作者:李孟苏 2006年9月4日,英国摇滚明星皮特·多赫提因涉嫌藏毒在伦敦出席庭审
2006年9月4日,英国摇滚明星皮特·多赫提因涉嫌藏毒在伦敦出席庭审
31岁的漂亮姑娘娜塔莎·柯林斯在BBC算不上一线大明星,也还有点名气,她在收视率很高的儿童系列剧《See It Saw It》中扮演宫廷小丑,特别受小观众喜爱。小“粉丝”们给她取了个昵称——猴子。她还是不太成功的模特儿,形象只不过出现在网络广告和邮寄产品目录单上。但她的未婚夫马克·斯佩特——BBC儿童频道的节目主持人很有名。2008年新年前夕,娜塔莎在校友录中憧憬她和斯佩特即将举行的“梦幻婚礼??当然婚礼上还得有很多猴子”。
娜塔莎没能等来这一天。新年刚过,1月3日13点多,斯佩特发现娜塔莎死在了他们同住的公寓的浴缸里。尸检结果表示,娜塔莎死于可卡因摄入过量。据说,出事那天,娜塔莎吸食可卡因一直到1月3日黎明时分,开始迷糊犯困,大概在中午她醒来后觉得不舒服,便想泡个澡,接下来就是斯佩特发现她赤裸的身体。
警方怀疑斯佩特为死者提供A类药物,带走了他。交了保释金后,斯佩特暂时获得自由,在家等待警方对他的进一步调查。他通过母亲说,娜塔莎是生病吃了医生开的处方药后死的;又通过朋友告诉媒体,他没有做任何伤害未婚妻的事。不管如何辩解,他的职业生涯到此为止了。1月3日当天,BBC即停播他主持、出演的多档儿童节目。BBC现在是可卡因的重灾区,闻可卡因色变。比娜塔莎事件早几天,BBC的另一主持人凯文·格里宁服用大剂量可卡因、摇头丸、GHB(一种迷奸药)后,兴奋难当,玩起了一种很危险的性游戏,一命呜呼。BBC的可卡因麻烦始于10年前,那年小报爆出BBC最红儿童节目《蓝彼得》的主持人吸食可卡因。该主持人立刻被解雇,儿童频道的主管在电视上做了正式道歉。此后不断有主持人、演员、知名记者被义务道德协管员——小报曝光吸毒丑闻,还有更严重的:1999年BBC电台很受欢迎的DJ理查德·培根因向记者提供可卡因被捕。BBC对此类事情采取“清洁”政策,一旦事发立刻下岗。
即便有众多前车之鉴,BBC旗下将可卡因看做维他命的主持人、编导绝非只有死去的格里宁、娜塔莎·柯林斯。可卡因是传媒业的流行食品,吸食者大有人在,只不过没有曝光而已。一向中规中矩、有“大婶”之称的BBC,还有各媒体,是怎么了?戒毒慈善组织Addaction的负责人黛博拉·卡梅隆说,“BBC现象”折射出一个可怕的现实,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是可卡因的最大用户。死去的娜塔莎·柯林斯同样出身良好,一路上的是好学校,同学、老师众口一词称赞她从小是好学生,模特经纪公司的老板夸她敬业,脸上总是带着笑。她在10年前进入电视业,一入行就和知名主持人斯佩特搭档做当红的节目,成了电视明星。生活如此顺利的她却成为又一个可卡因受害者。
从外因看,一场车祸撞碎了娜塔莎的生活。她爸爸去世狠狠地打击了她,她似乎是想自杀,一头撞向疾驰的汽车。此后,她的生活滑向不幸。她病态地消瘦,从电视中销声匿迹,开始做模特儿,发展很不如意,生前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在网上宣传某品牌的床垫。外人看不到的因素在娜塔莎的可卡因生活中占有多重的比例,永远无法知晓了。反药物滥用机构发现,传媒业压力巨大,使从业人员成为可卡因的易感人群。黛博拉·卡梅隆有个星期五的晚上走出位于伦敦法灵顿区的办公室,被眼前的场景吓了一跳。法灵顿是伦敦传媒机构集中的地区之一,被酒精和药丸“嗨”高了的制片人、节目编导们不时撞到卡梅隆身上。卡梅隆说,电视从业人员普遍存在三个极端:极有压力,工作时间极长,极有成就感。对生活在聚光灯下的人士而言,必须随时保持较高的肾上腺素水平,这样才能展现出他们的魅力,绝对不能向公众露出精疲力竭的样子。他们普遍不认为自己吸食可卡因是出现了药物问题,视之为职业、社交生活的一部分。
 娜塔莎·柯林斯
娜塔莎·柯林斯
在警方的调查公布之前,不能确定斯佩特对娜塔莎沉溺可卡因起了多大的作用。不过,42岁的斯佩特是有名的“派对动物”。按伦敦社交圈的潮流,可卡因在20世纪50年代是爵士乐的背景,七八十年代做香槟的佐酒小点,如今则是一切娱乐的必备品。时髦的派对,中产阶级的晚宴别称Canapés & Cocaine——主人以Canapés(西班牙风味的开胃小吃)作头盘,送上可卡因当餐后甜点。同好们坐在一起,将一小片可卡因仔细研成粉末,在CD上撒成1.5英寸长的细线,轮流嗅吸。聚会能否掀起高潮全靠可卡因,所以伦敦时装周期间的派对上,模特、设计师、记者,人人手持“可乐”(可卡因的另一称呼),也不奇怪了。于是,酒馆或俱乐部的老板们纷纷改造厕所,让小隔间看起来干净舒适,以适合吸食可卡因。最重要的是必须把水箱藏起来,让客人找不到,以防有的客人不自觉,偷走老板藏在吧台后的可卡因,扔进水箱再找机会取走。
可卡因的流行早已不限于传媒圈,2000年后它超过大麻、安他非命、摇头丸,成为英国头号毒品。据英国国民医疗保健系统发布的药物滥用报告,7%的成年人(英国现有人口6000万)曾吸食可卡因,是10年前的4倍;英国紧跟西班牙之后,成为欧洲第二大可卡因消费国家,每年购买可卡因的金额近30亿英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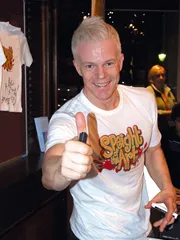 卷入可卡因丑闻的知名主持人马克·斯佩特
卷入可卡因丑闻的知名主持人马克·斯佩特
英国最大的可卡因消费群体和黛博拉·卡梅隆平时帮助的瘾君子完全是两个阶层的人。传统药物依赖者多是社会边缘人、贫困社区缺乏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失业者、被银行没收财产的人、精神异常者、长年的病患;可卡因的用户,伦敦一个可卡因零售商描述说,是些“有份正当的工作,星期五晚上想出去乐和一把的普通中产阶级”,甚至有口碑“稳重、循规蹈矩”的部长、法官、律师。
进入21世纪以来,可卡因价格暴跌,最近的市场价格每克40?60英镑,让这种原本专属雅皮士和摇滚歌星、模特儿们的“娱乐消费品”迅速流传开来,比麻醉剂还容易得到,在某些地区的酒馆,可卡因半公开出售。警方的传统观念认为,娱乐性的吸食可卡因很少引发刑事犯罪,部分警界人士对可卡因的态度要轻松得多。法律对贩卖可卡因的行为处罚较轻,毒贩子们纷纷改行做这一生意。
很多毒品有“阻断系统”,吸食以后人的精神渐渐颓靡;吸了可卡因后,食欲、睡眠的生物钟不会发生变化,反而在数秒钟之内为吸食者提速,让人做什么事都很起劲儿,为担心不能按时完成工作的白领助了一臂之力。因此可卡因往往被视作“干净的”药物,有了两个亲切的名字,“白雪”和“查理”。这些名字暗示它很安全,对身体的危害可以忽略不计。
从社会规范的角度讲,可卡因通过鼻子用力嗅吸,没有海洛因的针管注射法那么大张旗鼓,也就不会引发海洛因级别的社会耻辱感。全国性的戒毒组织“转折点”西伦敦分部的主任说,他的一位从事金融业的朋友派驻纽约3年后回到伦敦金融城,看到同事们在办公室派对上吸可卡因,极为惊骇。在美国,绝对见不到此类情景,这意味着可卡因在伦敦是可以被接受的。伦敦大都会警察局局长伊恩·布莱尔爵士认为,中产阶级吸食可卡因有很大的隐蔽性。他们有稳定的工作,很少因为吸毒把生活搞得一团糟,从而引起警方和反药品滥用机构的注意。而且,他们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逃脱了法律的监督和制裁。这更加深了对可卡因的误解。就连可卡因贩子都给自己定位是“手机店老板那类服务业从业人士”,而非社会公敌。
伦敦圣玛丽医院的毒物学教授约翰·亨利说,有1/7的可卡因吸食者需要治疗。早在2001年,他平均每天就要收诊一名因吸食可卡因引发胸痛、心脏病发作、出现妄想、因神志不清而自伤的患者,患者身份既有15年药瘾的妓女,也有中年商务人士。英国从1993年开始记录可卡因吸食者的情况,那一年有11人死于过量吸食可卡因,到2006年仅英格兰和威尔士就有190人死于可卡因。他说:“我们生活在即时满意的时代。今天的人们有个荒谬的想法,认为我们有权拥有任何东西。可卡因恰恰告诉了你,只要你有钱,随时随地就能得到想要的东西。”
中产阶级成了可卡因主力军,连带出另一个问题:他们的雇主将为可卡因文化买单。据苏格兰政府反毒品办公室的调查,苏格兰10%~13%的可卡因使用者是专职员工,可卡因远远超过旷工,成为公司面临的第一大职场问题。上世纪90年代初,苏格兰的企业因员工滥用可卡因造成的医疗、安全、工作效率、旷工等损失每年达8亿英镑,现在超过了10亿英镑。2005年,苏格兰反毒品办公室出台了一份新的毒品监督规范,指导公司对他们怀疑的瘾君子做药检,在招聘新员工时应该筛掉有吸毒嫌疑的人。这一规范得到大公司的欢迎,在食品、运输业的反响尤其强烈。但是,药检要查血液和小便,这又引发了关于人权和隐私权的讨论。 可卡因毒品话题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