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东之:古陶的价值暂时还在一个低谷里
作者:朱文轶
( 唐白陶官 吏俑 )
我的收藏是从冷门入手
文学时代我们都是文学青年。写文章的同时,我也好些其他的,美术、收藏,这些兴趣也都比较浓。搞收藏和我的其他爱好都靠点边,它首先是从美术开始,文物首先是直接的美感对我构成了诱惑。
古陶特有的价值是必然的,虽然它目前在市场上和其他藏品相比还是价位偏低的领域。文物真正的价值跟市场评估价是两回事。市场价值最好的东西不见得有特别重要的文物价值,它是市场、社会和当下需求造成的一个结果。可以说近百年来,不是真正的收藏家、文物鉴赏家在主导这个市场,而是有钱人、能够消费得起它的人在主导它。一类东西的行情起来,是因为有人在买它,他能看懂这东西,能喜欢它。一些东西在他们能力之外,在市场猎奇的需求之外,就变得冷门了。收藏现在变成一个挺怪的行业,收藏的文化和传统的基础其实在五六十年代就已经被否定了,而它现在的兴起恢复又通过隐秘的消费流通方式,夹杂着经济膨胀后的财富彰显,因此当然在整个文物领域里,是那些更俗的、更靠近我们生活的东西价值先升起来。
以前玩古董的是贵族,有钱也有贵族文化的传承。但现在这个贵族式的传统没了。有钱的是商人,他们看中的是市场行情;能真正看得懂文物的,那些老先生们喜欢得要命,再喜欢也拿不出钱来,于是这些东西就变得寂寞。
我收藏的这个领域,陶靠近中国金石文化的风泥、瓦当、砖瓦,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和正宗,是在考古和文物上一个最重要领域,也是退后一百年或者再早当时的收藏家、学者、一些大家族最关心和看重,想要花重金去购买的。它们一直有价值,只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它们的价值被颠覆、淹没,并且现在还在一个低谷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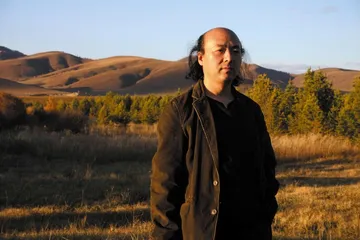 ( 路东之
)
( 路东之
)
20年前我收藏这些东西时,实际上就是从一个当时社会相对的冷门入手,它们价钱比较低,这也恰恰成全了我以一个穷学生的身份才有可能去占有这些东西。如果说我关心的这个领域当初就是热门,有钱人要是参与进来,那就根本轮不到我了。
在这个前提下,我出于自己的判断,出于内心喜爱,才一路走过来。所以我的收藏从头到尾不是投资行为,没有计算过,是一点一点花钱的。回头看,花的钱是很多,也不堪回首,不堪计算,但在当时花的都不是大数。现在很多收藏界人,是因为某个行业热门起来了,大家觉得这里面有重要的人物可能进入,投资也好、押宝也好,就有人花钱进来做。这和我涉足收藏的初衷不一样。另外,瓦当、古陶,这些年代较远的东西,从根上对我有诱惑力,对我来说,离我们生活越远,诱惑越大。我现在更痴心的是史前文明那段神话传说那些遗迹,它们离我们生活太远了。离我们近的东西对我诱惑力小,比如明清的东西,可能价值很大,但我的兴趣不在那儿。
 ( 战国 秦鹿蟒蟾 蜍纹瓦当 )
( 战国 秦鹿蟒蟾 蜍纹瓦当 )
现在我的博物馆展出的这部分藏品很多人已经很惊叹,但这只是我的一部分。当然一大部分是博物馆成立后汇集的。刚开馆,就是这个展厅,400平方米对一个私人收藏来说,还是挺奢侈的,但实际上很难装完我的东西。我的书房叫“梦斋”,也不大,当时已经像个文物库房一样放满了东西,我吃住就和这些古器挤在一起。有一次东方收藏家协会的雷耀方到我那儿看了后开玩笑说,“总算见识什么是真正的收藏家了”。
后来那个屋子的东西往博物馆拉的时候,一直拉不完,一次一次拉,怎么也清不完的感觉,直到博物馆开馆两年后,我那房间里还有一小部分东西没移过来。建馆前我收东西很繁杂,虽然那些东西的种类数目基本心里还是有个数,但是东放西放,整理的时候,实际的数量还是大大超出我自己的想象。我一直觉得这挺神奇。
 ( 战国奔虎纹瓦当 )
( 战国奔虎纹瓦当 )
其实说起来,收藏不是钱的问题,甚至不能用机会去说它,它真是缘分。只要你跟一件东西有缘分,它自然会找到你,你也自然会得到它。我自己是个挺典型的例子。从来没有人给我投资,我也没有产业。我从读书时候开始做这件事不可能有投资动机,一点一点花钱买,但是我用全部的资金做过来。我就那点钱,这点钱恰到好处够用,恰到好处使到够用的地方。我始终能用我仅有的一点钱,得到我想得到的东西,其实现在也是这样,到现在我也没有更多的东西,但我需要的东西还是往往可以得到。当然我也比较克制,好的收藏家只能专注一个专题领域,你不能贪心过大,你想得到天下宝贝怎么可能。
20年的收藏变迁
 ( 位于北京大观园北门的古陶文明博物馆 )
( 位于北京大观园北门的古陶文明博物馆 )
80年代早期,和许多人一样,我的收藏也从古钱币始,进而到其他古物和书画。我家当时住在西单辟才胡同,我买到的第一件书画作品是在北京长椿街,一个小伙子花5块钱进了一副篆书对联卖不出去,说是砸在手里了。看我有兴趣看,死乞白懒要“平推”,我当时只能拿出5块钱来。一会儿来了一堆卖画的,跟我游说,好像最贵的一幅画才35块钱,我觉得挺好,却是不敢再掏钱了。1986年春,朋友介绍西安的一个藏瓦大户乌金福来我家。乌金福送我一条朱拓汉字瓦当拓片,后来看我对文物有些研究,就掏出一直背在身上的汉绿釉陶罐。这是我第一次亲手接触到这么早的出土文物,里面的封土,外部的绿釉,像新的一样完美。这太让我着迷了。
很多人看过一些出土文物,包括看到我现在展厅里的一些文物,觉得太完美太干净了。民间的非专业人士往往认为,只有残破的才是出土文物的真品,其实这真是误解。当一件地下文物一直处于一个恒定的环境中时,它本就不应该有变化。对古陶器、汉瓦当这些分布于黄河流域沿岸地下的文物,黄土高原的水土是保存它们最好的恒定环境,真的是几千年就一瞬。它们刚刚从地下出土就是完美光鲜的。实际上,也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兴土木的年代,这种恒定才被破坏。
 ( 红陶神人首 )
( 红陶神人首 )
1987年,我到西安西北大学作家班读书,当时的西安就正处在这种环境的动荡中。学校的一排平房拆掉盖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工地上经常能找到残陶片瓦。我第一件真正的藏品是在那里找到的一块唐碑残石。上有三行六个字:第一行一字“有”,第二行两字“菩萨”,第三行三字“不住色”。“有菩萨不住色”,我就觉得我和这些古器有天然的缘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就一门心思收瓦当。
我收藏的起步肯定是和我在西安读书的背景有关。到现在,北京和西安之间我恐怕跑得不止百次了。我在那读书的时候,西安的收藏风气就不好,当然这和陕西作为文物大省的地位有关,即使有人家里有家传和私藏的宝贝,能公开自己收藏物品的人很少,所以合法和非法的文物拥有者都更倾向于把文物卖掉。相比之下,北京的收藏氛围要宽松很多,潘家园、琉璃厂的文物交易传统也很悠久,在80年代,河南、山东、陕西这些文物省份的文物向北京输出很多。
 ( 印章
)
( 印章
)
我回北京后,北京文物市场上的彩陶还很少,后来逐渐多起来,那些彩陶贩子到北京来卖,我可能是最早的主要的买家。我的大量收购,造成青海和甘肃的一些彩陶商就在北京常驻,常年做这生意了,人越来越多,最多时候有几十个人在北京专门做这事。当时懂这行的人还少,他们到北京一定要让我先开箱,先挑,别的客户买了之后往往也让我来看。这种情况维持了很多年,基本就是我在买,我一个人带动了北京的彩陶市场,影响了一帮人来跟着买,但都是些艺术家、书画家,不是为了投资的。
几年前在全国我的彩陶收藏量都是最大的,但现在恐怕不是了。这几年古陶价格虽然比不上像明清瓷器这类古玩,但也涨了不少。各地开始出现这么一个趋势:当地资本开始大量收购当地文物,疯狂买进,一些地方大商人都成为当地某些门类的大户了。瓦当,在西安很热门了,有一大群人在收藏,把价钱炒得很高。这样一来,好藏品从北京这些消费地向原来的文物输出地回流,最贵的瓦当珍品就会出现在西安,而唐三彩,北京的价格比起洛阳要便宜得多。
 ( 秦封泥——右丞相印 )
( 秦封泥——右丞相印 )
我个人的力量没法跟那些大企业家竞争,一些古陶器中的精美大器,图案出奇的器物,我已经买不起了。
任何文物,价格一涨,赝品马上就来。陶器的成本低,这直接造成了作伪的泛滥。80年代,那些送上门来的彩陶贩子的东西里,就参差不齐,真的掺些假的。现在就更疯狂了,一个是赝品多,还有一个是做得真好。但总的说,以我的逻辑,这种越原始的,越朴素的,离我们生活越远的,其实是越难以做假做得好做得像。就是因为它们离我们远,我们所能获得的信息太少。陶,一块风泥,一块瓦,它们简单到就和了个泥,压了个样,但是你做不到完美的,从我们收藏者来说,它们被辨伪的可能性更大。
出土文物的收藏困境
但总的说,与那些拍卖场上的“宠儿”相比,古陶这类远古文物的价值远没有被发掘。这一部分当然和我们国家文物政策对出土文物的重点监控有关。现在的文物法虽然肯定了个人拥有文物的可能性与合理性,你合法得来的,合法继承的,那就是合法的,过去没有这个东西,从法律上讲,你有就是不对的。但和其他文物比,出土文物的流通还是显得困难,大家有心理障碍。
我收藏的陶、砖、瓦是来源于遗址,它虽然是出土文物,但和墓葬没有关系,身世还会清白一些。比如说,铜镜,它是陪葬用的古文物,它必然是出土的,而且是墓葬出土。这样的项目,前两年开始,嘉德就拍了收藏家专场,文物局对此不太管。后来各个拍卖行就陆续拍,现在铜镜的流通就没人管了。这样一来,仅仅两三年功夫,铜镜的价值就涨得很高很快。铜镜过去是个不起眼项目,藏的人也不太多,价值也偏低,尤其普通铜镜值不了几个钱,就是因为它准许拍卖了,升了几十倍不止。彩陶、砖瓦准确地说,目前还是“有价无市”。
我们自己就是在那么一个复杂状态走过来的,当初也有各种各样的风险,有各种各样的争议。它本身是逆向行为。这个博物馆本身便是有争议的,它是中国第一批私立博物馆。1996年我们这批私人博物馆报批,北京市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最后批的,当时批了四家,其中一家后来没有开;一家是艺术家工作室性质,还不算文物;另一家是马未都的,是传世文物;只有我这一家是出土文物。真正跟政策相冲突的就是我们。当时私人占有出土文物并公开展出还是不可想象的。北京市文物局决定批,上面也比较关心,但很多专家,包括国家文物局的一些重要专家跟官员,他们都有看法,他们认为这种做法很冒进。好在后来的结果还说得过去。我的收藏确实汇集成了一个体系,这个体系足够成为我的一个框架,成为现在这个博物馆的本身,这个博物馆有了根本的立足点。我的藏品的学术价值应该说是民间收藏领域最高的。
新问题是我现在要拓展我的收藏,增进一些好藏品,在资金上确实有些难以为继。我还是要求助于市场。这才有了我拍卖98块“梦斋甲骨”事。这些甲骨文不是我博物馆名下的,是我恩师的藏品转给我,也有我零散的一些藏品,属于我私人收藏的一部分。文物局一开始也是不允许卖,说是上海的那批东西就不合法,就不能卖,说虽然已经卖了他们还打算追查,头一年没有允许。第二年我们继续跟他们去谈,那批东西的传序是有记载的,不存在违法问题,最后总算通过了。我们也没有宣传,结果,我们的底价是600万元,拍卖的最高报价是480万元,离底价还差120万元,还是流拍了。
路东之藏品的三大门类
彩陶
陶普遍被认为是融汇金木水火土全部要素的“五行之艺”,主要出土于甘肃、青海、河南等地。作为路东之最重要最丰富的藏品之一,他的藏品时间跨度很大,各时期的陶器代表作品都有收藏。而因为一些地方大面积基建工程的完工,古陶出土量锐减,加上近年来一些大户购进成批古陶的行为,使得器形大、造型好的古陶器在市场已经很少见到。古陶在文物市场上正日渐走俏。
瓦当
瓦当是指中国古代建筑上的一种构件,用于椽头,起遮挡风雨和装饰房檐的作用。它是文字、文学、美学、书法、雕塑、装潢、建筑等多门类综合共蕴的艺术,反映了丰富的自然景观、人文美学和政治经济内容。它是路东之最早涉足的收藏,也是全世界最完整最具影响力的瓦当收藏体系,1994年至1995年,路东之以一年时间,完成了《路东之藏战国秦汉瓦当原拓本》60部,此后每两年选择一个藏品系列作手拓本。
封泥
封泥是古人封缄文书、信件、货物时在封口处用来盖印的泥团,是印章最初的使用痕迹。自清末发现封泥以来,一度受到金石学家、收藏家的特殊珍爱,成为考古探微、补遗证史和研究古代印学与书法的绝好材料,成为继甲骨文、金文、简牍之后,金石学的又一重要成果。是路东之收藏中学术研究价值最高的藏品。1987年,路东之在西安一个农民家第一次见到封泥,最初是十来块,后来又要了十几块。此后,路东之的封泥藏品一直没有收获,直到1995年春天,他一次购入200多枚秦封泥。 路东文物博物馆低谷价值文化古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