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2.0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吴戈
 ( 莫桑比克的疟疾患者 )
( 莫桑比克的疟疾患者 )
美国《发现》杂志在2006年第12期上开始评选首届年度科学家奖。最终这家杂志只选了一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42岁的合成生物学家杰·基斯林,此人的研究即使在这些杰出人物中也举足轻重。这种研究在3年前刚刚被人称为合成生物学,其目标不仅是操纵单个基因,而是将很多基因组合起来,就像晶体管组成集成电路一样。
在此之前,遗传工程已经创造了奇迹,但只是把一个物种的部分基因延续、改变并转移至另一种。合成生物学则从最基本的要素开始,一步步制成零部件,用不同部件,设计和构建可以按预定方式存在的生命体。本质上,这是一个逆自然的过程。
即使最狂热的预言家也很难想象它的前景。人造DNA?还是实验室中有控制的进化?谁知道!唯一可以比拟的是,这就像指望60年代的计算机先驱们预测出后世的互联网和iPod一样。但与计算机根本不同的是,这扇大门后面不是一个虚拟世界,而是造物主的私人花园。“有一天,我们现在思考的事情将显得如此短视。”麻省理工学院的萨曼莎·萨顿说。
萨顿的人生转折发生在电气工程学位的第二年,当时她正在测试防抱死刹车。“总像缺少了什么。”她说:“我感到普通的工程并不是我想象的创造,实在找不到真正兴奋的地方。”内心的冲动使萨顿走出了不同寻常的一步:毕业后转向了生物学。现在,她正用基因和蛋白质而不是电线来组装“电路”,细菌细胞是“底盘”,被当作电路板和电池使用。当传统生物学家仍将细胞看成一个整体,竭力了解它微妙的细节时,萨顿和同事们却想去掉这种复杂,创造简单而神奇的细胞。
一砖一瓦
 ( Genentech公司的实验室 )
( Genentech公司的实验室 )
与计算机革命相比,今天的生物黑客最不利的一点是基础。“苹果电脑起步时,已经有很多商品电子零件。”麻省理工学院的合成生物学家德鲁·恩迪说。“沃兹不需要连电源都要从原料开始制造。”而这是商业遗传工程的现实。“过去完全是随便从自然界找点遗传物质,直接加以利用而已。”恩迪说。
实际上,“遗传工程”这个说法并不恰当。首先,他们最多的还是用大肠埃希氏菌大量制造需要的蛋白质,还常常发现借来的基因序列在习惯的环境以外水土不服。恩迪说,真正的工程师是根据预先的设计,制成能可靠运转的系统,“而遗传工程看上去一点也不像工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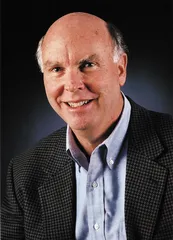 ( 克雷格·文特尔
)
( 克雷格·文特尔
)
所以,麻省理工学院的合成生物学家们将建立可靠的标准部件库作为初步目标之一。最简单的部件是一小段DNA,包括制造蛋白质的基因序列,以及控制基因活动的钥匙。还有复合部件,它们能构成简单的基因装置。目前,这个部件库已有167个基本部件和421个复合部件。虽然与电子部件的规模不可同日而语,但每年都有稳步推进,始于2003年的国际遗传工程机器竞赛已成为年度盛事,沃伊特的装置就是2004年的获奖作品,2006年的比赛吸引了全球39个队参加。
合成生物学家也在努力驯服他们的装置所寄居的细胞。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遗传学家弗雷德·布拉特纳培养出简化的大肠埃希氏菌,基因组少了约15%,但还有约3700个基因。莱特更青睐从佛罗里达的一种花里分离的初级微生物,这种花只有682个基因。现在,莱特正试图重构这种微生物的基因组。克雷格·文特尔也在全力探索生命所需的最小基因片段。
 ( 杰·基斯林 )
( 杰·基斯林 )
证明自己
合成生物学的第一个有趣成就出现在2005年11月的《自然》杂志上。加州大学的克里斯·沃伊特领导的小组把大肠埃希氏菌变成了活着的摄影胶片。他们将藻青菌感知光线的基因接到大肠埃希氏菌中,后者遇到红光就产生黑色素,成为一种老式但分辨率很高的摄影胶片。
更实用的成果出自杰·基斯林。2004年12月,比尔·盖茨夫妇基金会为他提供了4260万美元,希望通过合成生物学方法,大幅度降低抗疟疾药物的价格,拯救全球每年死于疟疾的约300万人。
80年代初,遗传工程刚刚走出实验室,少数公司开始尝试制造胰岛素、生长激素等产品。基斯林的博士学位选择了化学工程而不是生物。他猜测,在一个细胞里发生的事应该酷似一个化工厂:石油输进去,经过一整套反应,出来的是塑料。如果进入微生物细胞,使它变成制造药物的化学反应器,不光可以采用糖等便宜的原料,还能迅速扩大规模。
1992年,基斯林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到2002年研究已初见成效,还建立了世界第一个合成生物学系。他的方法可以制造薄荷醇,也可以制造β胡萝卜素,但直到偶然从一篇文章上获悉:治疗疟疾的特效药青蒿素来自苦艾植物,提取过程缓慢而昂贵,使它的价格是其他抗疟药的20倍。
虽然当时甚至不知道青蒿素是什么,但基斯林清楚:这是合成生物学的曙光。2003年,他们首次成功制成青蒿素的前体。2005年4月,他们已经将细菌、酵母和苦艾的基因合为一体,使酵母变成一个生产青蒿酸的化工厂,剩下的只需找到大规模生产的办法。在当月的《自然》杂志上,基斯林透露:可望2009年末投产青蒿素,届时成本将从1美元/克降低到10美分/克。
从计算机革命到合成生物革命
与传统的制药公司相比,Genentech等领先的生物技术公司也许已经是尖端,但在合成生物学家看来,它们与60年代的IBM公司并无二致。既然精于拼凑单个基因的Genentech一类企业也是一叶障目,合成生物学家们组成了自己的公司——“密码子装置”公司,曾经创办Celera公司、投资人类基因组排序的克雷格·文特尔也创办了合成遗传学公司。
今天,以技术挑战为本的“黑客”已经被和破坏者混为一谈,他们坚持的计算机的开放也被人利用。风险更大的合成生物学也可能给觊觎生物武器的破坏者提供方便的工具。目前最主要的担忧是基因合成,这意味着危险的病毒甚至细菌的DNA都能订制,而不断增加的基因合成服务公司难免唯利是图。2002年9月,《科学》杂志就报道了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埃卡德·温默小组人工合成天花病毒全基因组序列的消息。
2006年5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召开的合成生物学2.0会议上,研究者们签署了一个防范风险的行为规范,包括严格限制允许合成的病毒的范围,如果有客户计划危险的试验,基因合成公司应该报告。汤姆·莱特说:“对付危险技术有两个办法,一是技术保密,另一个是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快更好地完善,我的看法是只有用后者。”
对合成生物学的危险,基斯林的回答是:“如果我想做坏事,我可能不会选择生物学来做。这是相当复杂的。反过来,从一定程度上说,任何有水平知道怎样利用我们公开的这些生物部件的人,不管怎样都能做到。我们同时也在帮助防范者。”如果要控制什么样的人可以搞合成生物学,“也许就不会有便宜的抗疟药,也不会有这个领域所能带来的很多东西。”基斯林说。
合成生物学的可能性
2005年11月24日的《自然》杂志上,麻省理工学院的合成生物学小组用一部小喜剧来展示这个领域的难与易。比如细菌气球,只要能使细菌组成一个封闭的膜,然后开始产生氢气,不就行了吗?然而气球爆炸了,因为我们连如何让程序停止也不知道。剧中有这样的对话:
“看,我们正在制造东西。”
“你确信你对要做什么足够了解吗?你不想把事情搞砸吧?”
“只有试试才知道。”
试试的负面可能在1986年的美国经典恐怖片《变蝇人》里已让人胆战心惊。这部电影根据1958年同名经典恐怖片翻拍而成。一名致力于生物分解、组合的科学家用自己做实验时不幸变成半蝇半人的怪物,经历恐惧和疯狂后,他选择了自我毁灭。1989年的《变蝇人II》中,科学家留下的后代在出生时就吓死了母亲,被政府收养和研究。到一定年龄,苍蝇之子变身后与人类大战,威力有如超级跳蚤。
合成生物学的首批成果就是开关。2000年,波士顿大学物理学家杰姆·柯林斯开发了一种RNA核糖调控子。它能准确、高效地阻断或打开特定蛋白质的生产。这意味,通过修复细胞功能,消除肿瘤,刺激细胞生长,使某些决定性细胞再生,今后很多疾病由人体细胞内部就能解决。配有生物芯片的细胞机器人还能在动脉中游荡,检测并消除导致血栓的动脉粥样硬化病灶。
改造过的细菌可以分解杀虫剂、制造生物降解塑料,甚至处理核废料、探测化学和生物武器。它们也能将化合物中的氢原子释放出来,制造清洁燃料。文特尔已经着手研究能吸收二氧化碳,呼出大量甲烷的甲烷球菌。基斯林的下一个目标也是生物燃料。
还有一些人看到了未知的应用,比如生物计算机和其他今天由电子元件完成的任务。“我可以想象生物学和无机工程之间的某种结合。”哈佛大学的合成生物学家乔治·丘奇说。他认为:可以复制自己的简单半生物装置将是一个合理的初步目标,3年内就有可能实现。 生物技术科学科普生命合成生物学基因合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