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肃游戏”:本不必如此逼真
作者:曾焱 ( 哈伦·法罗基(摄于2009年)
)
( 哈伦·法罗基(摄于2009年)
)
哈伦·法罗基(Halun Farocki)的合作伙伴马蒂亚斯有一天给他寄来一张新闻剪报,里面有个小故事,提到美国军方正在使用电脑游戏治疗伊拉克战争中受过心理创伤的士兵。法罗基觉得有意思,或许可以从中延伸出来拍点什么。
他设法联系到两个美国军事基地:位于洛杉矶南部地区的二十九棕榈村海军基地和华盛顿附近的刘易斯堡陆军基地。为了获得拍摄许可,他各用了6个月时间来和两个基地分别沟通,过程艰难。不过到2009年进入拍摄后却变得非常顺利,他说:“我带了三四个人进去,10天拍完全部镜头。”
他从一家艺术机构总共拿到5万欧元赞助来完成这件作品,取名:《严肃游戏》(Serious Games)。这个名字让人联想到他最有传播度的另一件作品,以2006年世界杯决赛为主题的影像装置——《深度游戏》。但法罗基说,“严肃游戏”并非他自己创造的概念。“在游戏行业,他们通常将那种具有实际用途而并非仅供大众娱乐的软件称为‘严肃游戏’。”
影像装置《严肃游戏》目前正在柏林汉堡火车站美术馆展出。在德国,这座美术馆是展示当代艺术的一个著名场所。3月15日下午,哈伦·法罗基将它带到北京,由德国歌德学院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座谈会上放映了一场。
以他一贯的旁观的影像语言方式,法罗基记录了这个“战争与游戏”的当代案例:战前,美军运用电脑游戏对士兵进行模拟培训,战后心理治疗师同样通过运用电脑游戏复原战时环境来对士兵进行疗伤。这是一场电脑游戏的战争,还是现实战争的一部分?都是,好像又都不是。一如片名所暗示的,它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场“严肃游戏”。
 ( 哈伦·法罗基作品《严肃游戏》在奥地利布雷根茨美术馆展览 (2011年)
)
( 哈伦·法罗基作品《严肃游戏》在奥地利布雷根茨美术馆展览 (2011年)
)
围绕同一主题的四个章节各自独立,除第二部稍长为20分钟,其余都是8分钟短片。第一部《沃特森倒下了》在二十九棕榈村海军基地拍摄,据法罗基说,该基地位于一片沙漠中,和海湾战争或伊拉克战争的真实环境都十分相似。我们看到的影像为同屏双频呈现:屏幕的左半部分图像是电脑游戏里的战争模拟场景,右边是对正在训练室里操作电脑的士兵的现实记录。观众不得不同时出入现实和虚拟。在模拟画面中,一列装甲车队正行驶在阿富汗山区,枪炮的射程都按照真实情况来设计;训练室里,身处同一辆战车的四名士兵并排而坐,盯着前面电脑上显示的地形变化和突发状况——教官随时通过程序埋设地雷,或安放一个敌方狙击手。士兵们紧张的现场对话,从旁边另一屏幕滚动敲打出来。“我们镜头所拍摄到的那个小队遭到了伏击,车上的炮兵被狙击手击中。在画面上,他摔出了车外,一命呜呼。血肉模糊的士兵沃特森退出了游戏,一脸失望地瘫坐在了椅子上。”一如法罗基的描述,整个章节就在这个令人深感挫败的镜头上结束。
第二部《死了三个人》还是在二十九棕榈村基地,整个场景都根据电视画面在沙漠里模拟而成。美军的机动指挥中心用大集装箱组装在沙漠上方一块微微隆起的地势上,犹如电影布景。除了几十位海军士兵,还大约有300名阿富汗和伊拉克平民“参演”,他们和士兵套磁,排队领取食物,在炸弹突然爆炸后奔逃。这一幕,电脑虚拟混同于现实虚拟。在爆炸的巨大火球过后,影片戛然止于无声奔跑的身影。
( 艺术项目“关于劳动的长镜头”网站上的作品集结 )
第三部《沉浸感》开始讲述战后心理治疗师通过电脑游戏软件为士兵治疗战时创伤。法罗基说,2009年,他们为这个部分在华盛顿州西雅图市附近的刘易斯堡陆军基地拍摄了两天。20分钟时长,全部场景都发生在一个室内的治疗工作坊中。观众看到,几位非军方的心理治疗师正在向军方治疗师示范如何使用一款治疗游戏——“虚拟伊拉克”。这套模拟程序被他们简称为VI,作用是帮助患者提升和加强在造成自身恐惧的过往经历中的沉浸感。从法罗基的影像记录中我们目睹情节以角色扮演的方式推进:治疗师头戴耳机坐在电脑前,交替出场的士兵患者站立或坐在治疗师身旁,并佩戴了运行“虚拟伊拉克”程序的虚拟现实眼镜装备。程序仅两个场景:一辆行驶在沙漠公路中的装甲车,一个由集市、清真寺、露天广场、小巷和胡同组成的当地小镇,使用者可以驾车在其中随意行驶。整个导航过程由患者引导,治疗师则负责选择特定的事件:他将患者引入一场虚拟的伏击之中,或是让他们目击一次恐怖袭击。整个画面还可以根据需要搭配上不同的声音:直升机的轰鸣声、祷告声、爆炸声等等。法罗基说,这个项目针对的是那些因战争而留下心理创伤的现役和退役士兵,通过沉浸式交互治疗,他们将复述和再次体验过往经历中的关键场景。“在拍摄的第二天,我们目击了一场近乎完美的表演。一位扮演病人的平民治疗师讲述了一次在巴格达巡逻时的经历。这是他第一次外出巡逻,他被安排与一个叫琼斯的人搭档。他们的任务是清理街道,其实就是撕掉街道两侧的宣传海报。琼斯建议他们分开行动,一人负责道路一侧,虽然这违反规定,但他们还是这样办了。就当他进到一个院子中时,他听见了一声爆炸声。他出去一看——这时,他突然岔开了话题。扮演治疗师的那位治疗师打断了他,问他到底看到了什么?扮演患病士兵的治疗师回答说:‘当我走到那里的时候,我看到……他膝盖下面的部分都给炸没了。’说到这里,他整个人瘫坐在了椅子上。此后,他数次要求停止治疗,声称自己无法再继续下去,但治疗师仍然坚持继续。患者表现出犹豫,说话开始结巴,在讲述自己当时的想法和负疚感时显得有些语无伦次。”法罗基说,这位病人的表演是如此逼真,以至于尽管当时处在拍摄现场的旁观者事先都知道这是一场角色扮演,仍坚持相信,那位扮演士兵的治疗师一定是在叙述自己的过往经历。
“那位平民治疗师精湛的表演事出有因——因为他要推销这套程序,但整个场景其实本不必如此逼真。”
 ( 第二部《死了三个人》 图像
)
( 第二部《死了三个人》 图像
)
本不必如此逼真。也许这正是这部分影像的吸引和力量所在,萨特所说的“荒唐的战争”。作为旁观者,很难再像观看前两部时那样,清醒地区分现实场景和游戏场景。观众开始感到迷惑,并随着情节推进,不再确信于认知边界。对于那位扮演士兵的治疗师而言,他过于沉浸的表现让人联想到“路西法效应”——情境中的性格转换以及逐渐失控。“人和情境常常处于相互影响的状态,纵使认为自己拥有稳定一致的人格,也可能不是真的。”同样是扮演一名士兵的女治疗师,在游戏过程中,她被要求描述在虚拟情境中的所见及感受,很明显,她的声音传递出强烈的焦虑不安。她说出了这样一种感受:我进到里面了,我非常恐惧,我想要随便向什么人开两枪。
第四部《没有影子的太阳》是全部影像中最为平铺的部分,但法罗基通过双频方式提示了颇具意味——当然另一部分观众可能对此毫无感受——的细节:那一款训练游戏对环境的模拟十分逼真细致,包括太阳的阴影的落点。而在治疗游戏中,即便是同样场景,太阳却是没有影子的。“用于帮助回忆创伤经历的软件还稍微便宜一些。毕竟软件中的人和物都不会投下影子。”
 ( 第三部《沉浸感》 图像
)
( 第三部《沉浸感》 图像
)
在50岁以前,法罗基是作家、著名电影人,而20年之后,70岁的法罗基现在是德国最具关注度的当代影像艺术家之一:2007年,他携《深度游戏》参加第十二届卡塞尔文献展。2011至2012年,他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举办个展“战争的图像(从远处相望)”。在2013年威尼斯双年展上,作品《转播》代表德国参展。在1996年以前,他的作品主要是在影院和电视里放映,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由世界各地的著名美术馆或画廊空间来呈现。在一次访谈中,他曾坦率谈到这种变化的原因,某种程度上是来自受众人群的吸引:1993年,他拍摄了影片《关于一场革命的录像带》,在柏林两家影院上映,只有两名观众买票入场。但当他在2011年将影片带到纽约MOMA播放时,每天都吸引了数千人去排队。
法罗基生于一个叫新伊钦的捷克小城,在他出生的1944年,那里是纳粹德国占领区。1966到1968年,他进入西柏林的德国电影电视学院,此后拍摄了上百部电影,包括纪录片和剧情片。无论变换到哪种表达方式,法罗基都被认为是一个镜头冷静却深度敏感于画面关系的艺术家,“他的作品始终批判地看待活动的影像——这些影像所具有的意义、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是否对社会产生了本质性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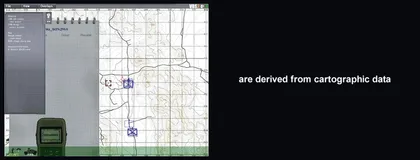 ( 第四部《没有影子的太阳》图像
)
( 第四部《没有影子的太阳》图像
)
在他那件著名的装置影像《深度游戏》(2007)中,法罗基将12块宽屏同时悬挂于一个展示空间,从不同视角“观看”2006年世界杯上法国和意大利的那场决赛:体育场上方天空颜色的渐变,来自保安部门的监控录像画面,在不同方向和不同时刻拍摄的球场镜头……所有画面元素在平行世界里各自发生又互为交错,活动中的每一个镜头都值得去捕捉和呈现,这是法罗基试图用影像为这个世界建构的一种深度关系。“在一块单屏的大银幕上,这些永无实现可能。”法罗基说。
三联生活周刊:你肯定听说了,导演史蒂夫·麦奎因刚以《为奴十二年》获得奥斯卡大奖。在这之前,他是一位著名的当代影像艺术家。而你,似乎和他走了一条相反的路,你放弃电影转向了当代影像。你曾说艺术空间比影院给予你更大自由度。什么是你所说的“自由度”?
 ( 哈伦·法罗基作品:《严肃游戏》第一部《沃特森倒下了》图像
)
( 哈伦·法罗基作品:《严肃游戏》第一部《沃特森倒下了》图像
)
法罗基:在创作时,我并不会刻意区分电影导演或艺术家这两种身份,区别只在于我使用什么媒介。说到自由度,其实主要是我无需再在拍摄前向人喋喋不休地解释自己要做什么。假设我用电视或电影媒介来完成一个像“严肃游戏”这样的主题,制作方可能会施加压力,要求我先在结构上描述一下战争本身,然后解释一下心理创伤的来由,历史上有什么不同的治疗方式……在电影制作环节里这些事情是无法避免的,这样会让我偏离自己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有人说,你很看重影像作品是否对社会产生“本质性的影响”。在你看来,何为“本质”?
法罗基:我不记得自己曾经这样说过。这么多年来,我其实更多的是想以不同方式反复切入某个同样的题材——不是说主题、理论有何不同,不同的是视角和入点。
三联生活周刊:简历上只介绍你1944年出生在捷克,1966年到西柏林上学。那这之间20多年,你的青少年时期在哪里度过?那段经历对你后来的艺术态度有多大影响?
法罗基:我父亲是印度人,移民到德国后做了外科医生。我出生后不久,全家就搬回印度生活了。当时印度正在内战中,我们四处流离,搬了七八次家,最后去到印度尼西亚。所以我最早学习的语言不是德语,其实是荷兰语。1953年,我随父母又回到德国,很幸运,当时这个国家正处在战后经济奇迹般飞升的黄金时期。我从莱茵省一个小镇搬到汉堡,现在生活在柏林。
三联生活周刊:这样说,虽然你总是被人介绍出生在捷克,但捷克文化其实对你并没有多少影响。
法罗基:对,我只是在那里出生,待了两个月而已。我更多的是以一个德国人的身份来看待事物,德国文化在我身上根深蒂固。像我姐姐,她还学习了一些印度语和伊斯兰文化,但我不同,已经完全被同化了。这些迁徙的经历给我的最大收获,可能是让我从中学会,以保持一定距离的局外人身份来看待这个世界。
三联生活周刊:可以说说你最近的创作状况吗?
法罗基:我自己最爱干的一件事就是坐在编辑台前,那是我的“创造力所在”(creative agency)。
但目前我正在世界各地做一个艺术项目——“关于劳动的长镜头”。从2011年起已经在15个不同城市举办,这让我接触到不同国家的很多艺术家。参与者以“劳动”为题,拍摄和制作时长为1分钟到2分钟的短片,但必须由一个长镜头构成。在中国,项目正在和歌德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合作开展。我并不关注参与的人是否有名气,比较有意思的是形成网络广度,可以讨论和分享。
(本文图片由歌德学院提供)(文 / 曾焱) 严肃游戏逼真如此不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