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未谋面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园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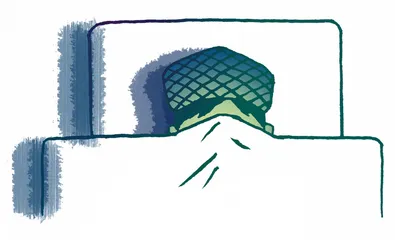
一直想讲讲他的故事,却因为从未见过而变得有些难以捉摸,不知如何下笔。是高还是矮,是胖还是瘦,是粗犷还是清秀,都一无所知,也永远不会有机会见到他。因为就在两年前的这时候,他已经安静地躺在了贵州某个小山村不起眼的小山坡上。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毫无疑问,我经常想起他的故事,尽管我们的交集只是仅有的两次擦肩而过。
第一次,是我和森同学结婚的前一年,我们在中秋节假期从杭州去江苏一个叫盛泽的地方玩。那是一个纺织重镇,有着无数的织布机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者。那时森同学的不少亲戚、邻居、老乡等分布在那里不同的厂区,做着各种各样的工种。由于他们平常几乎没有假期,所以中秋节我们特意过去看他们,从杭州出发也不是很远。大家相聚非常欢乐,那种普通的、平凡的、很容易满足的快乐至今让我特别怀念。只是第二天,森同学的堂弟收到了一个消息:森同学的邻居,一个在农村看来可能已是大龄未婚男青年的老乡,在前两天发生了车祸,骑着自行车与一辆摩托车相撞,头部着地,伤势严重。大家立即相约去医院看他,我也跟着森同学一起去了。
他躺在重症监护室,不是所有人都能见到。刚好赶上一个探望时间点,只能在一群人中挑选几位代表进去。当然基本都是他的亲人,森同学可能因为读的书稍微多一点,也被选为代表和他的亲人们一起进去了。我在外面和大家静静地等待。还有几位没能进去的他的亲人,在默默地抹眼泪。
探望的人出来后,乡亲们围上去询问情况,说是头绑着绷带,还没能醒来。至于什么时候能醒来,就要看他自己了。所有的人神色凝重,森同学打破沉默问起摩托车司机的情况,他弟弟说是个本地年纪较大的人,身体没事,但家里经济情况也不好。当时的医疗费还是他哥哥所在的工厂厂长暂时垫付的。大家都有些黯然,却也没有能力帮上大忙。我和森同学因为次日就要返杭上班,也只好和其他乡亲一样,塞给他弟弟一点小心意,就离开了。
让人高兴的是,不久后传来了他醒来的消息,意识、神智都还有。只是头部已受损伤,不能再上班,几个月后被家人接回贵州老家休养去了。从此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不再有他的消息,也认为他应该能基本恢复,渐渐便也遗忘了这件事。
中间森同学回过老家一趟,去看望过他,说是恢复得一般,头部还有个小凹陷,走起路来略显怪异。还说真是可惜了,本来他人长得不错,比较聪明,特别是毛笔字写得很好,以前村里过年不少春联都是出自他的手笔。这个说法我后来在森同学的二哥那里得到了印证。
那是一年之后,我和森同学于正月初八在老家办结婚酒。差不多办好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位邻居已于正月初三喝农药自杀了。由于是年轻人,按规矩,三天后就上山了,也就是说,初六左右他就安静地躺在了家乡的小山坡上了。二嫂说他真是一个聪明的孩子,连死也知道不妨碍别人家的喜事儿。我当时就震惊了,也不知道该做什么表情和如何表达。二嫂继续说,他是因为自己再也不能恢复到以前的样子而想不开的,好像是过年期间去外面玩,反应有点慢,他感觉到了别人有点异样的眼光吧。二哥在旁边补充说,他曾经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长得也不赖,有一个女孩子等了他好多年,在他休养期间,还曾拎着鸡来看他,愿意继续等他,可没想到,他却突然钻了牛角尖。唉!
我是一个不讲究忌讳的人,只是他这样的离开,让我突然有一种特别的悲凉。尽管从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却在他两次处在生死之间时,我与他擦肩而过。一个鲜活的生命,那么轻易地被一场自行车与摩托车的车祸而改变并消失了。痕迹那么的短,那么的淡,而他的亲人们承受的痛苦却是那么的重、那么的凉。我们在酒席办好临回杭州时,他的父亲也在场送我们,我握住他冰凉无助的手,企图用我的手传递一点温暖与安慰。他似乎也明白我的意图,紧紧握着我的手,只是他眼睛里充满了迷茫:“你说,我们喂饭接尿地把他救回来,他怎么能说走就走了呢?”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噎住了。或许,他有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他需要解脱,而这,我不能跟老人家说。
如今,已经过去两年了。但我有时还是会想起这位聪明、好看,并能写一手漂亮毛笔字的布依族小伙子。听说他的父母如今更加深居简出了,没有了以前的笑容与生机。 素未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