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无不胜的论辩术
作者:薛巍(文 / 薛巍)
 ( 梅森·皮里 )
( 梅森·皮里 )
学点谬误的专有名词
正确的论证都是相似的,而错误的论证却各有各的不同。所以,错误论证即谬误都很有趣。比如“没有杂工是面包师傅,也没有面包师傅是渔夫,所以没有杂工是渔夫”。这个有趣的例子暴露了一个问题:一些错误的谬误显得很不自然,因为逻辑学研究所有可能的推理形式,但其中一些在日常语言中几乎不会出现。比如“有些澳洲人是有趣的家伙,有些赌徒不是有趣的家伙,所以有些澳洲人不是赌徒”。
美国逻辑学家梅森·皮里所著《笨蛋!重要的是逻辑!》的第一章介绍了11种形式谬误,基本上都跟三段论有关,如错误换位、不当周延。其中可能唯有四词谬误还算跟生活比较接近。我们知道,大小、高矮等关系是可传递的,甲比乙高,乙比丙高,甲就一定比丙高,但有些关系是非传递性的,比如朋友关系和父子关系。“中国对法国友好,而法国对美国友好,所以中国一定也对美国友好。”“约翰是彼得的父亲,而彼得是保罗的父亲,所以约翰是保罗的父亲。”这样推理都是错误的,具体错在哪里呢?逻辑学家会说,标准的三段论要求中词在两个前提中重复出现,而在结论中消失。如果中词第二次没重复,而是变成另一个词就不对了,比如“约翰在彼得右边,而彼得在保罗右边,所以约翰在保罗的右边”,此结论并不有效成立,他们可能围坐在圆桌边,错就错在前一句中有“彼得右边”,后一句只有“彼得”。
皮里给他介绍的所有谬误都附上了英文或拉丁文的专有名词,他说这些名词非常值得学习,“因为当你的对手被这些拉丁文的专有名词责难时,听起来就好像他得了一种罕见的热带疾病,这会让那些责难看起来博学多闻且具有额外的权威感”,比如“复合问句”(Plurium Interrogationum)、“滥用类比”(Analogical Fallcy)等。有些谬误的名字很生动,如“红鲱鱼”(转移话题)、“稻草人”(夸大对手的立场)、“井中投毒”(人身攻击)。
皮里说:“逻辑谬误有持久的魅力,而且已经被研究了2500年之久。”但“诉诸石头”只有200多年的历史。它源自约翰逊博士对唯心主义者巴克莱的反驳:巴克莱说“存在即被感知”,约翰逊用脚踢石头来反驳他。在逻辑学家看来,约翰逊博士这么做是无效的:他完全忽略对手的整个论证,拒绝讨论其核心主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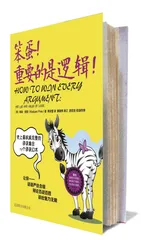 ( 《笨蛋!重要的是逻辑!》 )
( 《笨蛋!重要的是逻辑!》 )
谬误之所以产生,要么是因为人们忽略了逻辑推理、证据的性质,或是如何辨识相关的信息,要么是因为有人故意用谬误来骗人,对这类人去指出他们的谬误是没用的,只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所以皮里说:“这本书就是为辩论的输家而写的,它更像一个武器,它将教大家如何有效地辩论,哪怕偶尔使用诈术。了解谬误,一方面能让你识破他人的谬误,从而帮助你防止别人用谬误攻击你;另一方面,灵巧地使用这些谬误可以让你战无不胜,赢得每一场辩论。”
有意使用谬误的包括哲学家和广告策划人。“重新定义是哲学家最爱用的求助方式之一。当曲棍球偶尔射在门柱上而非优雅地进入网中,哲学家们便有可能会去重新定立这些门柱,将它们摆在稍微不同的位置,以使球不会击到门柱。大多数神谕和保险代理商常常使用模糊调和话术。”
有一种很强大的、错综复杂的推理叫两难推理,比如,一位希腊母亲告诉她政治生涯踌躇不前的儿子:“别做了。如果你说实话,人们会恨你;如果你说谎话,神会恨你。当你必须选择说实话或谎话时,你必定会被人们或神憎恨。”皮里说,其实很多两难困境都是虚假的,都是伪两难推理,在许多情况下,所提供的信息是错误的,选项也不止两个。比如,那位希腊母亲的儿子可以否定相关的后果,宣称这个两难困境是虚假的。他可以否认如果他说了实话,人们会厌恶他,他可以说因为他说了实话人们会尊敬他。他还可以有时说实话,有时说谎话。
处理两难困境的第三个方法就是去驳斥它,“用和原本元素相同的元素,制造一头同样凶猛的野兽,在对立面迎头攻击”。在前面的例子中,那个年轻人可以回答:“母亲,我应该从政。如果我说谎话,人们会爱我;如果我说实话,神会爱我。当我必须选择说实话还是说谎话时,我要选择被人们爱还是被神爱。”
皮里给了一个练习题:“如果我们允许在这个地区给问题青年们开一间旅馆,那么这个旅馆要么是空的,要么是满的。如果是空的,将会造成金钱的浪费;如果是满的,则会给地方带来许多麻烦制造者,让地方难以应对。”同样地,这一伪两难推理也有三种应对方法,最厉害的应该是:“这个旅馆如果是空的,就不会给地方带来任何麻烦;如果是满的,则能有不少金钱收获。”
丐辞、不相干的幽默、失控的火车……
你是否曾经突然想到一个好主意,然后觉得难以置信:这样的主意怎么之前没人想到?这时你要小心“非预期”谬误了:认为凡是值得做的事情,都已经被做过了。
合成谬误认为,对某个类别中的个体成立的事实,对整个类别也成立。但团队是一个不同的整体,它可能具备其中每个个体都不具备的性质。当把整体团队当成个体,就会导致谬误。比如:“如果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可以照顾自己,那我们的社会就可以照顾自己。”(这会变成人人都能自己照顾自己的社会,然而,也许社会还有需要被人照顾的其他方面。)
跟合成谬误相对的是分称谬误,某些事情只有在某个团体被当作整体时才会成立,如果把它归于这个团体中的个体,这就会造成分称谬误。如:“冰岛人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民族。这意味着比约克必定比其他流行歌手更古老。”
丐辞:把尚待证明的结论预先包含在前提之中,只要你承认了那前提,你自然不能不承认那结论了,其本质是“因为我是对的,所以我是对的”。比如:“英国政府应该禁止把康斯塔伯的画卖给美国的博物馆,因为英国政府应该禁止所有艺术品输出。”
不相干的幽默:使用与主题不相干却诙谐有趣的材料,以转移对论证的注意力,便犯了不相干的幽默谬误。在政见发表会上质问起哄的人,就是这种谬误的典型。他们用更有趣、更智慧的理由,掩盖所有合理的论证。问:“你了解农业吗?猪有几个脚指头?”南希·艾丝特:“你何不脱掉你的鞋数数看就知道了?”一个宗教教派的发言人,时常邀请听众提供与他见解不同的《圣经》引文,当听众一如往常地回答时,他总会如此反应:这听起来就像是吉尼斯(Guinesses)而不是《创世记》(Genesis)。卫博福主教跟赫胥黎辩论进化论时问赫胥黎:“你说你是猴子的后代,到底是你的祖父还是祖母是从猴子变来的?”赫胥黎也不示弱,他说从猴子演化成人并不可耻,但如果我有一位祖父跟你一样聪明睿智、权势显赫,却只会用这些轻浮的话来嘲笑严肃的科学,那我宁可要猴子当我的祖父。
失控的火车:当用来支持某个行为过程的论证,同时也支持更多的行为过程,就犯了“失控的火车”谬误。把高速公路限速从时速70英里降低至60英里,就能拯救生命,这可能是真的,但不足以构成限速60英里的理由,因为把时速降到50英里、40英里能拯救更多的人。如果单单只是以拯救生命为目标,限速0英里不就可以救助更多的人吗?我们很多日常活动都具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以冒险为代价来换取便利和舒适。如果仅仅因为拯救人命而设下60英里的时速,论述者必须提出其他理由,否则他论证的“失控火车”会把他带到50英里、40英里直到0英里。再比如,应该禁烟,因为在全民医疗制度下,吸烟者治病的费用会由他人负担。这也是一个“失控的火车”,为什么要停在那里?同样的论证也适用于其他严重影响健康的行为,如摄入过量黄油或白砂糖。
类推谬误:假设几件事情在某一方面相似的话,则在其他方面也相似。当我们在已经确认的事物的基础上,进一步假设未来事物的相似性,就会产生类推谬误。比喻可能为我们暗示质问的线索,却无法作为建立新发现的基础。在休谟的《自然宗教对话录》中,克瑞安提斯把宇宙比作精巧的钟表,从而推论出钟表匠的存在,斐罗说对他而言宇宙更像包心菜,从而扼杀了前者的论证。
复合问句:当好几个问题被合为一个,要求回答“是”或“否”,被问到的人无法将问题分开回应,这就产生复合问句的谬误。如:“你是否已经停止打老婆了?”“你的愚蠢是天生的吗?”这些问题都还有一个附带肯定答案的假设,正是这些假设给回答者带来了麻烦。有些大人用这些来难为小孩:“你是现在就去睡觉,还是等你喝了牛奶之后睡?”“你想把你的积木收到盒子里还是放在架子上?”但10年之后,家长便会得到报应,孩子会问:“你是给我买一个迪斯科游戏板还是一个摩托车当我的生日礼物?” 逻辑谬误论辩战无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