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的网络算法与现实选择
作者:王星(文 / 王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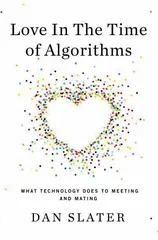 ( 丹·斯莱特和他2013年出版的新书《算法时代的爱情》 )
( 丹·斯莱特和他2013年出版的新书《算法时代的爱情》 )
雅各布的故事
雅各布在美国东海岸读了几年大学,然后在各处转悠了几年,最后搬回了家乡俄勒冈州,在波特兰(Portland)定居。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很难结识女性朋友。他之前在纽约和波士顿地区居住过,已习惯于遍地约会的社交情景。但在波特兰,他的多数朋友都已经形成长久的情侣关系,他们一般在大学相识,而且大多已经开始考虑婚姻。
雅各布单身了两年,26岁时,他开始与一个年龄比他略大的女性约会并很快住在一起。女朋友看起来很独立,交往的成本不高,这对雅各布来说很有诱惑力。雅各布之前的女朋友都抱怨过他的生活方式:太沉迷于运动赛事、音乐会和泡酒吧。雅各布被描述为:懒散,没有目标,缺乏金钱概念。
不久,雅各布的新女友也产生了类似的感觉。雅各布自怨自艾说:“我无法让一个女人感觉到她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她们总是说‘真希望我和篮球赛或音乐会一样重要’。”雅各布是家里的独子,他倾向于通过交换付出来维持关系,比如:如果女朋友能跟他一起看比赛,他就陪女朋友去郊游。这样的交换令雅各布总是很被动,但不管他们的关系中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雅各布说服自己,这样总比再次单身好。然而,5年后,女朋友还是离他而去了。
弃儿的故事至此结束,下面雅各布就要走王子运了。雅各布是丹·斯莱特(Dan Slater)2013年1月的新书《算法时代的爱情》(Love in the Time of Algorithms)中的人物之一。斯莱特曾经做过诉讼律师,后来成为《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男性健康》、《GQ》等报刊的专栏作家。在为宣传自己的新书所写的专栏文章中,斯莱特先介绍了这个他认为具代表性的采访对象,在真实原型基础上使用了化名。然而,许多读者却质疑这个人物是纯粹虚构的,因为他们认为,雅各布后半段的王子故事实在不可信。
斯莱特的新书副标题是“科技如何改变了交往”(What Technology Does to Meeting and Mating)。这是雅各布的王子运的契机——分手后不久,他注册了两个约会网站:一个是付费的Mach.com,他在电视广告里看到过;另一个是免费的Plenty of Fish,他在城里听说的。于是,雅各布转运了。
斯莱特描写说,雅各布对他回忆:“难以置信,我是个长相很普通的人,忽然之间我开始每周和一两个非常漂亮、富于激情的女子分别约会一两次。一开始我以为自己撞了狗屎运。”
 ( 2003年2月14日,印度孟买一家网站的员工(右)正帮助一位女士参加一个网上配对活动 )
( 2003年2月14日,印度孟买一家网站的员工(右)正帮助一位女士参加一个网上配对活动 )
6个星期后,雅各布遇到了22岁的蕾切尔:“我在几个网站注册后就发现了她,当时我只与几个人约会过。”雅各布说,蕾切尔既年轻又漂亮,还说她的年轻和美貌让他振奋,朋友们都很嫉妒他。更让雅各布满意的是,蕾切尔不介意雅各布对运动着迷,而且喜欢与他一起去听音乐会。约会了几个月后,蕾切尔搬来与雅各布同住了。雅各布认为这次找到了真命公主,然而,两年后,蕾切尔说她要搬出去,这次是雅各布松散的金钱观念触了礁。
斯莱特说,雅各布在过去是那种难以与女朋友彻底决裂的人,然而,这次不同了。雅各布说:“我感觉约会网站使我发生了一些重大的改变,我原来把找朋友看作艰巨的挑战,现在我对感情更加放松、更有信心。”在蕾切尔搬出去的当天,他登陆了Match.com。他的个人简介还在,还有一些不知情的人发送试探信息过来。在他没登陆的两年,约会网站做了改善,网页更加时尚、网速更快。波特兰市的网上约会人数也增加了三倍,雅各布从没有想象过这么多的单身人群在等待约会。雅各布告诉斯莱特:“我敢说,如果我是在现实中遇到蕾切尔,如果我从未使用过约会网站,95%的可能性我已经和蕾切尔结婚了。我会忽视其他的一切,努力让这场感情继续下去。网上交友改变了我对永恒的感觉么?毫无疑问。当我感到分手势在必行,我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哀叹自己注定要孤独。相反,我盼望着去看看外面有谁在等我。”
 ( 2012年2月7日,美国小伙史密斯(左)与通过网络结识的女子参加一个速配活动,两人的谈话有些尴尬 )
( 2012年2月7日,美国小伙史密斯(左)与通过网络结识的女子参加一个速配活动,两人的谈话有些尴尬 )
于是,蕾切尔离开后,雅各布与很多女性通过网络约会。有些喜欢与他看篮球赛和音乐会,有些喜欢在酒吧喝酒。他一度看上了在同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律师助手和律师,同时还另有一个理疗师、一个药剂师和一个厨师。他和其中的三个人在第一或第二次约会后就发生了关系,同另外两人的关系也正走向较为亲密的身体接触。雅各布告诉斯莱特,他最喜欢那个药剂师,认为她会是一位理想的女朋友,问题是她在身体接触方面进展缓慢。雅各布两年前还在担心自己被弃,这次却开始担心相反的事:有那么多可以选择的替代者,自己可能没有耐心等待。一天晚上,那个律师助理向雅各布倾诉:她与前男友的关系相处不融洽,但是雅各布给了她希望,她唯一需要的就是诚实。多情王子雅各布想:噢,我的天哪!
斯莱特说雅各布想成为一个好人,但雅各布也知道自己早晚有一天会被当作一个混蛋。事情到了后来,已经很像一场随意的探雷游戏。雅各布最喜欢的球队是Green Bay Packers,在最后一次与斯莱特的谈话中,雅各布说,最近他一直尝试用“Packers球迷”作为关键词在OK Cupid网站(另一家免费约会网站)上搜索伴侣。借助OK Cupid的“本地”应用,雅各布现在可以广播他的位置和他所期望的活动,工蜂一般忙碌于和女人的约会中。一天晚上雅各布正独自喝啤酒,街对面的酒吧里有个女人广播寻找卡拉OK伙伴,雅各布回应了她,并和她一起度过那个夜晚,但此后两人再没有说过话。
 ( 英国人劳伦斯和他的泰籍妻子在英格兰他们经营的乐器店里。除了经营乐器,他们还通过互联网为顾客挑选泰国籍的新娘 )
( 英国人劳伦斯和他的泰籍妻子在英格兰他们经营的乐器店里。除了经营乐器,他们还通过互联网为顾客挑选泰国籍的新娘 )
斯莱特引用社会学家的理论说,所有的交往策略(Mating Strategy)都要付出代价,不管是名誉损坏还是错失可替代伴侣。雅各布注意到,他和朋友见面少了,朋友们的妻子们也厌倦了和他新交的女朋友相处,由着雅各布从一个女人身边换到另一个女人裙下。与此同时,雅各布也发现:随着时间推移,他对新的约会已经感觉不再那么兴奋了。他于是自忖:“是我老了,还是网络约会的问题?”
变成多情王子后的雅各布最后留给斯莱特的话是:“每一段关系都是一堂课,你会更了解什么有用、什么没用,你真正需要什么,你可以不要什么。这感觉起来是一个有益的过程。我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和错误的人一头扎进一段关系中,或过早承诺什么。但是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呢?从什么时候起这种学习曲线变成了不想投入精力维持感情的借口?也许我现在有信心去追求我真正想要的人,但我担心自己已经无法感受爱情。”
 ( 牙医莫伊伦与妻子温的合影。他们俩就是通过劳伦斯夫妇介绍认识的 )
( 牙医莫伊伦与妻子温的合影。他们俩就是通过劳伦斯夫妇介绍认识的 )
斯莱特希望用雅各布的故事说明这样一个假说:“当我们可以很安全、很容易地找到另一个合适的人时,那种关于承诺的古老的想法就会受到猛烈的冲击。”
斯莱特质疑:“网上约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互联网使单身者更容易与适合自己的单身人群碰面,组建成他们认为好的情侣关系。但是,如果网上约会使寻求者遇见新伴侣太容易了呢?如果良好关系的标准太高了呢?如果我们总是追逐伴侣的模糊替代人选,那么,点击鼠标寻找永远更兼容的伴侣是否会意味着未来彼此关系的不稳定?”
斯莱特进而引用研究人际关系学的心理学家的说法,指出有三个因素决定了“承诺”(Commitment)的强度:对这段关系的投入成本(包括时间、努力、共同的经历、情感等),对关系的整体满意度,可替代伴侣的质量。其中后两个因素很容易受到互联网所提供的巨大交友圈子的直接影响。网上约会的核心就是一连串的替代伴侣。有证据表明,当出现对现有伴侣与其他可替代伴侣比较的诉求时,这正是对该伴侣做出低承诺的明显预兆。
雅各布与三个约会对象在第一或第二次见面后就发生了关系,故事中的这个细节似乎也验证了斯莱特的担忧。随着网上约会日益盛行,旧的短期交往策略将让位于新的。人们寻求承诺,女性更是如此,人们还为此发展了种种策略来检测欺骗、捍卫承诺。女性会通过在性问题上有所保留来评估对方的意图:女方的矜持理论上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我并不想随便和什么家伙睡觉”;男方表示愿意等待也理论上传达了回应的信息,“我感兴趣的不止是性”。然而,在雅各布的故事中,以网络约会为代表的科技发展步伐却颠覆了这些交往策略。雅各布发现,在网上发展起来的情侣关系进展速度很快,他将这种“速熟”归结为两个原因:首先,在互发信息或电话联系的阶段,双方就建立起了熟悉度;其次,如果一名女性在约会网站注册,这个行为本身就说明她渴望联系。在雅各布看来,网上约会与在现实约会的最关键区别在于紧迫感(Sense of Urgency):“我们没有时间游戏。或者‘试一下’,或者‘再见’。”
忧心忡忡的斯莱特却没有得到美国读者的热情回应。在质疑雅各布只是为验证斯莱特的假说而虚构的人物的声音中,最具地域色彩的说法是认为斯莱特选错了样本采集地。《大西洋月刊》的助理编辑乔丹·怀斯曼(Jordan Weissmann)就认为,波特兰完全是个例外:“根据美国人口普查,超过33%的居住在波特兰的女性拥有至少大学本科的学历,这一数字超过同学历的当地男性,与纽约完全相反。”怀斯曼继而引证1983年古藤塔格(Marcia Guttentag)与赛克德(Robert Secord)的理论:“在女性过度教育的群体中,男性会更为滥情;在男性过度教育的群体中,女性会更加忠诚。”怀斯曼的论辩甚至超越了国界:“对117个国家的实证分析中,上述理论似乎都得到证实。男性比例高的发展中国家有较低的离婚率,而且罕有私生子现象。在20世纪初的美国移民社区,当男性比例上升,男女的结婚率都会提高。在当今美国,学者发现,女大学生很难有男朋友或进行传统约会,她们大多对校园男性的感觉很差。有趣的是,对中国的研究发现:在男性较多的社群中,女性反倒更有可能发生婚外性关系。”
罗彻斯特大学临床和社会科学系教授哈瑞·莱斯(Harry Reis)从实证方面质疑莱斯特的观点:“网络约会始自于1995年,也即Match.com初次出现时。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2006年的统计数据,它很快成为美国最主要的交往途径,超过20%的美国人是通过网络开始交往的。当时没有学者留意过相关的断交或离婚比率,尽管当时人们决定结婚的年龄和现在一样晚,但结婚的概率看起来与1995年并没有多少不同。我希望看到能够证实互联网在超越浏览新闻与收发邮件功能之后,改变人们‘承诺’意愿的更硬性数据证据。”
美国成人娱乐网站Fleshbot编辑勒克斯·阿尔普特劳姆(Lux Alptraum)的意见倒更为务实,她的评论文章名为《网络约会让我期待承诺,而不是回避》。她在文章中说:“我开始网络约会的理由很平常,可以用‘焦虑性人格’来解释,简单说就是‘酒吧只是喝酒的地方’。我从来不觉得在酒吧结识陌生人很自在,与朋友的朋友谈朋友在我看来也很别扭……我对网络交友的看法遵循一个既定的规律:在某些场合下,我的意思是,我刚结束了某段关系或有兴趣尝鲜时,我觉得会很感兴趣。浏览不同人的自我介绍,就像打量不同的自己有兴趣打发一夜光阴、但未必把他当作未来的伴侣一样。兴趣来了时,我会安排很多约会,打发掉我每一个空闲的晚上。在某个我特别有目标的时期,我会把6天压缩成4天,虽然那样对于我来说也有些过分……在兴致最高的时候,我带着最好的希望去赴约,更多的情况下,我不过是自娱自乐,通常不会有第二次约会。网络约会也许能帮你找到分享你日常爱好的、有吸引力的单身伴侣,但不会确保长期的深层次联系。而且不久我就会发现自己开始厌倦,因为觉得越来越难与同一个不可能继续发展下去的陌生人再产生真正的共鸣。与雅各布不同,约会次数越多,我越期盼真正的相知,越渴望找到某个我真正全身心喜欢的人,以便摆脱这种无穷无尽的令人疲惫的初次约会。”
约会网站的算盘
无论网外游离的男男女女如何申辩,斯莱特提出的假说根基在于那些约会网站。丹·温彻斯特(Dan Winchester)是英国一家免费约会网站的建立者,他预测:“未来会有更好的情侣关系,但是离婚率也会上升。作为男人,你的年纪越大,经验就越丰富,你知道该如何和女人相处,如何和女人对话。这些影响都会带到网络交友上来。我经常会想,网络交友让人们如此容易地找到适合自己的人,这个过程又是那么愉悦,婚姻是否会因此而被废弃?”
斯莱特承认:“当然,没有人确切地知道有多少伴侣关系是由网络交友平台制造的。”但他继而强调:“但在我的新书《算法时代的爱情》的写作过程中,我所采访过的大多数约会网站的高管都同意调查数据中所表明的:网上约会的崛起意味着‘承诺’的总体下降。”
曾经出现在雅各布的故事中的Match.com的母公司CEO格雷格·布莱特(Greg Blatt)说:“从历史的角度看,情侣关系总是被认为是困难的,因为,情侣关系的最终目标就是承诺。你可以说网上约会只是简单改变了人们对于‘承诺’本身是一种生活价值的看法。”伴侣的缺乏也在人们的决定中起了重要作用。布莱特是一个40来岁的单身汉:“如果我住在爱荷华,我可能已经结婚并有4个孩子了,而在曼哈顿就很正常。”
Badoo是一种会面与约会应用软件,全世界约有2500万用户。Badoo的社交媒体市场总监尼福麦(Niccolò Formai)说:“我认为,总体看,生活变得越来越现实,离婚率会上升。想想网络上的其他内容板块,比如股票行情和新闻。网络存在的目标就是使它们更加快捷,约会也会发生类似的改变。和新朋友见面是令人兴奋的,更不用说那些和爱情无关的好处。在互联网上找个工作、找个合租公寓的人,久而久之你就会融入到这股洪流中来。人们总说对稳定性的渴求会让‘承诺’得以延续下来,但这种想法的基础是人们都生活在一个无法结识很多人的世界里。”
 ( 1月5日,在美国太阳城,98岁的唐纳德在舞曲结束时亲吻妻子玛琳。与他们共舞的还有单身或丧偶的老人,约会网站为他们提供了温和的交友氛围 )
( 1月5日,在美国太阳城,98岁的唐纳德在舞曲结束时亲吻妻子玛琳。与他们共舞的还有单身或丧偶的老人,约会网站为他们提供了温和的交友氛围 )
诺埃尔·比德曼(Noel Biderman)是Ashley Madison公司的创始人。该公司自称“为谨慎人士提供邂逅服务的领先网站”,说白了也就是“世界顶尖偷情约会服务网站”。比德曼说:“社会价值观总是被首先放弃的。婚前性行为曾经被视为禁忌,所以女性容易遭受痛苦的婚姻,因为她们不知道自己还可以有更好的选择。但是今天,更多的人尝试过失败的交往过程,他们从失败的关系中恢复过来,继续生活,最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人们意识到:幸福很多时候正是因为曾经有过失败。当人们发现自己有能力更安全、更自信地去找到另一个更适合自己的伴侣时,传统的关于‘承诺’的想法将受到十分严峻的考验。”
在约会网站中,eHarmony是最保守的之一,最终达成婚姻和承诺似乎是唯一可以接受的目标。即便如此,该网站的关系心理学家贾姆·贡扎加(Gian Gonzaga)也承认,“承诺”和科技之间存在不协调处:“你可能会说网上交友允许人们开始一段恋爱关系,学到一些东西,最终可以做出更好的选择。但你也很容易发现,网上约会将使人们在刚刚感到挫折之时就轻易离开,‘承诺’的价值整体上被弱化了。”
亚历克斯·梅尔(Alex Mehr)是约会网站Zoosk的合创者,在斯莱特采访到的约会网站的高管中,他是唯一不认可这种普遍观点的人。梅尔认为,网上约会无非是为人们排除了约会的障碍而已:“网上约会不会改变我的口味,我在第一次约会时的表现,或者我是否能成为一个好伴侣,它只改变了发现的过程。至于你究竟是从一而终的人还是逢场作戏的人,都与网上约会无关,只与个人品性有关。”
爱丽·芬克尔(Eli Finkel)是美国西北大学的社交心理学教授,她也在研究网上约会将如何影响人际关系。芬克尔认为,目前只能得出三点客观的结论:“第一,最好的婚姻可能不会受影响,因为幸福的伴侣不会在交友网站游荡。第二,网上约会将增加婚姻状况不好或者平平的伴侣离婚的风险。第三,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它的好坏尚未可知:从一方面来说,有更少的人感到被束缚在不良的关系中对社会来说是好事;从另一方面来说,有大量的证据表明,拥有稳定的爱侣将意味着各种健康益处。”
约会网站的生意越来越好,这也是一个客观事实。2010年11月,号称“第一份互联网大报”的《哈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上已有报道指出:随着越来越多新兴的在线约会网站诞生,网络约会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男女社交的主流方式。美国直销协会(Direct Selling Association)主席尼尔·奥芬(Neil Offen)也宣称:“我们估算有18%的美国单身男女在使用互联网安排自己的约会。”同年《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公布的Pew Research机构的统计数据显示,有将近300万名美国人通过在线网站安排的约会实现了长期的稳定交往或家庭关系。
同一时期,约会网站们也宣布它们的“配对成功率”从20世纪90年代的10%上升到如今的25%。Match.com 宣称每天缔造12场婚礼,而Plenty of Fish 的创始人兼CEO表示,自己的网站每年玉成10万桩婚姻。根据Match.com网站进行的一项调查,网络已经成为人们第三大交友途径(排在第一、第二的分别是“通过工作/学校”和“通过朋友/家人”)。每6对新婚夫妇中就有一对通过网络约会网站结识(一夜情未列入统计范围)。对于很多习惯于在网上开展大部分社交活动的20多岁的年轻人来说,网络约会就像在教堂或是夜店排队上厕所时邂逅异性一样自然。
然而,约会网站毕竟不是婚庆公司,事实上,许多网上交友网站的盈利模式和用户想要建立长期伴侣关系的想法是背道而驰的。贾斯汀·帕菲特(Justin Parfitt)是位于旧金山的一家约会网站的主办者,他就十分坦率地向斯莱特解释了一个典型的约会网站执行官的心态:“他们是这样想的:我们应该尽可能地让这个笨蛋经常回到我们的网站上。”
当用户的账户在Match.com这样的约会网站上很长时间不再活跃时,用户就会收到通知,通知他们有很多美妙的人浏览他们的资料并渴望和他们聊天。“我们的大多数用户是回头客。”Match.com的布莱特说。1995年上线的Match.com是最早的约会网站之一,如今它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约会网站,也是最大的约会网站信息汇总商,在其名下汇总了30家约会网站的信息。Match.com隶属于美国电子商务大亨迪勒(Barry Diller)的IAC公司,其收入占母公司总收入的1/4。2011年1月,美国“互联网约会业执行董事联盟”(Internet Dating Executive Alliance)主席马克·布鲁克斯(Mark Brooks)发布一份名为《网络约会如何改变社会》的报告。根据报告中提供的数字,截至2009年8月,全世界互联网上已经存在1.13亿网络约会网站用户,而此类网站2008年在美国的年收入达到13亿美元,到2013年预期达到17亿美元。该报告引用来自Juniper Research机构的统计数字:美国的手机约会市场拥有近5.5亿用户,而中国的互联网约会产业用户在2010年也已达到近1.4亿。

精准算法与虚幻数据
在2011年7月的一篇文章中,《纽约客》的专栏作者尼克·鲍姆加登(Nick Paumgarten)详细描述了约会网站的配对算法(Matching Algorithms)。大部分约会网站至今仍然只依靠传统的问卷调查收集信息的方式。这些原始数据在配对过程中揭露了大量的个人爱好,被称为“表述性偏好”(Stated Preference)。人们具体描绘自己希望交友的对象与实际情况往往不符,这种心口不一被称为“显示性偏好”(Revealed Preference),是配对算法中的必要部分。即使网站不真正了解你,它也能推测出谁正好适合你。存储了你的表述性和显示性偏好后,软件会寻找那些在这两者上与你类似的人。
约会网站配对成功的技巧在于如何权衡每个变量间的相对分量。系统工程师阿马拉斯·桑博尔(Amarnath Thombre)负责监管Match.com的基本算法,算法中考虑了1500种变量,比如:是否抽烟、是否跟抽烟的人来往、是否言行不一。这些变量会与其他人的变量进行比对,然后产生一系列所谓的“交互作用”(Interactions)。每种交互作用都有一个评分,以量化对象对某种行为的忍受度。
因算法独特而大获成功的约会网站是OK Cupid,它选择了轻松、诙谐的路线,采用了直觉方法和独有的配对策略,更像是年轻人的消遣。因为访问量高、风格活泼,OK Cupid有潜力拥有互联网上最多的钻石单身汉。
OK Cupid的创始人是4名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数学专业学生。20世纪90年代末还在学校时,他们就创立了一家名为Spark的公司,编写并发布在线学习指南而大获成功。当时,他们以名为Spark Match的交友网站做过试验,配对算法所用素材是一些性格测试和滑稽的调查问卷,他们将这些发布到Spark上以招徕访客。2001年他们将Spark出售,但2003年重聚时再度产生了建立约会网站的设想。为了解决约会网站需要有大量用户才能吸引用户的难题,他们设计了一些测验,其中最重要的是“约会人格测试”(Dating Persona Test)。用户可以通过测试得知自己是“公羊男”(Billy Goat,深思熟虑而粗鲁的性幻想者)、“抚背男”(Backrubber,深思熟虑而温和的性幻想者)、“蒸汽男”(Vapor Trail,随意的粗鲁的爱情高手、“泳池男”(Poolboy,随意的温和的性幻想者)还是“末日超男”(The Last Man on Earth,随意的粗鲁的性幻想者)。随后可以得到相应的建议,比如:“半人马男”(Hornivore,漫无目的、性欲旺盛、以身体思考型)可以考虑“成吉思汗女”(Genghis Khunt,控制男人欲、带来痛苦型),但要避开“十四行诗”(Sonnet,浪漫、充满希冀、沉着镇静型)。他们也鼓励用户提交自己的测验。至今为止,用户已经向该网站提交了4.3万项测验。回答不同的问题,你就能找出自己是《迷失》里的哪个角色、哪个国际象棋子或者是哪种化学元素。
OK Cupid以各种时髦的无厘头测验为诱饵,吸引了大量用户,随即开始了配对的魔术。如今,OK Cupid已经收集了超过8亿个答案(网站上人均回答了300个问题)。它的创始人之一、编辑部主管克里斯汀·拉德(Christian Rudder)维护着OK Trends博客,他筛选浩如烟海的数据,编写成有数学论据的小型论文。每一问题首先被分解为三个变量:用户自己的答案,用户希望配对的人会给出的答案,用户心目中双方答案的重要性。随后问题会被按照对人群分类的有效性进行排序。
除这种常规筛选算法外,OK Cupid式算法的重要依据之一是那些“具有意料之外的高预见性”(Unpredictably Predictive)的问题。筛选过程中OK Cupid发现,“你喜欢啤酒的味道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是否你第一次约会就愿意做爱”这类判断,比其他相关问题都具有预见性(Predictive)。换而言之:对前者回答“是”的用户很有可能对后者同样回答“是”。OK Cupid还分析了3.462万对在OK Cupid网站相遇并成功配对的情侣,结果显示:如果不经意间他们对首次约会问题“你是否喜欢恐怖电影”、“你孤身到外国旅游过吗”、“你不觉得抛下一切去海上漂泊很有意思吗”有相同的答案,这很可能预示着他们能够长相厮守。
OK Cupid的用户还可以对其他用户的个人介绍进行评分,网站则将这些分数归入配对算法中,并根据其他人对用户的看法,展示哪些人大致处于其魅力等级中。OK Cupid的另一创始人、总监兼创意总管克里斯·科恩(Chris Coyne)将这种以“八卦问题”为特色的配对算法的灵感归结为日常生活中的约会经历:“我们试着把这个软件当成生活中的一个朋友。如果我是你的朋友,并且告诉你某人希望与你有一个完美的约会,你一定会先开始问我一些问题,比如她喜不喜欢跳舞,她是不是体毛重,她是高是矮等等。在网上也是如此——人们喜欢向系统提问或者回答系统给出的问题,哪怕是一些极端私人的问题。”
OK Cupid把所有的回答输入位于纽约的服务器中。首先系统算法会按照用户的重要等级找出那些答案与用户的回答最相符的人——不只是他们的答案符合用户的期望,用户的回答也要符合他们的期望,然后系统判断这种特别关联的独特程度。这些配对随后以百分率的形式表现出来。每一个配对搜索都需要经过数以千万计的数学运算。
如何处理计算好的配对是随后要解决的问题。拉德说:“酒吧里存在一种自动的配对调节机制:当你看到10个男人围着一个女人,可能就不去凑趣了。在互联网上人们却不知道某个人会有多走俏。这就造成了一种恼火的情况:男人们收不到回信,而一些女人由于受到太多关注而不堪重负。”信息交流的频率因此也被列为重要因素。OK Cupid的CEO萨姆·亚甘(Sam Yagan)说:“我们监视着客户,他们却不知道被监视了。”随着监视,算法不断被改进,某些变量的比重被改变,以此来调节上一次循环计算的成功率或失败率。假如说在OK Cupid的世界中还存在某种长久的信仰,那就是“数学”。
2011年2月,OK Cupid以5000万美元现金的代价出售给Match.com。同一年,OK Cupid还从另一性质的买卖中挣到了钱。网站运营期间,OK Cupid得到了大量数据,这个数据库本身就为OK Cupid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资源,可以将其卖给学术界。从广泛的人口统计学意义来说,没有其他的氛围会让这么多的人自愿回答如此多的私人问题,对于社会科学家们来说,这简直是个巨大的金矿。事实上,自2010年底开始,OK Cupid已经陆续将原始数据出售给了6名学者。曾有美国政治科学家仔细查看OK Cupid的数据,以此来决定政治观点是如何影响选择社交伴侣的,并由此预测大选中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成败。
OK Cupid声称原始数据出售时已经经过编辑或者匿名处理以保护客户的隐私,但2012年1月手机交友平台Grindr的数据泄密事件又将焦点集中在约会网站数据管理问题上。美国电子前沿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EFF)在2012年3月的一份报告中称:约会网站大量收集了用户的隐私数据,但在保护隐私上做得很糟,使个人信息(如性取向、关系史)可被多方获取,如法庭、未来雇主、广告公司、黑客等。EFF董事雷尼·莱特曼(Rainey Reitman)称:“银行等使用HTTPS协议加密来保护用户密码,许多约会网站却不把该技术作为缺省选项。OK Cupid根本就不用加密,这是个大疏忽,很容易泄露信息,而用户还以为该类信息受到了保护。”OK Cupid同时被指责出售含有真实姓名的个人信息:“这些网站的经营者从用户摘出大量数据,将其打包、出借或出售给网上营销商或附属机构。”
当涉及Ashley Madison这样的网站时,网站数据库中的信息能否作为离婚诉讼的证据又成为益发纠结不清的法理问题。然而,所有这些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是:个人账户中的信息全部是真实的。埃米·韦伯(Amy Webb)是Webbmedia Group的主席,一直致力于研究新科技对于交际的影响。在斯莱特出版《算法时代的爱情》的同时,她也出版了自己的新作:《约数,一个爱情故事:我如何在网络约会中游猎并找到我的配对》(Data,A Love Story:How I Gamed Online Dating to Meet My Match)。有读者抱怨斯莱特在他有关约会网站的文章中丝毫没有考虑女性的视角,韦伯的新书倒可以提供另一个角度的看法。韦伯在故事开始时是一个30岁的单身纽约女性,经过几次失败的网络约会后,她认定“我的个人档案吸引来了错误的男人”。利用自己学过的数据库分析知识,她更改了自己的档案。总结了自己理想对象应当具有的特征后,塑造出了两个人物:“犹太医师1000”与“律师2346”。以找到“母亲梦想中的犹太医生或律师女婿”为动力,开始以逆向学习的方法了解什么样的女人会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韦伯因此在一个月里实现了同96名女性的网络约会,获益匪浅。在她恢复自己的女性身份后,称她心意的犹太帅哥很快出现了。
这个故事的后半截很励志,但前半截很有些间谍小说的味道。在“潜伏”的过程中,韦伯印象最深的是:“我知道约会者一般都会对自己的体重撒谎,我有思想准备。令我震惊的是,有那么多的女人会对自己的身高撒谎。与我约会的96个女人都将自己的身高报为5英尺1英寸到5英尺3英寸之间,而据我所知,美国女性的平均身高是5英尺4英寸。这些女人都认为男人会偏好更矮小、更秀气的约会对象。原因?因为男人也都对自己的身高撒谎。” 选择雅各布爱情现实算法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