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真实的于是之
作者:石鸣(文 / 石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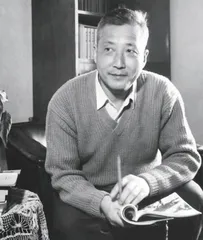 ( 于是之 )
( 于是之 )
2013年1月20日下午,濮存昕正在参加《北京青年报》年会。去年是北京人艺成立60周年,《北京青年报》文艺版的系列报道获得了报社年度评奖的特别奖,濮存昕作为北京人艺副院长,在会上旁听发言。“说到了北京人艺庆祝60周年的时候,相继有多少老艺术家故去,有多少在医院里生命垂危,有多少身体已经不好了。恰恰在17点10分时候,还在说于是之,说到去看他,提到他的名字。仿佛冥冥中,是之老师气断的那个刹那,就是那个瞬间。”濮存昕向本刊记者回忆。之后没过多久,他就接到了短信,17点19分,于是之辞世。其时正是傍晚,被阴沉雾霾笼罩了一整日的北京城飘起了雪,白雪纷纷扬扬,如同《茶馆》最后一幕,三个老头话完沧桑后,纸钱抛洒飘落。那日是农历大寒。
那天晚上,北京人艺新一轮由年轻演员主演的《骆驼祥子》正好演到最后一场。于是之曾在戏中扮演老马,这个人物是他最满意的一个角色,也被认为是他演得最好的角色之一。多少看过当年演出的人提起他的那场戏,都用“出神入化”来形容。整场演出中,老马上场不过两次,戏份不过10分钟,一个在雪地里拉车拉到快要冻僵的老头儿,想烤烤火,于是进门“瞧瞧老掌柜”,顺便与在场的其他车夫拉拉家常。暖和过来了,又深吸一口气,撩起门帘,冲进外面的风雪中。台词没几句,情节也不复杂。“但是他一上场,就是天上划过的一道彗星的光亮,是众多礼花绽放中最震动人心、最让你喜悦的一次爆发。你会觉得在今天晚上的审美欣赏中,最美的那一瞬间出现了。他创造了那个瞬间的艺术真实,比生活本身更加真实。”濮存昕说。
濮存昕告诉本刊,当晚演出开始前,他走进后台,此时,于是之逝世的消息已经传开。扮演老马的张万昆正坐在沙发上,一笔笔勾画于是之创造的那个装:花白的头发,脸上的皱纹、胡茬儿,皴裂的皮肤,手上的老茧,披挂的破衣烂衫。本来是上台前平常的准备,此刻却具有了特别的哀悼意味。与于是之同台共事过的人都知道,他生前对设计角色的外在形象颇为看重,他甚至说,最“腻味”演员临上演前还“不负责任地”把脑袋交给化妆师:“斯坦尼说过,在脸上抹油彩而寻找性格化的事是可信的,化装是演员的创作啊!”
谢幕时,主演祥子的于震带领所有演员,与观众们一起悼念于是之。他引用了后者生前告别演出时谢幕的一句话:“感谢观众的宽容。”这一次,于是之是真的告别了。
于是之先生86岁的一生,留下了多个光彩照人的舞台形象,表演艺术之精湛后人谓之“一代名优”,当了8年北京人艺院长,任上主持了各种是非功过任人评议的工作。他不好著书立说,不张扬自我,名片上仅印“演员于是之”五个字;他孜孜好学,人前话少,面对纷争,多选择隐而不发,后来者只能从他身边人的只言片语中努力捕捉其形象,又往往因“为尊者讳”等等顾虑难以一窥真貌。他给人们留下了一个个谜团——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 《茶馆》中饰王掌柜 )
( 《茶馆》中饰王掌柜 )
用濮存昕的话说:“有一个个性的于是之,复杂的于是之,他有大爱、大恨、幽默、忧伤,在台上光彩照人,表演深深陶醉着观众,也陶醉着他自己。他也会失意、茫然,不知所措,一个有太多太多话要说,却不知想说什么,缄口、失言乃至绝语,然而内心又有那么多不甘的于是之。——这些都得我们替他去想象,又或者我们的看法,也都是从自己的偏见出发。”
早年的于是之
 ( 《龙须沟》中于是之饰程疯子(左)、胡宗温饰程娘子 )
( 《龙须沟》中于是之饰程疯子(左)、胡宗温饰程娘子 )
曹禺之女万方向本刊记者回忆起于是之留给她的印象,是一个字:“亲”。从她五六岁起,就已经认识了这位“于是之叔叔”。跟他相比,苏民、蓝天野给她的感觉都不太一样:“觉得苏民叔叔可帅呢”,蓝天野则是“不光演戏,还画画,浓厚的艺术家气质”。
对于是之,万方说:“印象最深的是他来家里,跟我爸一块儿,还有梅阡,写剧本《胆剑篇》(后于1960年公演)。那段时间他经常在我家,我就跟他熟识了。但奇怪的是,梅阡叔叔其实也在,是三个人,可是梅阡叔叔就是一个很严肃的大人的感觉,有点威严,我跟他几乎没什么交流。于是之叔叔就不是,可以很随便地和他说话。”
 ( 《骆驼祥子》中饰老马(右) )
( 《骆驼祥子》中饰老马(右) )
她还记得,于是之管她妹妹叫“小滑稽”,说她心里老有一个小孩。长大后,她才觉得于是之“看人很准”:“我妹确实是长到这么大,实际上还是有天真的一面。”
小孩子们也可以嘻嘻哈哈地给于是之起外号,开玩笑。濮存昕说,对于他家三个孩子,于是之的专业称谓就叫“于树增”,因为他弟弟小的时候,口齿不清,叫不清楚“于是之”这个名字,“于、是、之,起音全都在前面,唇齿不费点力气,说不好这三个字”。
 ( 1992年,北京人艺建院40周年活动现场,于是之(右)和曹禺的合影 )
( 1992年,北京人艺建院40周年活动现场,于是之(右)和曹禺的合影 )
于是之逝世后,万方在悼念文章里写到了她七八岁时与于是之的一段对话,谈论他在《青春之歌》里演的余永泽。“他完全是把我当成一个小谈伴。我跟他说我不喜欢他(余永泽),他说同意,我也不喜欢这个人。”万方告诉本刊,“他和我爸爸很像。我爸爸就从来不把我当成一个小孩子,都是很平等地跟我说话。于是之叔叔给我很亲近的感觉,在他面前说什么,你都觉得很自然,就像和一个朋友说话一样。他不会否定你,即便有不同,也是引导你,从小就是这样。”
1952到1962年,北京人艺建院最初10年,在“四巨头”(曹禺、焦菊隐、赵起扬、欧阳山尊)的主持下,诞生了人们至今仍旧津津乐道的那些剧目:《茶馆》、《雷雨》、《日出》、《骆驼祥子》、《龙须沟》、《虎符》、《蔡文姬》……彼时,于是之一生中被认为最精彩的三个角色已经全部亮相:《龙须沟》中的程疯子,《骆驼祥子》中的老马,《茶馆》中的王掌柜。《龙须沟》被翻拍成电影,更让他红遍大江南北,而他当时年仅25岁。
 ( 1979年,老舍夫人胡絜青(左二)和人艺著名演员蓝天野(左)、于是之、郑榕(右)在一起 )
( 1979年,老舍夫人胡絜青(左二)和人艺著名演员蓝天野(左)、于是之、郑榕(右)在一起 )
“在老一辈艺术家里,他是最早成功、最先成熟成名起来的一个演员,可是在生活中,他没有优越感。”濮存昕说。他从小在北京人艺长大,看到的于是之“平平常常”、“普普通通”,在饭堂、在操场,义务劳动下乡割麦子时碰见他,从未觉得谁对他有什么推崇。于是之家在北京人艺,也是到处搬迁,这儿住住,那儿住住,史家胡同56号也住过,剧院宿舍也住过,从来没感到他得到了什么特殊待遇。
林兆华向本刊记者回忆起“文革”期间他和于是之一起在赵起扬保护下“深入生活”、下乡搞创作的事:“唐山大地震第二天,我和于是之就出发了,坐火车,到南方的各个铁矿去采访。那个火车真清净啊,一上火车,一节车厢,没一两个人,走到哪儿哪儿地震。那时候不是提倡同吃同住同劳动么,下矿,劳动,劳动一天完了回来就是吃饭,晚上还随便聊聊碰到哪些个英雄人物,哪些工人有什么性格,能写戏。”关于于是之本人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故事呢?没有。
 ( 《洋麻将》中饰魏勒(左) )
( 《洋麻将》中饰魏勒(左) )
于是之与英若诚是极要好的朋友。然而,两人性格恰恰相反,“英若诚比他精彩多了”。英若诚是公认的大才子,外号叫“英大学问”。“无论在哪里,人们永远围着英若诚,求着英若诚,请英若诚讲笑话,讲天下世界,他口才好,抽着烟,抿着茶,喝着酒,谈笑风生。”濮存昕说。他对早年于是之最清晰的一个印象,却有点狼狈的意味。“我们下乡劳动的时候,我还记得,是之老师穿一条肥腿裤子,那时候穿的衣服都肥。他抱着一个麻袋还是什么,为了走捷径,迈过卷扬机的皮带轮,皮带轮接缝的那个钉子‘哗啦’就把他的裤子从下到上勾裂了。”
除此之外,濮存昕努力搜寻自己几十年前的记忆,却一无所获,连于是之在舞台上的形象也显得模糊不清。“我有幸看了‘文革’前的《茶馆》,没看懂,那时我才10岁,对那里面于是之的表演也没有什么印象,只觉得第一幕最精彩。第一幕谁最精彩呢?黄宗洛老师(饰松二爷),李源老师,演小二德子,打架,李源老师恰恰是练摔跤的业余冠军,他跟郑榕老师(饰常四爷)那两下子真耐看。”濮存昕至今仍能绘声绘色地模仿李源演戏时舔手指甲的动作,这些表演,小孩子们“没见过,精彩!”
当年的北京人艺可谓藏龙卧虎,许多演员在进入剧院之前就已经是演艺界的明星,比如刁光覃、朱琳、吕恩、舒绣文……在政治上,比于是之先进的也大有人在。“抗战时期的干部就不下10个,欧阳山尊老师就不用提了,比如方琯德,那时就是县级干部。而于是之不是党员,没有政治出身,就是一个贫苦的孩子,通过演戏,接触了进步文化。跟随着解放军进城的这些演员比,他自愧不如。在那些大明星演员里头,他就是一平民。也没有看出来他将来会是北京人艺的当家人。”这就是濮存昕童年时对他的印象。
当“院长”的于是之
1984年,于是之57岁,正式担任北京人艺第一副院长,主持院务,这一任命持续了8年。“第一副院长”是北京人艺历史上很特殊的一个职位,在实际工作中,他履行了院长的职责,但在称号上,却仍然是“副院长”。“他主持领导工作的时候,从来没有觉得我就是院长了。我哪里敢继曹禺之后当院长?他对此心甘情愿。”濮存昕这样分析他对于是之这一职位的理解。
然而,已故剧作家李龙云在《落花无言》一书中提到:“在中国这样一个上上下下均处于‘官本位’的社会里,等级的制定与待遇上的差别是那样鲜明、赤裸裸,带给人的感受是那样具体、强烈。所有这一切,于是之在以后的岁月中将逐渐领教到。”
关于于是之如何被任命的过程,李龙云的书里有不少描述。然而他未提及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当时的院长曹禺的举荐和支持。于是之逝世之后,他的多年好友、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童道明打电话给万方,谈起当年曹禺让于是之当常务副院长的想法。“万方说,除了于是之,还有谁呢?”童道明说。
在采访中问万方,她对那过程的印象是:“曹禺不断权衡,想得晚上都睡不着觉,他打电话,去开会,给北京市的领导提建议,也有人来家里谈话。我爸爸是一个搞写作的人,实际上他知道自己没有领导一个剧院的能力。另一方面,50年代北京人艺建院时,他经历过那个‘42小时谈话’,又深知一个剧院领导之重要。尤其是,他对北京人艺看得特别重,一定要找一个内行,了解北京人艺,人品又站得住脚的接班人。”
当时曹禺斟酌了哪些具体的人选,万方并不知道,但是最终举荐于是之,她觉得有一个原因是:“他对于是之非常了解、信任,可以互相倾诉内心的想法。我爸爸一辈子其实朋友不是很多,但我觉得,是之叔叔是他的一个知己。北京人艺则是他们共同的情人。”
在万方看来,曹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举荐原因,即于是之有开阔的艺术家的胸襟。“80年代初,‘人艺’现实主义传统的保留剧目已经很厚重、很结实地放在那儿了,但是怎样汲取新内容、新精神,开拓新的艺术疆界?这一点,也是我爸爸觉得跟他有共识的。”
“当年在‘人艺’(搞改革),是比较难的,现在你看舞台上什么都有,但是当年在人艺,大部分人,甚至直到今天还有人,认为‘人艺’不要去搞什么实验,就演这些老戏就行了。但是,我爸爸并不这样想。虽然他也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他的戏大多也是现实主义作品,但他非常清醒地认识到,戏剧舞台创新的重要性。这种眼光、这种胸襟和包容,可能他在于是之身上也看到了。”万方说。
1982年9月,《绝对信号》在北京人艺饭堂临时搭建起来的舞台上演出,之后被认定是中国小剧场戏剧起始的原点。人们说,这个戏能上演,于是之功莫大焉。
编剧高行健,便是经英若诚介绍,由于是之从外文局引进北京人艺的。导演林兆华与高行健的第一次见面,便是在于是之的家中。“高行健跟他谈构思,谈了三个,还没《绝对信号》呢,那两个我不记得了,就记得一个《车站》。后来我说,这个戏我想排,于是就让他写了,写好后一看,因为是荒诞派的,于是之认为暂时还是现实主义为好,所以搁一搁,写个现实的,才有了《绝对信号》。”林兆华向本刊回忆。
实际上,在《绝对信号》上演前两年,于是之就已经感知到了“小剧场戏剧”这一新生事物可能具有的意义。1980年,《茶馆》第二次赴欧演出归来后,于是之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我们的道路走对了》,文中写道:“他们的小剧场,在西德和法国几乎是每一个大剧场都附设一个。我们见到的,观众少的只有70人,多的也不过300人。设备简单,服装、道具概不讲究。思想上、艺术形式上有新探索的戏以及有争议的戏,都可以拿到那里去演。也卖票,便宜些,请观众们来检验。失败了就散,经济上损失也不大;成功了就继续演下去,或搬到大剧场去演。搞得很火。这有什么不好呢?”
后来,“搁一搁”的《车站》也上演了。许多人认为,高行健的戏不是戏,没有传统的故事、性格,也没有传统的戏剧语言。然而,在于是之主持下,高行健的系列作品在北京人艺获得了上演,导演林兆华也被任命为北京人艺副院长。“这就在给予他保护。老于的戏剧观念其实不同于林兆华、高行健,但是站在这个领导人的位置上时,他宽容。”曾任中国剧协《剧本》杂志副主编、于是之曾经的好友王育生这样说。
童道明向本刊回忆,80年代中期“剧协”的一次会议上,许多人纷纷对高行健群起而攻之,于是之说了一句,“这个青年人正病着”,之后人们一片沉默。
“客观看,于是之挺难得的。说实在的,他并没有也不可能有那样一个戏剧观念,即要怎样超越北京人艺的风格,但是他是艺术家,像曹禺,都是艺术家,对艺术有一个宽容的态度。”林兆华说。
然而,处理行政事务、人事纠纷,并非于是之的长项,他也因此备受折磨。公认的一个说法是,他一病不起,与8年院长有很大关系。
“一个艺术家,怎么能去干行政工作呢?”濮存昕说,“曹禺先生也是同样,他也没法做好,他痛苦至今。而于是之,我认为是替曹禺在担当。”
分房子、评职称、出国,这是李龙云为于是之概括的任上的三大困扰。他的办公室就在剧院楼上,对他办事不满的人要找他,推门就进,躲都躲不过。濮存昕告诉本刊:“他最痛苦的时候是60岁上下时,一天中午吃完饭,正躺在沙发上靠一会儿,忽然鼻子前头有呼吸,一抬眼,脸对脸,鼻子对鼻子,对方按着沙发扶手,俯视着他,然后对他破口大骂,扬言不解决问题的话天天来骂他。还有人指着他骂,于是之你不是个艺术家。可是事后,他也从来没有搞过打击报复。他对这种事最强烈的反应是:‘我算认识这个人啦。’”
据说,像这样的事,如果仔细去追究,大概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童道明还记得,林连昆后来也当了北京人艺的副院长。“林连昆跟我说了一句话,我是要帮帮老于。意思是,老于太苦了,帮他分担分担。”
那时,曹禺已经卧病在床,于是之经常去家里或者医院看他,这时候万方多数在场。“他可能受了很大的罪,但他不说,可我爸爸都知道,别的人来,有时会告诉我爸爸。我爸大概对他说,是之啊,我知道你难受啊,你受了大罪啊。可是之叔叔就摇摇头,没什么话。”
“每次于是之来看我爸,我爸简直是高兴极了,拉着他的手,让他坐在身边。其实俩人也不是一直在说,也会停顿、沉默,坐一会儿,相对无言。但恰恰这种时刻,特别能体现他们彼此的相知。那种情绪和气氛,让我觉得,他们的交流不仅是对具体的剧院事务,可以说有一种对人生共同的感叹吧。”万方这样说。
演员于是之
1985年,于是之曾经有一个机会离开北京人艺,去担任文化部部长。这段故事在后来任文化部部长的王蒙的回忆录里有生动的描述。最终,于是之说服自己的最后一个理由是:“眯”在北京人艺,“抓空儿备不住还能演点儿戏”。
就在这一年底,于是之创造了他在北京人艺最后一个被人传诵的经典形象,《洋麻将》中的魏勒。他演戏一贯以认真著称,年轻时在歌剧《长征》里演毛主席,上台只有一句台词和一个背影,他却看完了整整四卷“毛选”。然而,此时由于行政工作繁忙,他几乎没有时间来准备角色。
“他演魏勒,随手拈来。因为他的年龄,完全能体会这个人物的内心,我觉得他都没怎么演这个人物,那几年当院长的经历——磨难、受苦、忍耐、极度无奈,他已经把这个老人的内心完完全全吃透了。”万方说。
这是一部只有两个人物的戏,从头到尾的剧情就是养老院里的一个孤寡老头和一个孤寡老太打了14把牌,一边打牌排遣无聊和寂寞,一边随便聊聊各自的故事。“他把自己的人生全部倾注进去了,一个在养老院里忍着去生活的暴老头儿,面对朱琳阿姨演的那个老太太,‘闷得很,打牌吧’,他又输,不断地输,最后勾起了宣泄,突然间发作,他拿那拐杖‘啪、啪’地抽打桌子,散发出他人生中所有的不快,淋漓尽致极了。你就知道,他一直不发火的一个人,也会瞬间发火。他有太多太多的不满、不公、苦难、积郁。”濮存昕说。
万方几乎看过于是之演过的所有的戏,其中她对于是之演技的印象非常深刻、人们谈论却比较少的一个戏,是1965年北京人艺上演的《像他那样生活》。英若诚、梁秉堃、童超三个人合作的剧本,于是之演主角——越战期间暗杀美国国防部长未遂牺牲的英雄阮文追。“那时候他岁数已经比较大了,我记得他当时锻炼,为了让自己整个姿态都像是年轻人一样。在舞台上看到他时,我特别惊讶,哎呀,于是之怎么成这样了?真的是一个年轻人的样子。虽然那个戏因为时代原因,可能再也不会有人提及了,但是他那种青春的形象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
在《龙须沟》的程疯子和《茶馆》的王掌柜两座高峰之间,于是之曾经经历过一个谷底的失落,那就是《雷雨》的周萍。他后来总结是,惨败,甚至差点因为这次失败而改行。
他也困惑过,当年演完程疯子,在焦菊隐先生指导下结结实实建立起了一套观念、方法,怎么后来就不适用了?在《十年从艺小结》中,他曾写道:“对周萍,立意不明,未能对角色高瞻远瞩,自己与角色有较远的距离,但没有克服这个矛盾。大家对这个角色的议论也不少,认为他冷酷、自私等等,我也不知道如何掌握,完全陷于被动。”
据万方回忆,当年《雷雨》排演时,其实不仅于是之一个人遇到了表演的难题,所有演员都有类似问题,为了解决演员们思想上的问题,曹禺还专门到茶馆去和他们聊剧本。当时在《雷雨》中演周朴园的郑榕曾经跟她说过,他们演戏前不由自主地先在心里酝酿,先想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我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一句台词之前不知道有多少想法,然后才说出这句台词。“当时我爸坐在底下看,幕间休息时我爸就跑到后台去了,说,‘快!快!快!受不了!’顾虑太多,台词说得太慢了。”
“在政治环境影响下,演员找不到自己的人物,拿不准该对他怀有什么样的感情,也没法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人物里面,等于前面隔着一堵墙。那个时候讲阶级斗争,周萍是一个资产阶级少爷,他是一个坏人,但是如果把他演成一个坏人,于是之叔叔肯定没法演了,不能接受。可是究竟他在心里应该怎么想这个人,我觉得他当时确实是有点混乱的,再加上他本身没有这样的生活经历。其实繁漪也有问题,但是我相信吕恩阿姨的繁漪应该不至于那么差,毕竟她借自己的经历,能够抓到一点东西。”万方说。
在濮存昕看来,于是之真正攀上其现实主义表演创造的高峰,还是在“文革”以后。“剧院开始恢复一批老戏,于是之经过沉淀、反省,再次在舞台上大放异彩。那时候不止他一个人,包括林连昆、朱旭,都特别受观众的喜爱,每每有非常精彩的创造。但是慢慢地,评论界、观众、剧院内部,逐步形成一种共识,觉得是之老师的表演最符合、或说靠近我们一直推崇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符合焦先生推动的中国话剧民族化的方向。”
与之相对应的,是他在创造上的不停歇。林兆华对他印象深刻的是:“演了多少年的角色了,已经很成熟了,他还在不断琢磨,这句台词说得怎么样,那个动作怎么样。这是艺术家的品格。”
1997年是中国话剧诞生90周年,一系列的纪念活动中,有一个“于是之表演艺术研讨会”,于是之本人出席了,那时他的病势已越来越重,并且在1996年《冰糖葫芦》后彻底告别了舞台。濮存昕作为年轻演员参会。“太多太多人的发言,说到一半时候,由于溢美之词越来越多,是之老师如坐针毡,在走神。你能看到曼宜阿姨在一旁安抚他,让他喝水。当一个他非常欣赏的作家、也是他要好的朋友,把他与老舍、焦菊隐先生并论的时候,他一下子急了,拍着桌子站起来了。所有人惊愕了,那个发言的人很尴尬,很多人劝是之老师坐下,他拒绝。”
接下来发生了濮存昕终身难忘的一幕:于是之一定要发言,因为疾病使得他的语言功能发生障碍,在场的人听不懂他的意思,他便让老伴李曼宜翻译。“焦,焦,他指着对面一座位。哦,他的意思是说,那是焦先生。他往门口走,站在那儿,关上门,打开门,进来,做了一个动作,焦,焦。哦,他说焦先生看了表演,说他演得不对。他又出去了,又做了一个动作,焦,焦。还是演得不对。又出去了,进来,从容一些,坦然一些地做了一个动作,舒了一口气。这回对了。”
“他说他就是演员,我就是干这个的,我是经过从不行到行的,我是一个真实的演员,什么大师不大师的,怎么可以把我和焦先生放在一起比。”他把意思表达完了,人们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
散了会,于是之也没有吃饭。“那时候生活也不富裕,有顿饭吃,大家很高兴的。我看着他走了,我留下来吃了。”濮存昕说。
很多人都忘不了1992年北京人艺建院40周年纪念演出《茶馆》时,于是之最后一场告别演出的情景。那次演出是当年的原班人马,老一辈艺术家们全部出动了。这些人里,于是之的身体情况最不好,恐怕以后再也没有上台的机会了,因此才定为了“告别演出”。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老演员在告别舞台的瞬间的背影。最后一幕,撒完纸钱,笑骂人生之后,一片寂寥,他一个人,很长很长的无言的空场。他默默走到椅背那儿,去拿裤腰带,准备上吊。这是他演了一辈子的戏,通常演这一段,重点是放在前头的,就是非常决然的,拿起来,捏在手里,拧身下场,这个戏就结束了。可是在那最后两天,他的手已然停在那儿,不动了,把脸别到后头去了,就这一个动作,一个背身,便是不忍、不舍,勾起了……”濮存昕说不下去了。
然后他又告诉本刊记者:“他所有的表演,都把他自己的人生融到里面去了,分不清是他,是角色,是表演,还是真的在生活。从他身上,我就得出我自己对于表演的一个标准:你会不会在舞台上生活?你这种生活,是和所有观众的心灵有关的。这种艺术,由艺术家的生命诞生,又被艺术家的生命带走了。”
也许用林兆华的一句话来概括于是之的演员生涯会很贴切:“他的一生都在戏里。”
关于知识分子的一点余音
1994年5月,于是之因病退休已两年,他给童道明打电话,提议做一次戏剧对话。“实际上也是他最后一次围绕戏剧的谈话了,以后也再没有写过文章。可能他对自己的病情有一个预感,觉得自己说话功能在逐渐失去。我们大概谈了一个多小时,由我整理,由他定稿,发在《中国戏剧》上。”童道明告诉本刊记者。
在那次谈话中,于是之明确提到了他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看法,声明了自己在“从自我出发”争论中的立场。有谁能想到,不过10年,要不要“从自我出发”的问题就已经基本上从年轻导演们的舞台创作中消失,似乎陈旧得要进棺材铺。困扰老一辈几十年,耗费了他们多少精力、多少心血的问题,新一代的创作者们轻轻一拨,就置于一边了。
“我们的谈话是非常多的,最最惊心动魄的,我觉得是他讲知识分子,说我们的戏剧有负于知识分子。”童道明回忆道。那是在英若诚因肝硬化而病重吐血的第二天,于是之去看望英若诚后,打电话要找童道明聊天。“他说,我最大的遗憾,是北京人艺从来没有演过一出为知识分子说话的戏。”
类似的观点,英若诚1985年也提过,“话剧是写给知识分子的戏剧”,结果引起很大争议。
“因为我是搞戏剧史的,我后来就写了一篇《知识分子与戏剧》,借题发挥。戏剧呀,以前都是讲帝王将相,西方的戏剧也都是这样。什么时候知识分子才走上舞台成为主角呢?易卜生,契诃夫。也就是说,现代戏剧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知识分子走上舞台。”童道明说,“老于早就演了《丹心谱》了,那个主人公是知识分子啊,老中医,为什么他不觉得这个戏是为知识分子说话的戏呢?因为虽然人物是知识分子,但并没有主体地位,那是个歌颂总理的戏。”
2009年4月,北京人艺首演郭启宏编剧的《知己》。王育生为此戏专门写了剧评《我为知己浮一大白》。“值得为《知己》喝上一杯!因为他把这个(知识分子)问题提出来了,尽管还是以借古讽今的方式。”年轻一代的剧评家想的却不一样,有人认为此剧并没有出奇的地方,“主要写的不过是知识分子的不平之气嘛”。
郭启宏来到北京人艺写剧本,当年也是于是之的招揽。他曾经专门写过文章,感慨于是之对创作的尊重,对异己之见的包容。2009年,北京电视台播出18集传记片《演员于是之》,一时间,于是之“平民演员”的称号广为流传。郭启宏却撰文表示反对,认为以所演角色的“平民特色”来定义演员的“平民性”不可思议:“与其臆说于是之与‘平民角色’有着不解之缘,莫如认真研究于是之的‘知识分子情结’。我认为,于是之是中国文化界真正的知识分子。”
此时,于是之已经躺在协和医院的病床上,对世事一无所知。与于是之家人熟识的人都知道,于是之患病早期,除了说不出话,认不得人,也无法与外界交流。他的病,许多人认为是“心病”,与他极强的自尊心,又极度内向的性格有关。
“尽管后来人们说,他把多少痛苦藏在心里,我爸爸也一样,有很多痛苦藏在心里,他们的性格是有率真的一面的,才会让一个孩子觉得亲近、随便。”万方说,“但是我爸在能够露出他率真的一面时,会更直接一些。是之叔叔让你觉得很亲和,但是他不会像我爸爸那样,一下子‘哗’,完全无拘无束。他比我爸爸更内敛一些,含蓄一些。”
于是之后来定居在紫竹院公园附近的一座高楼里。家里有一扇窗户是面向紫竹院公园的,那扇窗户的窗帘每天必须由他来拉开。要是哪天起来了,发现窗帘提前被拉开了,他就会不高兴,会很生气地把窗帘拉上又拉开。“这说明什么呢?他不能与外界交流了,可是他脑子里还在想什么呢?”濮存昕自问道。
万方对于是之、英若诚和父亲曹禺最美好的回忆之一,就是当年在英家聚餐:“都爱喝点儿,喝着酒,聊戏剧,聊艺术,聊人生的感受,可以直言心中的任何想法,他们之间的那种默契、热情、兴味盎然,我旁观着,觉得真的很幸福。”
童道明和王育生异口同声地说:“于是之是不可重复的。”然而,也并没有人愿意当于是之。为什么?“太难!要有担当。”
濮存昕说:“还是不要像是之老师这么痛苦。我们是经历过‘文革’的青年,也有对‘真’的认知能力。我们受前辈的影响,要把好的东西留下来,自然而然,也就影响后面的人。”
于是之逝世了,一个时代结束了。“他们这一代太顺从意识形态,不敢越雷池一步,虽然他们也知道,这些东西有的时候跟艺术创作是格格不入的,但是不能不服从,悲剧的地方也在这儿。”林兆华说,“于是之、英若诚、童超、焦菊隐、曹禺,像他们这样有文化的艺术家,当今不太多,但是你还是得寄希望于下一代会出现这样的人。” 曹禺于是真实于是之知识分子英若诚濮存昕林兆华龙须沟雷雨骆驼祥子艺术家戏剧爱情电影智利电影寻找